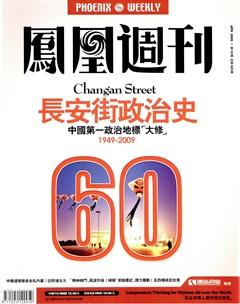五四:敞現或遮蔽
林賢治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五四運動的發生,距今已有90個年頭。當年的風云人物已然逝去,文物部分保留下來,部分遭到湮滅。所謂歷史,更多的是歷史學話語,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闡釋者,從權力者到學者文人,也都各自帶著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觀念和意識形態來審視過去。由是,五四出現了眾多的面貌。無論是事件和事實本身,還是固有的意義,五四歷史的完整性都沒有得到充分的敞現,反而,通過不斷的改寫而被遮蔽。
五四作為矛盾統一體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游行示威活動,抗議中國政府對日的屈辱政策。以北京大學為首,學生群體行動,印發《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散發傳單,高呼口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深得工商界及市民支持。在政府出動警察逮捕學生之后,斗爭的怒火迅速蔓延到上海,以至全國各地。
其實,愛國斗爭有很長一段引信。正如李長之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五四運動當然不僅指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的運動,乃是指中國接觸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歷程,‘五四不過是這個歷程中的一個指標。”
經歷過鴉片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后的兩度帝制復辟和軍閥統治的陣痛,新興的知識階級上下求索,終于選擇了一條有別于原來的“富國強兵”的道路,即通過思想文化方面的變革,普及教育,傳播新知,以促進廣大社會的精神覺醒。在此期間,《新青年》雜志的創辦及北京大學的改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兩個標志性事件,顯示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力量,在五四運動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一刊一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
五四運動是誕生于新世紀的政治與文化的連體嬰兒,既血肉相連,又相互牽制。“五四運動”一詞的發明者,運動的干將羅家倫明確提出: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與“救國運動”合流而成,著重的是兩者的統一。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對五四作為“青年愛國的運動”持一種批評意見,強調兩者的矛盾性,說五四事件使學生成為一個政治的力量,思想成為政治的武器,使原先的新文化運動“政治化”、“變了質”,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無論作為一個過程,還是一個結構來看,五四都是一個矛盾統一體。我們看到,《東方雜志》及《甲寅》群體雖然與《新青年》雜志群體相頡抗,但是,杜亞泉、章士釗,吳宓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介過西方的觀念和知識。就是說,敵對的雙方依然存在著某種一致性。我們還可以就五四新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在內進行觀察,其中,孫中山政治激進,文化保守,胡適文化激進,政治保守,陳獨秀和魯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顯得相當激進,然而,一個最終投向政治革命,集體主義,一個堅持“思想革命”,堅持“獨戰”,激進的方向和形態也各有不同。作為一個運動過程,五四是從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走向思想文化運動,再走向社會運動并還原為政治革命的,前前后后發生過很多變化,而作為一個結構,一個實體,五四同樣是多元多向、參差多態的。因此,必須看到這種文化現象的矛盾性,看到新舊事物彼此沖突、斗爭和互相轉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五四沒有一個基本的面貌,沒有一個核心價值。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五四是新舊政治文化勢力的一場殊死斗爭對五四的評論必須首先置于斗爭的場域中進行。二,五四運動的主體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是有意識地、自覺地要充當戲劇的主角,即啟蒙者而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毛澤東說五四運動的“弱點”,就是“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正好從負面揭示了這個事實。對于五四,或五四人物的評價,我們不能離開知識分子的一般定義,不能離開知識分子與權力、群眾和社會的關系來進行三、五四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源頭,當我們試圖發掘并利用其中的思想文化資源時,必須立足于當今中國社會的變革之上
五四作為一個歷史評價對象,是先天地具有傾向性的。因此,所有關于五四的闡釋,無論如何標榜“中立”,“客觀”、“公正”,其實都是有傾向性的,顯示出各自的官方的,民間的、進步的,保守或倒退的立場,沒有哪一位論客可以避免,
世界主義與本土主義
胡適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是人本主義對中世紀神權統治的挑戰,就這一意義上說,五四頗有與之洽合之處。但是,在歐洲,作為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是內發的,是古文明的復活,而在中國,所有更新的觀念都是從外部植入的,現代觀念的引進,意味著古文明——實質上是專制化等級化的儒家文化——的覆滅。
所謂現代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西方的觀念。自由、民主、人權、共和、科學,這些名詞無一不是從西方輸入的,放諸四海而皆準,是謂“普世價值”。《新青年》高張“德先生”,“賽先生”兩大旗幟,簡單化的理解惟是要求“民主”與“科學”,實際上其包涵的意義是更為廣泛的。只要回頭看看當時的文獻,就可以知道,小至個人行為,大至國體,沒有不在討論的范圍之內。
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五四一代提出“價值重估”,“打倒偶像崇拜”,要以自由主義、個性解放代替三綱五常,以尼采、易卜生代替孔夫子勢必引起舊文化衛道士的驚慌和仇限,全面進擊勢必遭遇頑強的抗拒。
五四前后,都曾有過關于東西新舊文化孰優孰劣的激烈論爭傳統主義者極力鼓吹東方精神優越論。康有為上書總統總理,公然主張“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杜亞泉稱說儒家思想是中國的“國基”,輸入西洋學說是“精神界之破產”。辜鴻銘也大肆鼓吹自2500年來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固有文明,作《中國人之精神》。反對世界主義而固守本土主義,在政治人物中更為普遍。袁世凱就打著“特殊國情”的招牌,恢復尊孔讀經。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中鼓吹“禮”,美化儒家文化,都因為它有助于政治“大一統”的形成。繼“新啟蒙運動”之后,毛澤東也提出了“中國化”、“民族形式”一類帶有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內容的主張。
清代以降,海禁大開。“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雖面向西方而多有保留:至辛亥-五四人物,才真正是一代氣魄宏大的世界主義者。魯迅說的“拿來主義”,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口號。他們主張學習西方,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制度、理論學說有不完善的地方,正如不是不知道舊文化中也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一樣,然而他們不得不走極端,在非常時期采取非常策略,連素性溫和的胡適也如此。比如,陳獨秀承認孔教屬“名產”,有其“精華”,但是不能不指出問題的實質在于它只適應于宗法社會封建時代而不適應于現代社會,所以,不能不贊同乃至鼓吹“打倒孔家店”的破壞性行動。“全有”或“全無”,這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策略和方法。在累積了幾千年的封建勢力及其意識形態面前,倘若像一些貌似平和的論客主張的那樣規行矩步,一代人是根本無法走出絕無窗戶的“鐵屋子”的。
但因此,陳獨秀們被指為“全面反傳統”,當年的反對孔教也被等同于“文革”時的“批孔”,正如稱指他們的激進主義成為“文革”“打砸搶”的“濫殤”一樣。“批孔”將學術政治化,出于政治陰謀是盡人皆知的,如何可以拿來同一場源自自由集體的思想解放運動作比呢?傳統的力量是強大的。君不見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對“普世價值”的提法,仍然有人對世界主義說“不”,仍然有人主張尊孔讀經,仍然有人主張恢復繁體漢字,仍然有人在儒家經典中尋找現代性的因子,仍然有人甚至是官員帶頭發起大規模祭祀活動,可以斷定,五四一代對傳統的破壞,實在太不夠了!
愛國主義與個人主義
五四運動被稱為“愛國運動”,救亡圖存,是清末直至五四一代的基本主題。比起辛亥的一代,五四一代更為激進的地方,在于進一步質疑國家,反對國家主義。
一般說來,專制主義者、傳統主義者,都一致標榜國家的利益至上,并主張無條件的服從。當時,一代精英如嚴復、梁啟超等都散布過大量的效忠國家的論調。嚴復提出;保存國家并使國家強大,是衡量價值、制度和觀念的唯一標準,梁啟超則明確表示,要站在中國的民族主義的主流之中。
這種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思想觀念,同樣為后來的政治家所推廣那后果是可以想見的。孫中山首倡“國家自由”論,說“自由”這個名詞“萬不可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蔣介石后來發展了這樣的思想,反對“個人自由”。他強調說,“在社會上,就是要服從各級政府,遵守一切法令。必須我們都能嚴守紀律,服從領袖!”就在這一國家至上的思想基礎上,又引進“黨在國上”、“一黨專政”的思想,建立起國民黨的現代獨裁統治。
憲法和法律是隸屬于國家的。對待所謂“法治”的態度,未嘗不可以看作對國家的態度的一個側面。五四事件發生后,北大教授梁漱溟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公然勸告學生自首。他的道理是,打傷人就是“現行犯”,運動中被稱為“賣國賊”的曹汝霖、章宗祥等縱然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也仍有自由,民眾不能侵犯。言論甫出,即遭到藍公武等人的反駁。要法律、要穩定的秩序呢,還是要人道和正義?北京《晨報》專門載文討論“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其中提出,“現在的國家法律的觀念第一要希望和正義相合……反乎人道正義的國家和法律,我們實在沒有受他們裁判的義務。“知識分子群起為學生辯護,提倡“司法獨立”和“教育獨立”,捍衛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
1920年8月,胡適,李大釗等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宣言說,“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經驗了種種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變遷,這黨把那黨趕掉,然全國不自由的痛苦仍同從前一卡羊。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則不會有真共和實現。”宣言正式提出,《治安警察條例》應即廢止。
民主和共和精神,是五四一代所熱烈鼓吹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強調國家的民主性質,甚至認為沒有民主便沒有國家。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中把國家列入“騙人的偶像”,在破壞之列:主張建立民主國家,以“人民的統治”代替“君主的專制”。他在一篇政論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中指出,除非國家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并關心人民的福祉,否則國家的存在就沒有正當的理由。李大釗一樣認為民族國家的強大與光榮并非基本目的,指出:“民與君不相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胡適對于國家的批判態度也十分激烈,他說“每一國人民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認為,應該把國家僅僅看成是個人屬于其中的許多集團中的一個,是為個人的自由發展而組成的。他在1918年作詩《你莫忘記》,甚至反問“這國如何愛得”,以致“指望快快亡國”。他自命為“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
“人民”,成了五四一代談論國家或愛國的關鍵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在這里并非指簡單的多數,而是“個人”的集合,沒有個人就沒有人民,沒有國家。《新青年》編委之一的高一涵出色地發揮了這一個人主義的思想,質問說,一個人是否應該無條件地忠于自己的國家?他認為,國家只是一種實現個人潛力和世界文明的手段,而非人生的歸宿。他提出國家資格與個人人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個人與政府是兩個關系平等的主體,不能“擴張國家的權利,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又說“國家為人而設,非人為國家而生。”陳獨秀指出,“社會進化,因果萬端,究以有敢與社會宣戰之偉大個人為至要。”胡適提倡“易卜生主義”,其實就是個人主義。他強調,“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他說,如果個人沒有“自由權”,像做奴隸一樣,那種社會國家便絕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傅斯年明確說,“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就是萬惡之源。”蔣夢麟提出,“國家社會有戕賊個人者,個人能以推翻而重組之。”這些言論,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可謂驚世駭俗。
《青年》雜志宣稱“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個人主義是五四最大的思想成果之一,是現代中國最重要最寶貴的精神資源。難得的是,這些先驅者在鼓吹個人主義的同時,對唯我主義(Egoissm)和真正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lsm)作出區分,對公私的權限作出區分。可是,歷史發展的一個事實是,這種講求科學的理性的態度,非但沒有得到確認,反而遭到歪曲,恰恰把個人主義當作唯我主義來批判,結果國家成了沒有個人和個性存在的國家,愛國主義也因為喪失了個體的靈魂,而僅僅表現為魯迅說的“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是五四被遮蔽的最主要的層面之一。
無政府主義與好政府主義
五四之后,胡適與李大釗曾經有過“問題與主義”之氧其實,五四時代既是一個問題的時代,也是主義的時代。這時,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各種社會思潮匯合到一起。1936年,毛澤東會見英國記者斯諾時說:“當時(1918-1919),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和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奇特混合體。”這種思想狀況在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中間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可以看作是無序的思想社會的一種反映。在這期間,無政府主義在各種社會革命思想中間勢力最大,流行最廣
無政府主義者旨在反抗霸權,幻想實現一個把社會責任與個人自由結合起來的社會,這種社會革命思想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使社會與政治對立,致力于文化革命,并把它看作是改造社會的最基本的手段。這樣,無政府主義者就不可能是新文化運動的旁觀者,而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參與者,他們不但影響了整個運動的思想定位,而且提供了一套新的話語。
從五四運動的整個過程來看,這是一場自發的社會革命,沒有一個有形的中心領導和決定一切,是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它充分體現了無政府主義反對政治組織,反對權威、無中心性,無限制性的特點。中國新青年不但不滿于黑暗的國家統治,也不滿于侵害個人日常生活的家庭權威,不滿于長者對幼者、男人對女人的壓迫、他們要打破的偶像,首先是窒息生機的日常存在的偶像,他們所體驗到的傳統的重負直接威脅到自身的生存,而所有這些,都可以從無政府主義那里獲得一種沖決的勇氣,一種前瞻的想象。可以說,正是無政府主義創造了一代激進文化。而今我們的學者仍在不斷攻擊五四的激進主義。其實激進主義不但是一種形態,重要的是一種思想,是一整個時代的靈魂。試圖抽掉激進主義,就喪失了五四的生命。
不能認為無政府主義只是破壞的、解構的,而沒有建設。無政府主義以自身的文化革命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促進基本社會結構的革命化。首先,無政府主義者把教育看作革命的基礎,但不是規范意義上的教育,而是改變生活習慣完善個人道德的教育,在教育過程中,將知識和勞動相結合,創造一個消滅勞動的根本差別的社會空間。
無政府主義者在五四期間的活動,保持了從文化革命到社會革命的一致性。這些活動,包括從法國的工讀運動到國內的工團活動,從北京大學的“進德會”到周作人發起的“新村運動”,還有形形色色的實驗,以一種社會革命的理想吸引廣大青年學生,開拓了現代勞工運動,一時成為潮流。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胡適都是不滿于無政府主義的,尤其胡適。
1922年5月13日,胡適和他的朋友共同發布了一份名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起草者胡適大約受了美國“好人政府協會”的思想影響,在宣言中重在宣傳“好人政府”,作為“政治改革目標”。顯然。這是同激進的反政府反權威的新文化運動相悖的。“好政府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正好是一副對子。
1930年代以后,中央集權統治形成,無政府主義作為洶涌一時的思想潮流已經沉落。這時,胡適和同留學歐美的一群朋友集體入閣從政,完成了對由他參與發動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作為一個獨立的、批判的、邊緣的知識分子身份的背叛。
一個世紀以來,在興起于五四前后紛紜眾多的思想中,恐怕沒有一種思想比無政府主義遭到更為無情的歪曲、詛咒、嘲笑和徹底抹殺的了,而深嵌其中的那些誘人的烏托邦圖象,以及一代踐行者的忘我開展的社會活動,是那般激蕩著一代青年的心!與此相反,在運動中暴露了知識分子的軟弱,奉行“好政府主義”,努力將自由批判的知識分子意向轉變為權力導向的胡適,卻被偶像化,尊為“中國自由主義之父”!
這種對比,不妨看作是五四這出悲壯劇落幕之后,繼續上演的一出短小的諧謔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