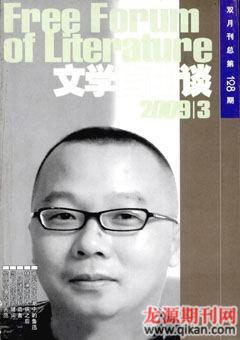倫理價值觀的失范
陳 沖
最近有幾件事,折騰得很是熱鬧:被指涉嫌抄襲的承德市作協主席劉英辭職;貴州省文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劉世杰被曝雇用槍手;新一輪張愛玲熱。這幾件事本身,都讓人覺得怪怪的,好像還應該再往深處想一想。這一想,讓我想到了倫理價值觀。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長期形成的各種倫理觀念。這些倫理觀念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線性的。同一件事,因角度的不同,常常會出現兩種以上的相互矛盾的倫理標準,于是就有了一個“誰管誰”的問題。一般來講,當然是低階位的倫理服從高階位的倫理,但在實際上,對于究竟哪個高哪個低,人們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就形成了不同的倫理價值觀。比如“孝”,本來是一個很高階的倫理,素有“百善孝為先”、“以孝治天下”一類說法。你的生命是父母給的嘛!可是一旦遇到“忠”,就要打折了。皇上要用你了,主子要用你了,老爸老媽的事只能后搭搭。“義”的階位稍低些,跟“孝”也比較容易“兩全”,問題是就怕碰上“大義”,一旦碰上了,就有“大義滅親”一說了。不過那個“大義”得弄對。當年兒子揭發、批斗老子,其實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那里面沒有大義,連小義都沒有。
高階位不是“高標準嚴要求”。像“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一種“高標準嚴要求”。如果某人真能一輩子一閃念都不曾閃過,自應受到尊崇,但這種人即便真有也不多,更何況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同樣應該受到尊重。但是,這兒又有一條底線,就是不能損人利己,也不能損人不利己。這種要求不高但卻是做人底線的倫理,也是一種高階位的倫理。
當作家,搞創作,有種種的寫作倫理。對于一個有追求、有出息的作家來說,創新意識只是起碼的要求。再降低一點,不模仿別人,不重復自己,應該不難做到。可是話說回來,一個初學者模仿模仿別人,一個江郎才盡的老作者重復重復自己,也不是多么嚴重的事。然而,不抄襲,不剽竊,卻是寫作倫理的底線。既然底線屬于高階位倫理,那么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作為越過這條底線的借口。
但是,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底線又經常會受到挑戰,尤其是受到某些話語強勢者的挑戰。郭敬明抄襲案就是一個彰明顯著的例子。
2003年末,莊羽將郭敬明告到法院,訴稱被告的《夢里花落知多少》抄襲了原告的《圈里圈外》。2006年6月,北京一中院做出終審判決。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挺郭的一方,主要是郭的粉絲,一直沒有停止鼓噪,一面支持“小四”,一面攻擊莊羽。終審判決出來以后,郭敬明被判定抄襲成立,被告方支付了罰款和精神撫慰金,但是卻拒絕道歉。這個“不道歉”激起了強烈的譴責聲,但是——至少據我的印象——仍然高不過郭的粉絲們的支持聲。然后,人們又看到了法律的邊界——法院可以判令侵權者道歉,但是無法強迫其道歉。這也對。道歉本質上屬于當事人的意愿表達,別人(包括法院)很難強迫,而且強迫出來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法院的辦法是,“逾期不履行,……法院將刊登本判決的主要內容,費用由郭敬明、春風文藝出版社承擔”。應該說,這是一種比強迫出來的假道歉更好的解決辦法,相當于明白昭示那個當事人沒有悔改之意,亦不失為對粉絲們的鼓噪一個有力的回答。
但是,最終決定天平向哪邊傾斜的,是另一家機構。就在這之后不久,這個拒絕道歉、沒有悔改之意的抄襲者,被接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此舉同樣明白地昭示出一種倫理價值觀。從協會的性質看,這應該是一種官方的倫理價值觀,或者說是具有實際社會影響力的倫理價值觀。雖然它既不能代替所有協會會員個人的倫理價值觀,也不能代替所有各省市協會的倫理價值觀,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家繼續譴責抄襲者,而新疆作協更是毫不含糊地將抄襲者遙遠開除出會。但是,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作協會員,還是作為地方機構的地方作協,其實際社會影響力都是無法與中國作協相比的。從倫理價值觀的角度講,一個沒有悔改之意的抄襲者照樣能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意味著抄襲行為已不再是寫作倫理的底線。如果抄襲者手里握有其他方面的籌碼,仍然可以就此做一番博弈,輸贏仍在兩可之間。郭敬明就賭贏了。遙遠則是賭輸了的例子;或者如有的論者所嘲諷,“很少有抄襲的作家像他(遙遠)這樣倒霉”。
在這樣的背景下,承德市作協主席劉英被指抄襲一事鬧騰得如此沸沸揚揚,就不免帶上了一種怪怪的味道。
這事兒咱們從后往前說。最近事情有了結果,有報道說:“承德作協前任主席劉英被指新作《草葉上晶瑩的露珠》涉嫌抄襲后,承德市文聯高度重視,責成相關人士開始核實詳情。調查人員分別對劉英、出版社等相關人士進行調查,文聯調查人員發現,《草葉上晶瑩的露珠》書中收錄的文章的確與原作者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承德市文聯的相關人士告訴記者,關于劉英是否抄襲其他作者文章,‘現在也不好說,因為文聯沒有權力對是否抄襲進行認定。”
看來承德市文聯不僅高度重視,而且高度慎重,所以在最后表態時,還記得他沒有“認定”權。美中不足的是,他忘了他實際上也沒有“調查”權。當然,這里所說的“調查”權、“認定”權,都是法律意義上的。如果只從文學的意義上說,是不是抄襲其實很簡單,因為《草葉》是本散文集,不像小說還可以抄情節、抄人物關系,散文要抄,只能抄文字,所以只要把相關的文字兩相對照,應該一目了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劉英的抄襲與否是明擺著的,用不著拿“有很多相似之處”打馬虎眼。至于確定是抄襲之后,數量有多少,性質嚴重到什么程度,也不難做出文學上的考量。
所以,這件事的怪異之處,就在于它本來沒有涉及訴訟,卻偏要拉開一副做大的架子,去做法律意義上的考量。這可真是一道奇怪的風景線:按報道中開列的名錄,被抄襲者人數眾多,健在者亦有多人,他們的作品被人抄襲,卻沒有一個人起而維權,倒是一些旁觀者在那里義憤填膺抱打不平。那么,你既然想就這事兒抱打不平,就理應了解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實情吧?像承德這樣的“廳級”,它的“市作家協會”是怎么回事,該協會的會員是什么樣的作家,它的協會主席是哪一級干部,是怎樣的“文壇掌門人”,又是怎樣產生的,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事實上,我看到過一篇文字,其作者說曾在網上將“劉英”百度了一下,發現在有限的幾個條目中,除了說到她是承德市作協主席,開過什么會,在會上講了什么話,并未涉及她有什么作品。可惜,該作者仍然只是將這些當作挖苦的材料,卻沒有想一想,雖然抄襲確實是很不光彩的事,但對于這樣一個沒什么像樣作品行世的作者,有必要鬧騰得如此沸沸揚揚嗎?何況那本《草葉》根本不是正版書,只是買一個書號就可以“出版”十本那種。這種書根本進入不了市場,更賺不了錢。從常理上講,確確實實沒什么值得鬧騰的。如果說這件事還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在拒絕道歉、毫無悔意的抄襲者郭敬明被接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之后,人們既然對大抄郭敬明無可奈何,就只好拿劉英這樣的小抄來足足地顯示一下自己的正義感了。
劉世杰是貴州省文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這個職位應是副廳級。他在一部“小說”上署了名,而且是惟一作者,但這部“小說”他沒寫過一個字,甚至沒抄過一個字,完全是“坐享其成”。事情好像挺明白,但是從法律的意義上說它是個什么“案件”,就難說了。如果讓法庭來判,未必多么難判,問題是和前一件事一樣,沒有任何一個具有訴訟主體資格的人進行告訴。為什么會這樣呢?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這個“小說”是由“同名電視劇”改編的。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是一個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你不署小說原作者的名,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一個由電視劇改編的“小說”,署不署原編劇的名,很可能就不是“問題”,因為它有很多個編劇,而這些編劇們沒人把那個據以改編為“小說”的劇本當作自己的作品,只認為自己干了其中派給自己的那份活兒,并且已經得到了該得的報酬。你看在那么多的議論紛紛、紛紛議論中,竟然沒有一個人、一句話提到誰才是這部“小說”的無可爭議的作者!有報道說,“書的真正作者是女詩人言美芳”,也就是那位所謂被雇用的槍手。雖然我對言女士的很多方面都極為同情,但我仍然認為她只是個寫作者而不是創作者,最多是個改編者。說白了,我們面對的是一部從流水線上“組裝”出來的“小說”,一部沒有一個真正的創作者的“小說”。如果有誰真想有意義地鬧騰鬧騰,我覺得這才是真正值得鬧騰一下的地方。當一部電視劇可以有很多編劇,卻沒有一個編劇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時,當一部這樣的電視劇又被書商找來寫手改編為“小說”,因而這個“小說”已經不存在確定的作者,以至電視劇的制作方覺得自己有權“指定”誰是作者時,我覺得——至少是在這部“小說”中——確實是“文學已經死了”。文學都死了,誰是作者還有什么可鬧騰的?
張愛玲熱是同一個問題的另一面。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有人喜歡、很喜歡,有人不喜歡、很不喜歡,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張愛玲熱”——總是隔幾年“熱”一次,隔幾年又“熱”一次,每次都“熱”不了多久,慢慢涼下來,然后就有人再把它炒熱。依我看,一次又一次的張愛玲熱,并不是真正喜歡她的作品的人炒起來的。張愛玲是個特點突出的作家,這些特點決定了她的價值,決定了她的局限,也決定了哪些人會喜歡她的小說,而這些人手里并不握有足夠的公共資源,不具有把她炒熱的能力。既有動機也有能力的,是那些擁有話語權的人,是那些某種意義上的“知識精英”。兩年前,借電影《色·戒》上映,一輪新的張愛玲熱卷地而來。它幾乎成為近二十年以來最熱的一次張愛玲熱,可惜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像炒家們估計的那么健忘,結果大熱變成了大涼。兩年以后,更新一輪的張愛玲熱再次卷地而來,這次借助的是一部叫《小團圓》的長篇小說。跟著摻和的還有一部從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傾城之戀》。摻和而已,從三萬字的小說變成了36集的電視劇,里面還有多少東西姓張,已經是很難說清的事了。實際上,一次又一次的張愛玲熱,本質上決不是對她早年那些作品的關注。那些能“代表”她、決定她的文學地位的作品,并沒有什么特別復雜的地方,它們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哪些不足,缺少什么,如果中國的文學批評界到今天還搞不清楚,那么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沒一個人還配活著。真正在那里來回“炒”的,不是張的這些作品,而是張本人的“行狀”,說白了就是她和胡蘭成那點事,最多加上那點事在她后期的作品里變成了什么樣子,剩下了一些什么樣的渣子。炒《色·戒》時如此,炒《小團圓》時仍然如此。炒《色·戒》時,《南方周末》發表了梁文道的《焉能辨我是忠奸》(2007年11月15日),它首先批評“中國人學歷史就像小孩看戲”,除了忠臣和奸賊,“再無第三條路”。然后引用德國在二戰后清理“通敵者”的故事,譴責“一些沒有什么天分”的人,借“狠批幾位造詣非凡的大師曾經出任納粹偽職”,“心態很陰暗”地“取而代之”。接著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國史學家的話,認為“曾經幫侵華日軍指認出藏匿于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的人究竟是好是壞,也“很難判定”,因為這樣做“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經過這樣一番彎彎繞,真是“焉能辨忠奸”了。連忠與奸都不可辨了,還有什么倫理價值觀可言?最近炒《小團圓》,《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對陳子善的訪談《張愛玲也許不高興》(2009年3月26日),說“張愛玲被胡蘭成連累了”,并質問道:“這是什么邏輯?你說漢奸的老婆不能紀念,那漢奸的哥哥能不能紀念,魯迅是漢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蘭成更大的漢奸,怎么可以開研討會?”做此質問,居然還提到邏輯。作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先生真的看不出這兩者之間毫無可比性?比如,魯迅在周作人當漢奸之前就已去世,而張愛玲是在胡蘭成正當著漢奸時成為他老婆的?
在對《小團圓》的炒作中,經常引用張愛玲自己的一句話:“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其實這正是問題癥結之所在,也正是張愛玲的一個死結。她在為《色·戒》辯解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說到王佳芝行為的心理依據時,用了很長的篇幅去強調王佳芝對“表演”的癡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鉤,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她還設置了種種其他的依據,例如“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說成是“羊毛玩票”,并非專業的特工;甚至還有個“遠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謀刺未成卻枉失了童貞,以至“有點心理變態”。總之,張愛玲為了使王佳芝的行為有合理的解釋,什么理由都可以用,連“心理變態”都用上了,惟獨鐵嘴鋼牙死也不往“愛國動機”上說。原因很簡單,一旦確立了王佳芝引誘易先生是出于愛國,那么最后的“捉放曹”就是叛國。“冰雪聰明”的張愛玲當然不會干這種傻事。說到底,《色·戒》只是一篇回避了國家立場的小說。它并沒有為漢奸辯護,更沒有歌頌漢奸。那不是張愛玲的動機。張愛玲的動機僅僅在于——為一個女人愛上一個漢奸尋找種種與國家立場無關的理由。
她不是不知道,在面對日本侵略者時,國家立場是“大義”,是倫理底線。她的刻意回避,恰恰證明她知道。這是她的態度,是她的選擇。圍繞張愛玲熱所出現的爭論,實質上就是對她的這種選擇和態度,我們應持什么態度。而這些不同態度的分水嶺,就在于倫理價值觀中的倫理底線有沒有剛性。這是一個是與非的問題,但背后卻是一個利與害的問題。強調倫理底線的剛性,對某些人顯然不利;而對這種剛性的削弱乃至抹殺,則明顯有利。
如果要找個人來和張愛玲比一比,為什么不選郁達夫?即便對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做出最高的估價,也高不過郁達夫——再退一步,高不過很多吧?郁達夫的個人行狀并非完璧無瑕,但在國難當頭之際,他的國家立場毫不含糊,決非張愛玲那種含糊、回避可比。但是,我們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張愛玲熱,郁達夫熱卻是一回都沒有。這叫什么?這就叫倫理價值觀失范。在人類社會中,這種失范必定會帶來某種普遍性的反應,所以就有了張愛玲熱,就有了中國作家協會接納郭敬明入會,就有了拿大抄無可奈何便拿小抄表示義憤,就有了認為自己有權指定小說作者的電視劇制作方,就有了幾個人便能代表“中國”來“不高興”,就有了——當然,就有了余含淚、王幸福、范跑跑、孫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