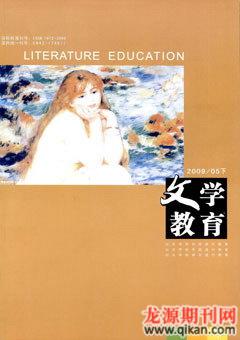古典詩詞佳句句法探微
趙明山
西方結構主義詩論認為,詩歌語言是對常規語言的系統違反,詩歌手法在總體上顯出一種普遍的反常規特征。詩歌較散文所受語言限制較多,而詩歌語言的限制越多,它表達的內容越豐富。詩歌在語言上與散文有明顯不同,這突出表現在散文中必不可少的虛詞上。如“之”“乎”“者”“也”等,而詩中能省略的也不止于虛詞。事實上一些通常字的大量精減,也絲毫不讓人感到不方便和不自然,相反的卻更集中、更靈活、更典型。這樣一種省略,也就是對常規語言規律的違反,其結果怎樣呢?是詩歌語言一方面更加整飭了、鏗鏘了;另一方面則更加凝練、雋永了。先舉幾個例子: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
沒有一個動詞形容詞,全是名詞的組合,類似一些詞組,然而它卻比兩個散文的單句能傳達更多的意思。梅堯臣論作詩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覺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后一句并列三樂器,則滿堂絲竹,急管繁弦如聞。離別的情意渲染得多么濃厚。
這一詩歌語言上的特點,在以下一首著名的元人小令中達到極致: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馬致遠《天凈沙》)
這支曲子前三句共寫九樣景物,其間似乎沒有什么邏輯聯系。然而,由于詞曲結構的規定性起作用,這些名詞組合在一起,就能產生超越常規的語言功效,組成一幅鮮明的圖畫。秋原的景色、旅人的寂寞悲涼,全都有力地表現出來了。
以少勝多,似乎是詩詞語言的一種特質。不懂這一層,有些看上去簡單的詩句,意思也不好懂: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李白《行路難》)
第一句不是說“大道難于上青天”,而是說“對旁人來說是康莊大道,對我來說則難如上青天”,其間有多少省略!
詞是由詞素構成的,一經約定俗成,便不能隨意顛倒或拆散。但在詩人,往往不予理會:
慨當以慷,幽思難忘。(曹操《短歌行》)
這里“慷慨”二字不但顛倒而且拆散了。
露從今夜自,月是故鄉明。(杜甫《月夜憶舍弟》)
“白露”這個節氣名被拆散顛倒了,然而景色卻宛如畫出,句式也因對仗更加好看而動聽了。
再從詞語的搭配看詩詞對散文語言常規的明顯違反。散文的遣詞造句,必須根據詞義考慮搭配關系。這是一種語言常規。而在詩詞,結構因素(如平仄,押韻)有更高的意義,以致在與語言常規發生沖突時,后者往往妥協;而具有創造天賦的詩人們,又得因利乘便,大晨才思,“爭價一字之巧,爭競一韻之奇”,寫成的詩句以其富于創造性為人喜聞樂道: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無題》)
在散文中,“相思”怎樣以尺寸計量呢。“灰”也不能與“一寸”這個數量詞搭配。然而李商隱這樣寫了,千古以來讀者不但沒有異議,而且還十分理解和欣賞它包含的痛切意味。
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古代詩詞在句法上也不斷地打破散文常規,漸成規律,最為特殊的便是詩詞的對仗句。散文句法接近口語,而詩詞的對仗純出于人工。因為有對仗這種形式,使得語言的濃縮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名豈文章著”一句單獨看是不易理解的,然而由于有“官應老病休”的對句,兩相比對,加以揣摩,便知是“文章豈著名,老病應休官”之意。
正是由于對仗句式的大量存在,導致古代詩詞常用的一種能使詩句既精煉又可解的修辭手法——互文產生。如漢樂府《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
一般讀者可能認為戰爭始于城南,終于郭北,頗覺牽強,就是不知互文的誤會。其實兩旬是說:或戰死于城南,或戰死于郭北。極言戰死者之多。又如:
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沈儉期《雜詩》)
“昨夜情”也屬于少婦。“今春意”也屬于良人,夫婦分擔,也是互文。單個詩句有“當句對”式。往往也用這種手法。例如“秦時明月漢時關”,將關、月分屬秦、漢,是互文,其意義即李白詩所謂:“秦家筑城避胡處,漢家猶有烽煙燃。”
駢句成為近體詩的主要句型。詩人逐漸從必然求得自由,奇跡便逐步發生,又非互文可以道盡: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泣春。(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
初次一讀,說:“這是以云霞出海寫曙光之美,以梅柳渡江形容春天之來呢”,反復玩味,原來曙從東至,而東方是海,陽光未照大地時先映紅海上云彩,這就是霞,所以云霞出海正是報道著曙的降臨;天氣變暖是由南往北,最早顯示春天消息的梅花、柳葉,也似乎是渡江北上的。這兩層意思,詩人各選五個字,按格律要求予以組合,便以最少的文字取得了極大的效果。
應當專門指出的是詩詞中倒裝和錯位的語序大量存在,也就是違反散文語序成為一種普遍的規律,不了解這一點,有些詩句便難通解。如;
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王維《隴西行》)
“蓋云走馬時一轡頭走十里。才一揚鞭不覺已走到半路了。寫其心頭火急,走馬迅速如風。”(金圣嘆語)如按散文語法,解作走五里才揚一次鞭,就大錯特錯了。同樣道理,“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是說:憐月光而滅燭,覺露滋而披衣。“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改寫以散文語法應是“暗泉流于石壁,秋露滴在草根”。“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后一句是說:“溪水直流到門前”。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首句云: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有人認為若“城闕”為長安則不通,長安怎能輔“三秦”呢?必得理解為成都才對。這也是不知倒裝為詩句語序之常例而發的不通之論。其實這兩句都是倒裝:長安以三秦為輔,望五津只風煙一片。這是一句之中語序倒置的例子。還有兩句倒置的例子: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意思是蘭澤雖多芳草,而涉江只采芙蓉。芙蓉是雙關語,寓夫容。
詩歌語言對常規的違反,有一個很顯著的后果便是它使得詩歌語言的聲音與文字的可理解性變得朦朧起來。有心的詩人也就據此故意造成雙關或多義的模糊語言,為詩詞增添了不少意趣,以致讀者每一遍閱讀,都能從中發現新的東西,獲得不同的審美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