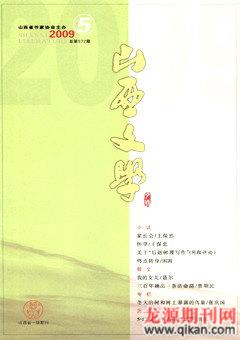作家氣質、“底層”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李云雷
我只見過一次王保忠,但留下的印象卻較為深刻。去年9月我去山西大同,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見到了保忠,在座的還有王祥夫先生,我們在一起喝了一場酒。我覺得他人很樸實本分,但又有著一種內秀,有一種內在的聰明或“狡黠”,比如喝酒時,他總是會想著法子勸你多喝點,喝高興點,而他自己卻按兵不動,辦法呢看上去都很誠懇,讓你很難拒絕。聯系到他的一些作品,我覺得很“像”王保忠寫的,也就是說,他的小說與他本人的氣質、性格有一種內在的契合,一方面他寫得很樸實本分,有著濃郁的鄉土氣息,甚至讓人想到趙樹理、馬烽等前輩作家的“山藥蛋派”傳統,但另一方面,他的小說中又有靈動、精巧的地方,常常能給人以意料之外的驚喜。而在這兩個部分中,樸實本分是基礎,是底色,而靈動精巧則是在其上生發出來的,或許可以說是人生智慧的結晶。就我的接觸與閱讀而言,無論是為人還是作文,保忠都給我以這樣的印象。
我記得在一本書上看到過,太老實的人寫不出好小說,因為老實人是有什么說什么,而小說的結構、敘事、語言卻需要技巧與機智,“文似看山不喜平”,如果只是竹筒倒豆子似的傾倒而出,在技術或藝術的角度上,很難說是好小說。但另一方面,過于聰明的人好像也寫不出好小說,在我們這個時代,“聰明人”早就不從事寫作了,即使還有在寫作的,他們也大多或者炫弄技巧,或者追蹤文壇最新的時髦,有聰明而無“智慧”,難以寫出真正的好作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一種聰明的“笨人”的事業,或者說是一種笨拙的聰明人的事業。另一方面,在我的理解中,就文學與世界的關系而言,文學是一種逃避,也是一種進取,是以進取為姿態的逃避,也是一種貌似逃避的進取。它不追求世俗的繁華與熱鬧,而是返過身來,與世界拉開一定的距離,以觀察、思考的方式,以藝術的方式,在內心與世界之間建立起一種聯系。它需要看透世界的能力與智慧,需要無所用心的“用心”,需要融人世俗生活之中而又超越于其上,需要看似舍棄的執著,或者看似執著的舍棄。所以,文學是一種精神的事業,一種寂寞的事業,也是一種執著的事業。而只有少數大家,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而文學的迷人之處,或許也正在這里。我想,王保忠置身于一個小縣城中,置身于一個文學不再輝煌的時代,而仍然癡迷于文學,或許也正是感覺到了文學的這一魅力。
在王保忠的小說集《塵根》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關注的主要對象是農村,并且他將自己的寫作自覺地歸屬于“底層文學”。的確,他筆下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他關注他們的困窘、尷尬的生活狀態,但又從中發現了溫暖、質樸的東西,在《奶香》、《前夫》等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主人公的生活雖然貧窮,但他們卻都有著一顆寬容、善良的心,而正是這些使他們獲得了內心的安穩。作者也善于捕捉生活中出現的新質素,在《美元》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張美元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又怎樣與一個少女的夢想糾合在一起,而這只是新的跨國交流帶來的故事;在《天大的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城市里做“雞”的妻子回到村里后,對丈夫的內心和鄉村的倫理秩序造成了怎樣的沖擊,而丈夫又以怎樣的態度包容、寬恕了妻子的行為,這是一篇讀來令人心酸的文字。王保忠的筆觸不僅把握住了主人公的生活,而且深入到了他們的內心,從“小事”中寫出了人物的生活態度與生活理想,而正是這些,表現了底層人物不屈的生命力。
在當前的“底層文學”創作中,不少人將描寫農民、工人、農民工的小說視為“底層文學”,這在某種程度上雖無大錯,但在我看來卻是不甚確切的。在我的理解中,“底層”是一種結構性、相對性的概念,它只有在一種結構的對比中才具有意義。在一種整體的社會結構中,農民、工人、農民工處于“底層”,但在他們的內部,也存在“底層”與否的區分,同樣在中層或者上層中,也存在相對的“底層”。所以所謂的“底層”,不只是一種大的社會分層的概念,也是一種微觀的“生活政治”。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底層文學”關注的是受到歧視與壓迫的階級或群體,但我們同樣不排除對其他階級中受到壓制的階層或個人的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底層文學”視為對所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秩序的批判與挑戰。
在王保忠的小說新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創作上的新進展,他的題材不再限于農村,而擴展到了新的領域。在《家長會》中,王保忠抓住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那就是煤礦老板這樣一個“新階層”的崛起,對“正常”的社會秩序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三個層面表現出來,一是對私立學校校長湯河的影響;二是對學校教師葉娜的影響;三是對正常教學秩序的影響,這尤其表現在對“家長會”的擾亂上。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小小校園中,“新階層”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至于在其他社會領域中會有什么影響,作者沒有展開,但我們也可以想象得到。對于以煤礦老板余黑子為代表的“新階層”,小說中對他們暴發戶式的做派與心態做了嘲諷式的描述,也流露出了一種隱隱的憂慮,結尾處更通過一個意外事件,揭示了余黑子“崛起”的秘密及其下場,這雖然只是一個個案,但對于我們理解這個“新階層”,及其在社會上起到的作用和造成的沖擊,卻是十分重要的。而小說從校長湯河這個“小人物”的角度落墨,更增添了故事的曲折性。
相比較而言,中篇小說《筆桿子》似乎就有些傳統,我們可以在“新寫實小說”、“官場小說”中清晰地辨識出它的脈絡,這篇小說向我們展示出,在官場文化結構中,幾個小知識分子如何為了個人的“前途”而相互傾軋,作者對主要人物的心理波動和他們之間的關系做了細致的描寫,揭示了其背后的猥瑣、可憐與辛酸,在小說的最后,作者讓小說的主人公毅然出走(并在敘述者的夢中飛了起來),是對現實的一種批判,但在小說的內在邏輯中,卻并沒有這種出走的可能,我們可以視為作者對這樣一個“小世界”的拒絕。這篇小說的好處在于,對于具有中國特色的官場文化及置身其中的“筆桿子”,有一種細致入微的刻畫,但正如“新寫實小說”一樣,作者對筆下的小人物有著更多的同情與體認,而在小說的邏輯中,卻看不到一種與“官場文化”相抗衡的精神力量,換一種說法是批判性不夠強。這也許是作品的一個遺憾。但是,只要我們想想他的底層寫作立場或姿態,以及他慣于以平等的視角對待小說里的人物,這一切就不難理解了。從這個角度講,《筆桿子》里的幾個被官場文化同化了的小知識分子說到底也處于底層,有其令人厭惡的一面,也有其辛酸無奈的一面。
王保忠在“創作談”中,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他寫作的源頭之一,他滿懷深情地回憶起自己最初閱讀《罪與罰》的情景,并在文章中梳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幾個方面的影響:一個作家要有感知社會和進入時代的能力;要有進人心靈,撬開所寫人物內心隱秘的能力;要有撫慰人的靈魂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我很喜歡的作家,看到保忠的創作談,我有一種遇到同好者的欣喜,但仔細一想,我發現我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樣。在我的理解中,《罪與罰》最核心的問題并不是“底層”或“苦難”,而是一個時代中人的“精神”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迷人之處,在于他能夠進入時代最核心的精神問題,并在一種宏大而開闊的思想視野中,以自己杰出的藝術才能,通過反復的爭論、思辨或追問,表達出一種矛盾而又有傾向性的思想立場,這也就是巴赫金所說的“復調”與“對話”。譬如在《罪與罰》中,他所面對的便是一種虛無主義,或者說是一種理性至上主義,這也是一個現代性問題。他為這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有抱負的人是否可以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而犧牲掉一個毫無用處甚至危害別人的人”?他的回答是“否”。這個看似簡單的回答,卻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多么巨大的波瀾,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內心痛苦的掙扎,直到小說的最后一頁,主人公才勉強接受了這個答案。而在這種掙扎之中,則隱含著不同價值觀的激烈沖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卓越之處,便在于他能抓住其中最核心的精神命題,并在沖突之中展開自己的思想、確定自己的立場,而在這背后,則需要杰出的思想能力和藝術表現力。
此處所談的,看似與保忠的具體創作無關,其實可以視為對他的一種“批評”,或者說對他提出了一種更高的要求。當然,以經典作家所達到的高度來期待王保忠,未免有些強人所難,但既然選擇了文學,既然喜愛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似乎也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至少也可以“取法乎上,可得其中”吧。
責任編輯陳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