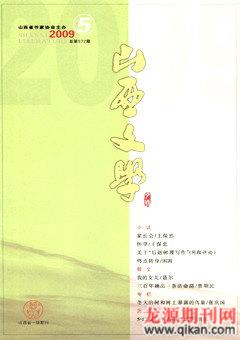在延續中尋求新的突破
吳秉杰
去年,參加了《黃河》雜志為王保忠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研討會。給我的印象是,保忠為人沉著、穩重、謙遜而又自信,他的小說同樣的內斂、含蓄,寫農民與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工,筆下的人物大抵都是有情有義的。保忠說,他要寫底層,寫小人物,不回避生活中真實、嚴酷的一面,同時創作也要給人以溫暖和愛心。我覺得,并不是作家刻意地要給讀者什么,而是作家心中有溫暖,能在這個世界、在底層人物生活中感覺到這種暖意,他才能在創作中反映出來。這猶如“鏡與燈”的關系。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保忠的一些小說,即便選擇了嚴酷的背景,仍能在作品里找到亮色找到溫暖的畫面。同時,在一個價值觀念多元化和價值沖突的時代,他努力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可靠的、讓人信賴的東西,小說的美感由此而來。另外,他小說中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均描寫得“有情有義”,譬如《塵根》這本集子中的《奶香》、《前夫》、《天大的事》;而這種“情”和“義”既體現人性,蘊有溫暖,實際上又是區別出了和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
最近,保忠又新創作了《尋找馬蘭花》、《家長會》和《筆桿子》等幾篇小說。他說:題材上稍有拓展,讓我看看,多批評批評。題材確實是不同了。它們寫的都是知識分子,小說主人公是教師或公務員。延續了王保忠小說個性或追求的是:第一,作品里仍然沒有寫什么奸惡之徒。或許是因為他意識到,從來便不是個別的“惡人”決定了人們的不幸,無論過去和現在,在任何時代“好人”總是占多數,因而也可以說是某種集體的機制,決定了我們的命運。第二,兩篇小說還是保持了敘事和心理描寫結合并融為一體的特點。這可能是文學形象塑造和其他形象塑造(譬如影視形象)最主要的區分,也是由人心開掘通向人性開掘的唯一途徑。第三,和第一點相聯系,我認為它依然是保持著一種文化審視的眼光。當然,隨著小說主人公身份的不同,王保忠的創作在延續中又有發展變化。
《家長會》表現了知識分子在金錢力量面前的尷尬、無奈、動搖或猶豫,總之,再也不能保持那超然獨立的地位了。金錢的力量是剛性的,是現代社會中誰也無法漠視的一種物質力量;這就像王保忠在他的另一部中篇《筆桿子》中寫到的地位和權勢一樣;注意,作為一種社會的“客觀存在”,社會地位和權勢同樣是物質性的。知識分子精神于是面臨著強大的社會存在的考驗。《家長會》中的“家長會”最后也沒有開,至少是小說中沒有描寫,但余黑子應諾的一百噸煤是送來了。煤礦又出了礦難,余黑子“出事”被抓起來了。博人學校女教師“校花”葉娜又離開了學校。一切都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除了湯河校長的猶豫、尷尬,葉娜的“個人隱私”,她和余黑子之間的關系,以及她為什么要離開這遠近聞名的博人學校,都隱蔽在敘事的背后,給人留下了較大的想象空間。精神與物質的矛盾沖突只顯示出了冰山一角,或許這也反映了短篇的藝術要求。我曾經說過,王保忠有出色的短篇寫作能力,他的相當一部分篇什都很好地體現了這一文體的藝術要求——節制、含蓄——這是短篇的境界、價值實現途徑和基本特征,也是他小說的一個特點。
我更感興趣的是他的中篇《筆桿子》,知識分子的處境和表現寫得更為充分。保忠不愿意說他寫的這一作品屬于“官場小說”,雖然它寫的是一個區委大院,但它也確實不同于那些我們已見慣了的表達正義立場、善惡沖突,最終要落實到反腐敗的那種官場小說。它寫的是一批機關干部、小公務員,可以說著重抒寫的是一種機關文化。這使我想起了劉震云早年的中篇《官人》、《單位》等,還有他的成名作《新兵連》,揭露矛盾,可最終揭示的還是一種軍營文化。現在創作普遍注重文化開掘,那是因為文化既包括物質方面,又包括精神方面,并把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轉換了主體的角度。也就是人的創造和生成的角度。我想《筆桿子》同樣是如此。王保忠所寫的其實是我們所熟悉的一些內容,無非是小公務員希望領導賞識,獲得晉升的機會,伴隨著小動作,小心眼,小心謹慎,看眼色行事,曲意逢迎等等。雖然作品中人物性格稟賦不同,可人生目標則是一致的。為此還不惜送禮,替領導拖地板、搞衛生,乃至在提拔干部的關鍵時刻“冒名”寫告狀信等,雖讓人“惡心”,卻并不特別讓人憎恨。其原因,這同樣是因為無奈。在現行體制下,“升官”對于公務員來說已別無選擇地成了一種價值的源泉,意味著待遇、社會地位、社會肯定。它使得作品中的這些“小人物”,在“機關”(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之為“官場”)的文化結構中,面對地位和權勢,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卑微的靈魂。我注意到小說取名為“筆桿子”,意味著它沒有主體性,只是工具。還有,保忠給小說主人公取名叫宋詞,這其中所隱喻的傳統文化與他的“筆桿子”身份是否構成了一種反諷?當然,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并不全是如小說所寫的那一群人,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現有文化結構中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也有一些人文知識分子有著自己獨立的事業和精神的追求,更不用說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與人文知識分子的區別了。但目前看,“單位”和“機關”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有著某種普遍的束縛。
《筆桿子》這部中篇的優點,還在于那體貼入微的心理描寫始終伴隨著主人公,于是便留下了這一段讓人難忘的生命的軌跡。之所以寫得這么細致入微,說到底還與保忠的小說創作理念有關,理念決定方法、敘述和作品的風貌,這一點在他的創作談里已談得很清楚。他說:一個作家要有進人心靈,撬開所寫人物內心隱秘的能力。于是我們看到作者在刻畫一種瑣碎、平庸的“機關日常生活圖景”的同時,更凸顯了一種隱秘而斑駁的心理圖景:清高與卑瑣,內省與自責,身不由己的沉淪與向上向善的自我掙扎,等等。小說結尾,宋詞選擇了“逃離”,雖然我覺得這一處理似有落入俗套之嫌,但這也許看作是主人公對人格中某種黑暗因素的否定,并渴望自我解救的一種方式吧。
寫機關、學校與寫農村是不同的,寫知識分子與寫農民同樣有所區別,這可以視為是保忠創作的一種明顯的發展。與此相應的變化是小說詩性的、抒情的成分削弱了,敘事得到了強化,不是以朦朧的感覺、某種空靈剔透的意象取勝,以情節、細節的敘述把握取勝,古典的傳統的情調中不可避免地羼入了現代文化成分,換句話說,這是一次向復雜性的進軍。保忠在自己的創作談中說,他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作家要做一個有“信仰”的人,我很贊同這一點。保忠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只是剛剛開始。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和寫自己眼中的復雜世界,那需要一雙有信仰的目光,人性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設的目光,我相信,保忠的創作,一定會迎來一次新的突破。
責任編輯陳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