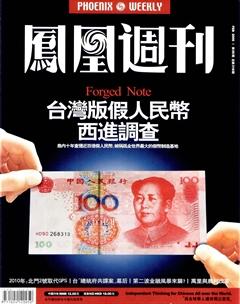故宮人的命運和鄉(xiāng)愁
吳曉東

高仁俊到臺灣時只帶了一身衣服,索予明還沒來得及安頓好老母親就上了船,那志良到臺灣后勸說大家不要買木質(zhì)家具,以免回北京時扔了可惜。李濟一直盼著早點回安陽繼續(xù)新的發(fā)掘,莊嚴在去世前還在和小兒子莊靈念叨自己終生的遺憾是沒能把這些寶貝再帶回北京去……
60年過去了,曾經(jīng)伴隨著文物來到臺灣的那些文物專家,大多數(shù)都已離開人世。60年前幾乎所有人在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都以為這里只是他們短暫停留的一站,可他們從此再也沒能踏上祖國大陸的土地。
在拍攝紀錄片《臺北故宮》的日子里,一幕又一幕的戲劇人生從歷史的深處被打撈出來。在這些故事里,國家的命運、文物的命運和人的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令人嘆息,更催人深思
莊嚴:一直帶在身邊的,只有國寶和孩子
1948年12月21日,712個裝有來自故宮博物院等五個機構(gòu)頂級國寶的神秘箱子,靜靜地躺在南京下關(guān)碼頭上,等待著離開這個港口。不久,國民黨海軍“中鼎”號運輸艦悄然駛進碼頭,它將執(zhí)行一個極為秘密而特殊的使命,終點是臺灣島的基隆港。
跟隨這些文物一同前往臺灣的一共有9個人,這其中包括一對夫婦,他們是來自故宮博物院的莊嚴和申若俠。故宮文物走到哪里,他們就跟到哪里。十幾年跟隨文物大遷徙的動蕩日子里,他們的家已經(jīng)簡化成了幾個包裹,一直帶在身邊的,只有國寶和孩子。
“七七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遷大后方。莊嚴押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shù)展覽會”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學(xué)圖書館暫存,再從長沙經(jīng)廣西桂林到貴州,接著到四川,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再輾轉(zhuǎn)回南京。這期間,莊嚴的妻子及三個未成年的兒子跟著他一路奔波,他的四兒子莊靈就出生在貴陽。
當(dāng)年坐上“中鼎”號和父母、哥哥們押運著第一批文物去基隆的時候,莊靈只有10歲,但他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飄洋過海的經(jīng)歷。那幾天海面上天氣陰沉,風(fēng)強浪高,壞了一個推進器的“中鼎”號在海中前進,左右前后上下?lián)u晃。人就睡在由文物箱子堆成的平臺頂上,上面鋪蓋著油布,人像被不斷搖篩的煤球。申若俠又因暈船吐了一路,就這樣熬了四五天后,才終于到達基隆港
莊靈現(xiàn)在住在臺北郊外的觀音山上已經(jīng)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和他父親莊嚴一起第一批運送文物到臺灣的大陸文物專家,現(xiàn)已全部過世,隨著時間的日益久遠,這段歷史已經(jīng)開始漸漸蒙上了灰塵,而對于生在文物中長在文物中的莊靈來說,中國歷史上這段舉世矚目的文物大遷徙,勾畫出來的正是他們家兩代人的命運軌跡,那些歲月早已深深沉淀在自己的記憶里。
據(jù)莊靈回憶,莊嚴在臺灣一直牽掛著石鼓的事。當(dāng)年文物從北京故宮南遷,莊嚴奉命負責(zé)把安定門內(nèi)國子監(jiān)兩廡的秦代石鼓包裹裝箱,和故宮文物一起南運。莊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終于完成這項艱巨的包裝工程。這批石鼓自從戰(zhàn)前在北平裝箱運出,一直到運回南京,20多年來始終不曾開箱看過。由于石鼓太沉,沒能帶去臺灣留在了大陸,莊嚴在臺灣懸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寢食不安”。
許多年后,大兒子莊申從香港帶來消息說,有一本專談中國藝術(shù)的書《遐庵談藝錄》中曾經(jīng)談到石鼓后來開箱的情形:“1956年故宮有設(shè)置銘刻館之議,因約同人于英華殿開箱檢視有無損壞,余與焉。啟箱則氈棉包裹多重,原石絲毫無損……”這個消息讓莊嚴十分激動,他后來在《山堂清話》書中寫道:“當(dāng)我看完這段文字之后,不僅如釋重負,內(nèi)心更為之狂喜不已,40多年來對于這批國寶之運遷與維護,終于得到圓滿的交代。”
1980年,82歲的莊嚴因腸癌病逝臺北。此前,莊嚴常對兒子們說,他此生有兩件憾事: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在臺灣重新聚首。莊嚴在《山堂清話》中的《我與中秋、伯遠二帖的一段緣》中曾寫到過,當(dāng)時第一批文物南遷之前,郭葆昌邀請馬衡和莊嚴等人到他家吃飯,拿出了珍藏的中秋,伯遠二帖供大家觀賞。那時郭葆昌曾當(dāng)來客及他的兒子郭昭俊的面說,在他百年之后,把這二希帖無條件歸還故宮,讓快雪、中秋、伯遠“三希”再聚一堂。后來《快雪時晴帖》隨大陸文物遷臺,郭昭俊曾帶著中秋、伯遠二帖去臺灣履行他父親生前宏愿,但希望能得到一些報酬。但國民黨政府當(dāng)時資金緊缺,郭昭俊于是攜此二帖遠去香港,后來轉(zhuǎn)售給國家。“三希”至今仍沒能聚首,這個遺憾讓莊嚴耿耿于懷。
而莊嚴第二個最大的遺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親自帶著這批遷臺的故宮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宮,回到他成長求學(xué)、立業(yè)成家、浸潤深耕歷代中國文化藝術(shù)的故鄉(xiāng)。他自己的一首小詩反映了他的復(fù)雜心境:“我與青山結(jié)宿緣,巖居招隱四十年。此日披圖重太息,何時歸臥故鄉(xiāng)山。”
李濟: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
1948年的冬天,和莊嚴夫婦一起搭乘“中鼎”號去臺灣基隆的,還有中國考古學(xué)界的開創(chuàng)者、安陽殷墟考古發(fā)現(xiàn)第一人李濟。年過半百的李濟帶著包括毛公鼎在內(nèi)的珍貴文物登上駛往大海的輪船(由于時間倉促,司母戊鼎因為太重,沒有被運上飛機,最后留在了南京機場),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故鄉(xiāng)。在遠離故鄉(xiāng)的日子里,李濟常常是在悠遠的琴聲中思念祖國。
80年前,由李濟率領(lǐng)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河南安陽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正當(dāng)他們?yōu)樽约旱某煽兣d奮不已時,抗戰(zhàn)的爆發(fā)改變了一切。1937年,在故宮文物遷出北京4年之后,考古組在安陽的發(fā)掘不得不暫停。隨后,從安陽發(fā)掘出土的古物和全部原始記錄都裝箱運走,和它們一起轉(zhuǎn)移的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大批文物。此時,李濟正任職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作為押運人,他擔(dān)負起保護文物遷移的重任。李濟一家七口從此踏上跟隨文物流亡的道路。
當(dāng)年,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有人勸李濟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李濟心里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東西在,人就要在”。李濟的兒子李光謨回憶那段時期,曾聽見父親和朋友在聊天時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
當(dāng)年,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有人勸李濟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李濟心里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東西在,人就要在”。李濟的兒子李光謨回憶那段時期,曾聽見父親和朋友在聊天時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
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對國共和談抱有希望,以為去臺灣只是躲避一段戰(zhàn)火,等安定后再回來繼續(xù)從事自己的研究。這些文物在戰(zhàn)火之中是很危險的,打起仗來子彈不長眼,萬一文物被毀了怎么辦?打完仗,再運回來不就完了。
為了文物,李濟攜妻兒遷居臺灣。到臺灣后,兒子李光謨的學(xué)業(yè)卻成了問題。因為曾經(jīng)休學(xué),當(dāng)?shù)貙W(xué)校都沒接收他,臺大同意接收,但條件是讓他倒退兩年,并要求學(xué)日語。李光謨不愿意,他決定回上海同濟大學(xué)接著念書。離開臺灣的那天,李濟正在臺北圓山參加考古調(diào)查。只有母親和過繼的弟弟來基隆碼頭送他。李光謨當(dāng)時心里想著暑假還會回來,并不知道這一走竟是永別,因為,兩岸很快就隔絕了,直到李濟去世,李光漠也沒有去成臺北。
近80歲的李光謨現(xiàn)生活在北京。當(dāng)年由于藥品短缺,李濟的兩個女兒先后在流亡的路上因病去世,李光謨成了李濟惟一的兒子。李濟曾希望兒子學(xué)醫(yī),但李光謨卻沒有遵從父親的意愿,他后來改學(xué)俄文,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理論的翻譯工作。1955年,李光謨回大陸6年后,李濟才輾轉(zhuǎn)得知兒子到了北京,并已娶妻生子。從那以后,李濟經(jīng)常托在香港的朋友給兒子一家寄油、糖等日常物品。“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李光謨和父母的來往更加不易,收到了家書,馬上就要燒掉,每一次“運動”都要被逼與在臺灣的父母劃清界線。
在海峽的另一端,李濟只能通過日以繼夜地繼續(xù)整理安陽發(fā)掘報告來排解對兒子的思念。1950年,安陽殷墟遺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中斷13年之后重新開始。武官村大墓的發(fā)掘又有了很多新的發(fā)現(xiàn)。很多時候,李濟都只能根據(jù)記憶將20年前那激動人心的一幕幕記錄在報告中,或是通過從日本買殷墟的圖片,通過香港的一本雜志了解到安陽殷墟的發(fā)掘情況。因為,讓他魂牽夢繞的安陽已經(jīng)遠在大海的另一端了。
1977年,81歲高齡的李濟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綜合性學(xué)術(shù)著作《安陽》(Anyang),為自己學(xué)術(shù)的一生劃了一個句號。兩年后,李濟心臟病發(fā),在臺北逝世。
1995年,李光謨在離開4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臺灣,在臺北的溫州街,把父親留下來的五個木頭箱子的遺物整理了一個星期。回到北京以后,李光謨幾乎將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整理父親的遺稿。這對相隔近半個世紀的父子,終于在另一個時空里完成了心靈的對話。
粱廷煒:一家三代兩岸守護故宮
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煒是1949年護送國寶赴臺的,留下歷史記載:第二批文物1949年1月6日運出,9日到基隆,共計1680箱……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80周年院刊上可以看到,這段歷史被冠以充滿感情的標(biāo)題,故宮館藏國寶“從此分兩地”,而梁金生的家族也因為護送國寶赴臺“從此分兩地”。
梁廷煒祖孫三代都在故宮工作,他本人去了臺灣,兒子梁匡忠和孫子梁金生都在北京故宮工作了幾十年。故宮,已經(jīng)成了梁家?guī)状斯餐男撵`歸宿。
當(dāng)年,盡管社會輿論對文物南遷各執(zhí)一詞,但從1933年1月開始,歷時5個月時間,還是有5批文物共1.3萬箱陸續(xù)運抵上海。已經(jīng)懂事的梁匡忠清楚地記得父親跟隨文物一同南下的情景,“因為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情況,母親和我,還有兩個弟弟就先留在了北京”。3年后,專為儲藏南遷文物的南京朝天宮文物庫房建成,并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上海的文物又分批轉(zhuǎn)運至那里。父親感覺形勢基本穩(wěn)定下來,一家人就在南京團聚了。可惜僅僅半年時間,中日戰(zhàn)爭就爆發(fā)了行政院下達命令,存于南京庫房的南遷文物再次避敵西遷梁家人也由此開始了長達18年的遷徙生活。
“1937年春節(jié)是在北平過的,1938年春節(jié)在寶雞過,1939年春節(jié)在陜西褒城縣(現(xiàn)漢中市勉縣)過,1940年春節(jié)在峨眉過,1941年春節(jié)在樂山過。”提起那段歷史,梁匡忠總是神色黯然,不知道什么時候到什么地方才能安定下來。此后很多年,梁匡忠一家仍舊是輾轉(zhuǎn)漂泊,他用所到之地給孩子們?nèi)∶洪L子在峨眉出生,叫峨生,女兒是國寶遷徙到樂山時出生的,叫嘉生(樂山古稱嘉定),接下來的兩個孩子是抗戰(zhàn)后文物返運南京以后出生的,所以分別叫金生和寧生。1953年開始,故宮文物陸續(xù)北返,梁家也調(diào)回北京,這時又有了一個小兒子,叫燕生。
1949年1月6日,梁廷煒登上招商局派出的海滬輪,護送2972箱國寶中的精華文物前往臺灣,他帶走了妻子和兩個兒子,還有孫子梁峨生。而梁匡忠則被命令留守南京,看護剩下的1萬多箱文物。當(dāng)時梁家人就認為是工作需要,沒覺得是個什么特別重大的事兒并沒有生死離別那種感情。然而誰也沒料到這一別竟成了永訣,等到上個世紀80年代梁匡忠輾轉(zhuǎn)獲得臺灣家人的消息時,父母已經(jīng)雙雙去世了。
一家人分居海峽兩岸,看守著同樣因戰(zhàn)亂而一分為二的兩個故宮,卻彼此不能見面,而梁家和故宮的聯(lián)系并沒有因此而割斷,隨文物回遷南京后出生的二兒子金生,在父親梁匡忠之后也進入故宮工作。“我祖父和父親把文物運走,現(xiàn)在我又進行整理。”如今梁金生負責(zé)故宮文物的管理,被人們戲稱為故宮國寶的“大內(nèi)總管”。他游刃有余地掌管著100多萬件文物的進進出出,無一件毀損。除了保管工作外,更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把故宮散落在民間的國寶征集回宮。梁金生管看得上眼的國寶級文物叫“東西”,經(jīng)他征集回歸的“東西”,每一件背后都有著一段曲折的故事。1995年以1800萬元回購北宋張先《十詠圖》,1996年以600萬元回購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2003年以2200萬元回購隋人書《出師頌》。
梁金生現(xiàn)在工作的地方離當(dāng)年存放《四庫全書》的地方很近,爺爺梁廷煒當(dāng)年在北京故宮就是負責(zé)保管《四庫全書》的,現(xiàn)在文淵閣已是書去樓空。梁金生每天上班都要從文淵閣路過,他很懷念那棟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