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道雜俎
秘錫林
一、 流行與傳統(tǒng)

有人說,中國書法史上凡有過的書寫形式,在新時(shí)期以來的短短二十余年里,幾乎都有人嘗試過,或正在嘗試。那種溫文爾雅的書學(xué)傳統(tǒng)似乎正在漸行漸遠(yuǎn),中國書壇由此進(jìn)入一個沒有旗手,沒有權(quán)威,但卻群雄并起,名家輩出,空前繁榮而又讓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的浮躁時(shí)代。五千年的書法發(fā)展歷史濃縮集中再現(xiàn)于二十多年里,這不但在中國書法發(fā)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藝術(shù)發(fā)展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繁榮伴隨著浮華,活力派生躁動,渴望成功與利益的驅(qū)使,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輕,加之生存空間的相對狹小,各種思想流派之間產(chǎn)生激烈沖撞,是不言而喻的。流行與傳統(tǒng)之爭,十多年來爭論不斷。
流行與傳統(tǒng)之爭,依我看,其實(shí)遠(yuǎn)遠(yuǎn)還說不上是建設(shè)性的論爭,而毋寧說是意氣之爭,山頭之爭,利益之爭。流行與傳統(tǒng)爭論的焦點(diǎn)之一,即是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從理論上講,這實(shí)際上是一個不會有解的命題:優(yōu)秀的藝術(shù)作品不會有優(yōu)劣之分。就書法而言,不同的書體,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時(shí)代,有不同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如果我們拿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不同的藝術(shù),我們所能做的大約就只能是削足適履;反過來,我們各持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同一個事物,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好做:吵架。流行與傳統(tǒng)之爭,這兩種情況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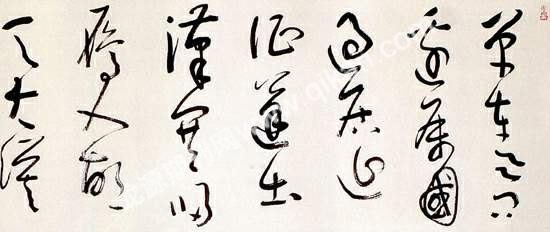
那么流行書風(fēng)與傳統(tǒng)書風(fēng)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呢?流行書風(fēng)實(shí)際上決不是一種沒爹沒娘憑空而生的怪胎,孕育流行書風(fēng)的恰恰是綿延幾千年的傳統(tǒng)書法。這是事實(shí),誰也否定不了。傳統(tǒng)書法是一座取之不盡的藝術(shù)寶庫,我們的先人們幾千年的藝術(shù)實(shí)踐,為我們留下了如此豐富的藝術(shù)瑰寶和無限的藝術(shù)發(fā)展空間;同時(shí),這個藝術(shù)寶庫也因我們的創(chuàng)造而日益豐富。創(chuàng)造,永遠(yuǎn)是書法藝術(shù)的永恒主題。但,創(chuàng)造并非也不可能推倒重來。如果另起爐灶,除了勇氣可嘉之外,不是無知便是不自量力,或者不妨說是別有居心!并且,那將與書法藝術(shù)無關(guān),譬如現(xiàn)代派的某些作品。當(dāng)然,如果墨守成規(guī),對于前人的東西不敢越雷池半步,書法藝術(shù)也就會變成了博物館里的老古董而失去鮮活的生命力。因此,我們可以說,流行書風(fēng)的出現(xiàn),它的那種對傳統(tǒng)的赤裸裸的悖逆與改造,它的那種出乎傳統(tǒng)想象的生命張力,確實(shí)為中國書壇吹來了一股清風(fēng),為我們打開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如果我們對流行書風(fēng)不帶偏見,如果我們對流行書風(fēng)主流作者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及其作品作一番認(rèn)真研究(當(dāng)然那些以丑怪為尚者除外),如果我們將流行書風(fēng)放在中國書法發(fā)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那么,說流行書風(fēng)是繼碑學(xué)大興之后對傳統(tǒng)書學(xué)的又一次大的革命,大約是不錯的。所不同的是,當(dāng)年趙之謙、康有為們是以漢魏碑刻為武器改造二王的帖學(xué),而今天流行書家們則比趙、康走得更遠(yuǎn),不但有碑,更有那一時(shí)期的原始形態(tài)的民間書法。我們且不說二者取法的高低,也暫且不去比較他們的藝術(shù)成就,單就其淵源而言,流行書風(fēng)所取法的民間書法與趙、康等人所師法的魏碑以及二王一樣都是由同一個母體派生出來的。正如碑學(xué)的興盛并沒有取代二王的帖學(xué)一樣,流行書風(fēng)的出現(xiàn),不會也不可能取代此前存在的傳統(tǒng)書法,相反,碑學(xué)的出現(xiàn)豐富了傳統(tǒng)書法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現(xiàn)在流行書風(fēng)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也正在極大地影響和豐富著中國當(dāng)代書法的發(fā)展,就其發(fā)展而言,也必將融入傳統(tǒng)成為傳統(tǒng)的一部分。至于這一點(diǎn),書史已有前轍可尋:宋之米元章貶唐代諸賢,清末民初康南海之貶帖揚(yáng)碑,矯枉過正,石破天驚,振聾發(fā)聵,影響了無數(shù)書人,然時(shí)過境遷,回頭再看,橫看成嶺側(cè)成峰,歐褚顏柳不因元章而廢;二王一脈也與碑學(xué)并存且不斷融合,當(dāng)時(shí)勢同水火,現(xiàn)在已經(jīng)和平相處,共同成為了中國書法藝術(shù)寶庫中的瑰寶。所謂萬川競流歸于大海,這或者正是中國書法發(fā)展大勢之謂。這,或者也必將是流行與傳統(tǒng)之爭的最終結(jié)局。
二、 學(xué)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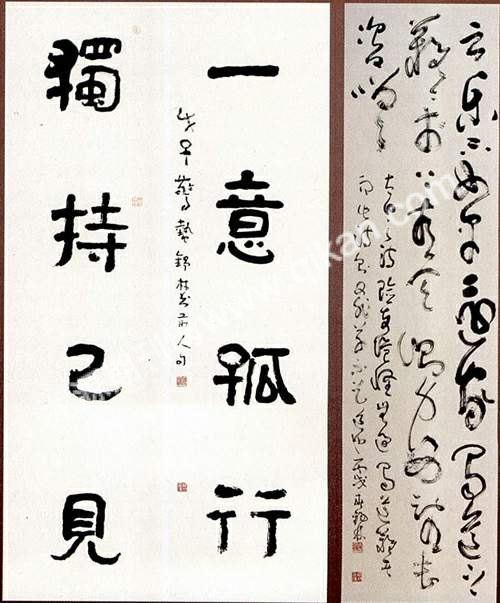
書家的“學(xué)者化”,已經(jīng)喊了很多年了。至于是誰首倡,什么時(shí)間,手頭既無資料,也無暇去考證了。不過印象里,大概總有十幾年了吧。迄今為止,“化”得怎么樣了,我想,凡是關(guān)注書壇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當(dāng)然,以十幾年的功夫,使書家“化”成一個個“學(xué)者”,未免難為書家們了點(diǎn)。
我們現(xiàn)在很容易從眾。尤其眾口所認(rèn)的是出自權(quán)威或被權(quán)威首肯過的時(shí)候。比如這似是而非的所謂書法家的“學(xué)者化”問題。這個命題的提出本身就很“學(xué)者化”。應(yīng)該說,這一命題的提出對中國當(dāng)代書法的健康發(fā)展毫無疑問有其積極意義,也是切中時(shí)弊的。但這一命題卻為眾多書家們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書法家絕不能僅僅只是個“寫字匠”,而必須具備豐厚的學(xué)養(yǎng),這是誰都明白的理兒,但是正如后人評價(jià)康南海的書法觀及其實(shí)踐主張時(shí)所說:看對了病卻開錯了藥。我們不否認(rèn),在現(xiàn)當(dāng)代活躍的書家中確有一些是“學(xué)者化”了的。但這是否就一定是帶有一種必然呢?我看未必。學(xué)者是做什么的?學(xué)者是研究某一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并有一定成就者。學(xué)者的專長是什么?我以為該是探究學(xué)理,其思辯方法主要是理性的。而書家在書寫過程中,講的是“技”進(jìn)乎“道”發(fā)乎“情”,古人說,書者,抒也,大約也正是這個意思。顯然這與做學(xué)問是完全不同的。做學(xué)者首先要冷靜,邏輯思維嚴(yán)密,材料要詳盡,力求賅備無遺,理要說得環(huán)環(huán)相扣,滴水不漏;而做書家卻要張揚(yáng)個性,獨(dú)抒性靈,得魚而忘筌,返樸而歸真。以此看來,要書家們個個去化成“學(xué)者”,豈不難為了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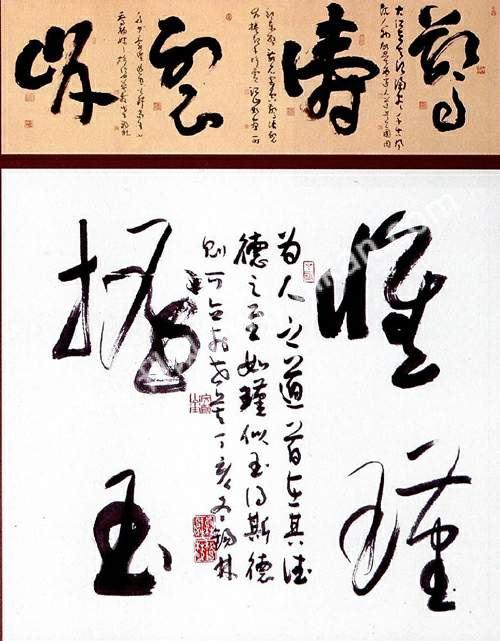
這倒使我想到了與此相關(guān)也相似的命題:書法家不妨“文人化”。書家們做“學(xué)者”不易,做“文人”就易么?當(dāng)然也不易。不過兩難相較,到底易些。為什么?一個專,一個博也。專了就須精深,要有創(chuàng)見,那是窮經(jīng)皓首的功夫,你想當(dāng)今但凡有些名氣的書家,應(yīng)酬趕場,恐“寶馬”之不速;推杯換盞,有紅袖添香;門外千般光景,怎耐得那孤影青燈。倘若硬要按于案前讓他去化成什么“學(xué)者”,這如何可以“化”得?倒是做個文人,無眠時(shí),讀兩卷書,酒酣時(shí),謅幾句詩,興來了,寫篇歪文,有靈感了不妨閉門幾日也“學(xué)者”一番,興之所至,信手為之,怡情遣興,雖說與“學(xué)者”的修為不怎么搭界,卻可免了坐冷板凳的枯悶,誰又能說這不是文人的雅事?
為書家計(jì),我以為實(shí)在應(yīng)該放書家們一馬,舍難就易,把書家們“化”成“文人”,任憑其海闊天空做魚做鳥。
(責(zé)編:劉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