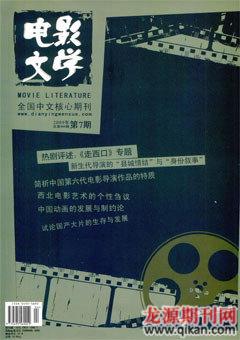反類型面孔下的三重門
昊迎盈
[摘要]學(xué)者陳墨認(rèn)為,武俠電影作為一種有民族特色的類型片的特殊規(guī)范,在其構(gòu)成要素中,“武”與“俠”是兩個(gè)最基本的要素。《十面埋伏》意圖把一個(gè)以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多義性為隱喻象的“愛情故事”當(dāng)做兵器,來突破武俠電影的類型藩籬。很可惜,它并不成功。沒有性格的“武”如沒有點(diǎn)上蠟燭的燈籠,因此它只能稱得上是黑暗中的“武”者。
[關(guān)鍵詞]武俠電影。《十面埋伏》,類型電影
在近百年的刀光劍影蒙太奇中,武俠電影擁有了一套自己獨(dú)有的類型語言。漫長(zhǎng)的農(nóng)業(yè)文明造就了中國(guó)觀眾觀賞武俠類型電影的集體無意識(shí)的審美文化心理,但當(dāng)下現(xiàn)代文明的轉(zhuǎn)型無疑又為20世紀(jì)90年代以后的武俠電影融入了現(xiàn)代人的生命感覺。21世紀(jì),張藝謀用《英雄》、《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以下簡(jiǎn)稱《黃金甲》)開創(chuàng)了武俠大片時(shí)代。《英雄》和《黃金甲》評(píng)述已多。若干年后,我們?cè)倩仡^看《十面埋伏》,它其實(shí)可以看做是張藝謀繼《英雄》之后,急于從武俠藩籬里突破的轉(zhuǎn)型之作,之后開啟了宮廷武俠的《黃金甲》。《十面埋伏》意圖把一個(gè)以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多義性為隱喻像的“愛情故事”當(dāng)做兵器,來突破武俠電影的類型藩籬。很可惜,它并不成功。
對(duì)類型電影的研究規(guī)則是受到文學(xué)研究的啟發(fā)而發(fā)展起來的,韋勒克和沃倫提出的創(chuàng)新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類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jǐn)U張它”不無參考意義。因此,對(duì)類型電影進(jìn)行突圍,事實(shí)上是一個(gè)不能完全背離類型規(guī)則的游戲。為類型留下幾道別扭的擦痕并不是創(chuàng)新,新的夢(mèng)境將由這些規(guī)則中內(nèi)生出的新鮮力量來完成。
學(xué)者陳墨認(rèn)為,武俠電影作為一種有民族特色的類型片的特殊規(guī)范,在其構(gòu)成要素中。“武”與“俠”是兩個(gè)最基本的要素。“武”是手段,“俠”是主題,而“江湖”則是“武”與“俠”迷蒙交織著的大背景。那我們就從這三個(gè)角度來分析《十面埋伏》的類型突圍。
一、扁平而殘缺的“江湖”符號(hào)
“江湖”原指長(zhǎng)江和洞庭湖,也可泛指三山五湖。經(jīng)過民間傳奇和文人詩篇的渲染,“江湖”已經(jīng)演變成一個(gè)兼有“仗劍執(zhí)酒”的豪情和“夜雨十年燈”的荒疏的意境世界。
學(xué)者陳清僑在他的《當(dāng)代香港武俠電影中的希望喻象和江湖想象》一文中說道:“‘江湖,在電影的意義世界里,往往寄意表征,涵括著對(duì)世界的借喻和象征,是人世間的一種喻象……當(dāng)此普及想象在電影中再現(xiàn)成章時(shí),敘事的脈絡(luò)往往便糾纏于天涯劍客如何多番探求生命真諦之種種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電影世界中的“江湖”是由導(dǎo)演想象構(gòu)建的縹緲時(shí)空,但在這時(shí)空的里層卻勾勒出了現(xiàn)實(shí)世界豐富而多義的印象。
那么《十面埋伏》為觀眾描摹了一個(gè)什么樣的“江湖”鏡像呢?
首先,從江湖鏡像中的具體場(chǎng)景——“江湖”的空間背景來看,張藝謀的確展現(xiàn)了一個(gè)充滿絢爛色彩的視覺奇觀。之前的武俠電影,很少帶給我們?nèi)纭队⑿邸贰妒媛穹贰饵S金甲》般的視覺感受。張藝謀用自己擅長(zhǎng)的色調(diào),把代表陰謀的富麗堂皇的牡丹坊、凸顯了“暴力美學(xué)”的綠色樹林和竹林以及象征著愛與死的白色花海組成一幕幕人間美景,讓我們的心靈在視覺的撫慰下得到了最表層的滿足。
由于武俠類型電影大多把武俠小說當(dāng)做腳本,它們延承了武俠小說的場(chǎng)景安排,多將“懸崖山洞”、“大漠荒野”和“寺院道觀”這三大處及其衍生地貌作為主要類型場(chǎng)景。在《十面埋伏》中,出現(xiàn)的重要場(chǎng)景依次有:牡丹坊、樹林、竹林、花海。除了“竹林”一場(chǎng)戲中明顯有著《俠女》《臥虎藏龍》的痕跡,武俠電影的類型場(chǎng)景及其衍生地貌都在《十面埋伏》中失去了蹤影。
在敘事結(jié)構(gòu)較強(qiáng)的武俠類型電影中,“懸崖山洞”、“大漠荒野”和“寺院道觀”都有著自己特殊的功能。這些“特殊功能”不僅體現(xiàn)在文本敘事上,也凸顯在電影的視覺印象中。因?yàn)橐朁c(diǎn)的不同,這些地點(diǎn)或“隆起”或“下陷”,或“開闊”或“幽深”,反映在視覺效果上,無疑都是視線的轉(zhuǎn)折和變化。不同場(chǎng)景在武俠電影中交織錯(cuò)落,切斷了觀眾“看滑了”“看膩了”的視覺慣性,形成了江湖“鏡語”構(gòu)圖中丘壑迷離的節(jié)奏感。
而《十面埋伏》中,我們看到的僅僅是平面鏡像的簡(jiǎn)單羅列。樹林、竹林、花海在本質(zhì)上都不具備上述場(chǎng)景中那些視點(diǎn)高低的區(qū)分,更不能給人帶來視覺突轉(zhuǎn)的沖擊力。它們宛如—張張色彩斑斕但卻面無表情的彩紙,貼在了《十面埋伏》的萬花筒式的江湖環(huán)境中。人物在這些平面展開的江湖鏡像中不斷橫向奔跑,機(jī)位也隨之不斷橫向移動(dòng),缺乏節(jié)奏感的江湖場(chǎng)景安排給觀眾帶來了游離于色彩之外的審美疲勞。
邏輯的混亂同樣是《十面埋伏》場(chǎng)景設(shè)置中的致命傷。比如影片的“樹林”、“竹林”、“花海”顯然分布在不同植物帶,影片主人公在影片給定時(shí)間內(nèi)穿越了它們并不能取信于觀眾。《十面埋伏》中的“江湖”鏡像在雷同的平面場(chǎng)景鋪排間造成了節(jié)奏感和邏輯性的雙重缺失,仿佛一個(gè)單純的色彩符號(hào),而不是有著通透靈性的象征世界。
其次,從《十面埋伏》里的“江湖”運(yùn)行機(jī)理來看。“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江湖”事實(shí)上是一個(gè)與“廟堂”即。朝廷”相對(duì)的意象。“江湖有江湖的生活方式,江湖有江湖的隱語黑話,江湖有江湖的是非標(biāo)準(zhǔn)”,這個(gè)世界與“朝廷”有著截然不同的兩套規(guī)矩。
在影片中,“飛刀門”無疑是“江湖”的代表。電影在開頭字幕中聲稱這個(gè)門派因?yàn)槌埍┒鴬^起反抗,但影片中并沒有予以表現(xiàn)。我們看到的僅僅是這個(gè)神秘莫測(cè)且尊卑森嚴(yán)的門派設(shè)定了一個(gè)“臥底”式的陰謀,并以犧牲個(gè)人情感甚至生命為代價(jià)。然而更讓人不安的是,這一點(diǎn)與作為“朝廷”代表的“總捕衙門”驚人地相似。也就是說,在《十面埋伏》里,“江湖”和“朝廷”奉行的是同一套規(guī)則。他們的面目在本質(zhì)上已經(jīng)毫無區(qū)別。到此為止,“江湖”的獨(dú)立意味已經(jīng)死了,或者說已經(jīng)被“朝廷”同化了。
然而這具“江湖”的尸首卻“死而不僵”,它還要和“朝廷”這個(gè)和它性質(zhì)相同的符號(hào)連成一體,成為影片悲劇的“假想敵”。
“在張藝謀作品的敘事符號(hào)體系中,一直有概念化的符號(hào)式的階級(jí)對(duì)立的意識(shí)形態(tài)論和虛擬夸張的世俗神話色彩。”回溯張藝謀的電影世界,幾乎每一部影片中都有一個(gè)陰暗的專制符號(hào)在壓迫生命個(gè)體的倫理需求,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里的面目不清的“老爺”。在《十面埋伏》中,這個(gè)想當(dāng)然的“專制”角色就由“江湖”與“朝廷”這兩個(gè)本應(yīng)該毫不相同的敘事符號(hào)來充當(dāng)了。與張藝謀以往的影片相似,專制“符號(hào)”是殘缺的,表現(xiàn)在影片里,就是飛刀門“大姐”始終籠罩的面紗和“總捕頭”肉身的缺席。“江湖”和“朝廷”以同樣的規(guī)則、同樣的敘事功能乃至同樣的意識(shí)形態(tài)融合在了一起,成為張藝謀的影片中一以貫之的干癟咒語,如幽靈一般揮之不去。
在反“類型”的旗號(hào)下,《十面埋伏》破壞了“江湖”的類型語法,對(duì)以往的“江湖”進(jìn)行了粗暴解構(gòu)。但是,“解構(gòu)”之后的江湖卻是一方殘破的空白。“江湖”不僅在時(shí)空上
呈現(xiàn)為抽離了歷史向度的扁平色塊,同時(shí)也失去了自己獨(dú)立的精神內(nèi)蘊(yùn),淪為一個(gè)失去了面目不清的破碎的“專制”符號(hào)。這個(gè)專制符號(hào)數(shù)年后附在《黃金甲》的“宮廷。中重生了。
二、人造柵欄后的欲望動(dòng)物——“俠客”
在武俠類型電影中,承載“俠”與“義”的生命個(gè)體就是俠客。張藝謀把“江湖”變成了“陳家大院”,《十面埋伏》中的“大俠”或“俠女”也和張藝謀以前鏡像中的人物有著基本雷同的面孔了。
首先,《十面埋伏》借鑒了楚原《天涯·明月·刀》式的臥底陰謀,把“江湖”分割成無數(shù)個(gè)以生命個(gè)體為基本單位的柵欄。金捕頭似乎背叛了他對(duì)劉捕頭的承諾,然而劉捕頭一開始就讓金捕頭掉入了陷阱中;小妹背叛了劉捕頭的情感,背叛了飛刀門,然而她和金捕頭逃亡之初也是同“行”異夢(mèng)……整部影片充斥著陰謀與背叛,而這其中只有“有意”和“無意”的差別。從影片的構(gòu)圖中,我們也明顯可以看出導(dǎo)演的這個(gè)意圖。無論是劉、金二位捕頭的初次出場(chǎng),金捕頭與牡丹坊老鴇(即“飛刀門”大姐的代表)的第一次見面,甚或是劉捕頭與小妹、劉捕頭與老鴇的會(huì)面,影片都讓人物處于對(duì)立分割畫面的位置,暗暗隱喻著他們的隔閡。
把“俠客”作為彼此間難以溝通和平衡的生命個(gè)體在影片《東邪西毒》里同樣有所刻畫。但和以寓言方式突出了武俠類型電影重圍的《東邪西毒》不同的是,《十面埋伏》輕松放過了對(duì)個(gè)體的人性矛盾的刻畫,轉(zhuǎn)而去追求那些并不能自圓其說的情節(jié)。在張藝謀的鏡像敘事中,“俠客”個(gè)體的生命軌跡被永恒設(shè)定為“自來如此”和“應(yīng)該如此”。也就是說,《十面埋伏》中生命個(gè)體的矛盾(包括門派內(nèi)部的矛盾)是想象出來的,是一道道硬加上去的鐵柵欄。影片沒有對(duì)這種矛盾進(jìn)行同一視覺和同一語言織體下的透視和剖析,相反把這些人性“深淵”視為理所當(dāng)然。因此,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十面埋伏》中的“俠客”是已經(jīng)概念化了的“矛盾。集中體,他們不再是“有屬于自己的秘密和夢(mèng)想”的生命個(gè)體,而變成了被抽離了靈魂的面貌相似的傀儡。
其次,當(dāng)武俠類型電影的“江湖俠義”遭到剝離,“俠客”們的個(gè)體行為就失去了依托,《十面埋伏》不得不為他們重新設(shè)置出場(chǎng)。動(dòng)機(jī)”。張藝謀同樣把自己所熟悉的電影語言填充到了這一片空浮的“動(dòng)機(jī)”里,把“俠客”變成了“高粱地”里的欲望動(dòng)物。
在《十面埋伏》的倫理織體中,飛刀門“大姐”是沒有性別的,唯一作為女性出場(chǎng)的就是俠女“小妹”。然而她與作為“俠客”的金、劉兩位捕頭卻構(gòu)成了一個(gè)純粹欲望的世界。
“小妹”在這個(gè)世界中沒有面目,也看不出任何個(gè)性,她淪為了男性的欲望、凝視對(duì)象。她甫一出場(chǎng)就處在金捕頭的目光注視下,半裸的肩傳達(dá)出強(qiáng)烈的被“凝視”信息。而-劉捕頭在“三年”后第一次見到小妹時(shí),她正在金捕頭的純欲望行動(dòng)中掙扎,小妹裸露的肩同樣暴露在劉捕頭作為“男性”的眼光之下。接下來的“牡丹坊艷舞”更是一種以男權(quán)為主導(dǎo)的“觀賞”行為,在“蕓豆”的挑“逗”下,處于劉捕頭目光中心的小妹翩翩起舞,這不能不讓人聯(lián)想到小妹與金捕頭見面后的第一個(gè)行為也是獻(xiàn)舞,“舞”在這里包含著戲謔的成分,成為女性臣服的外在象征。而接下來的公堂審訊一幕里,與其說處于高位的劉捕頭與處于低位的小妹之間是一種“官民”關(guān)系,不如說是一種征服與被征服的關(guān)系。在這樣的高低構(gòu)圖中,已暗暗彰顯出劉捕頭視野中的小妹,不過是屬于他的欲望獵物。這一點(diǎn)在影片最后的情節(jié)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劉捕頭在殺了小妹之后強(qiáng)調(diào)說:“你可以不愛我,但是你不能跟他走。”只要小妹還在原地,他就可以繼續(xù)把小妹當(dāng)做是自己的從屬物,但當(dāng)這個(gè)從屬物一旦不再屬于自己,男權(quán)中心的思想就讓他毀滅了她。
當(dāng)俠女被設(shè)定成“欲望獵物”,我們既看不出她的“俠女”身份,也難以讀解她內(nèi)心的矛盾和掙扎。我們只在她被欲望主體不斷凝視的過程中看見了她模式化的抵制和臣服,“小妹”這個(gè)符號(hào)設(shè)置只是一個(gè)干癟的客體存在,人性的多義遭到了懸置。
而作為“欲望主體”的金、劉二位捕頭同樣也是兩個(gè)面目不清的符號(hào)。他們對(duì)小妹的欲望行為呈現(xiàn)出一致的驚人面貌。對(duì)衣衫—欲望遮蔽體的撕破,對(duì)小妹—欲望客體的猥褻都采取了同樣的構(gòu)圖和人物調(diào)度,這不得不讓人心生疑問:在影片中,俠客和欲望動(dòng)物是不是就可以畫上等號(hào)。
《十面埋伏》以愛情的名義,撕毀了“俠”和。義”的基本存在;但它同樣沒有關(guān)注“人。的個(gè)體生命感覺。我們聽到的,是眾口一詞的生命呢喃;我們看到的,是沒有性格的,也失去了基本“俠義”精神的欲望裹尸布。
三、黑暗中的“武”者
作為類型片范疇的武俠電影,“主要視覺風(fēng)格和形式元素都是動(dòng)作,鏡語特征都是挖掘動(dòng)作、運(yùn)動(dòng)的形式?jīng)_擊力和美感”。
在這部電影中,張藝謀獨(dú)辟蹊徑地在遠(yuǎn)景構(gòu)圖中穿插了大量特寫鏡頭,使視覺沖擊力與詩意的美感同時(shí)呈現(xiàn)。而近景的多角度切換與寫意的慢鏡頭交織錯(cuò)落,賦予了武打動(dòng)作的節(jié)奏感。同時(shí),《十面埋伏》非常注重對(duì)武打動(dòng)作瞬間造型的雕琢,在起起落落的慢鏡頭加蒙太奇的延展中有著力與美的韻味。但《十面埋伏》的“武”戲滿足了“武”的“詩化”和“神化”,卻很難從中找到“性格”的影子。“武”的性格說穿了就是與心靈、情境、個(gè)體性格相符的動(dòng)作設(shè)計(jì)。比如說“輕功”,在徐克的《東方不敗》里,他將輕功做得很抒情,來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的歡娛。而在李安的《臥虎藏龍》里,玉蛟龍的輕功動(dòng)作輕飄,而俞秀蓮的動(dòng)作沉穩(wěn),這與她們的性格都是相符合的。
但在《十面埋伏》里,小妹的飛刀、大姐的飛刀以及劉捕頭的飛刀,甚至金捕頭射出的箭在出手時(shí)都毫無區(qū)別,都是以慢鏡頭呈現(xiàn)的悠悠飛行體:一樣的慢鏡頭,一樣的縱深,一樣的運(yùn)動(dòng)速度和軌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沒有性格的“武”如沒有點(diǎn)上蠟燭的燈籠,因此它只能稱得上是黑暗中的“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