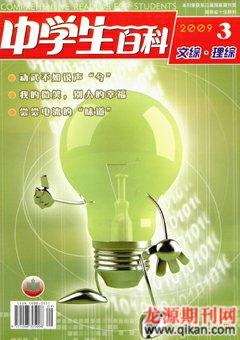高橋的預言
胡 堅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日本人大獲全勝,三位獲獎者,一個美籍日裔,兩個日本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一下想起了中學時代看的一本書《丑陋的日本人》。當年的那本書里,作者曾經放出狂妄的預言: “再過十年,也許諾貝爾獎就都要集中到日本了”——需要說明的是,這本書寫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若是嚴格打賭,作者肯定是輸了,但是面對這樣一個結果,今天的我們卻很難輕松起來。
上個世紀60年代,該書的作者,日本教授高橋敷跑到南美教書。背井離鄉之后,一個重要的感受居然是種族歧視。從外觀上分辨不出亞洲各國的居民尚屬正常,但是在當時,很多南美人對于亞洲的無知甚至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高橋曾經被出租車司機這樣問道:“你是日本人還是支那(中國)人?見鬼,我前幾天也拉了一個自稱日本人的支那人——究竟日本是支那的一個省還是支那是日本的一個省?”
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移民和游客在當地很難看到好臉色是一個明顯的原因,但更為久遠的一個原因對于南美洲的當事人來說卻更加不光彩——歷史上,南美在早期開發的過程中,倒霉的不僅有當地土著,還有大量被誘騙的、來自東亞的勞工。修建在安第斯山間的鐵路就布滿了他們血淚的代價。正是這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使得部分南美人在面對亞洲人時產生了毫無道理的優越感。
但是高橋敷先生——戰后逐漸走向振興的日本國民,面對種族歧視,最自然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奮起還擊,于是到處向人介紹世界第一的東京塔(當時的紀錄),介紹新干線高速列車,東京奧運會更是成為高橋對外宣傳的利器……
但是結果令人喪氣,高橋很快發現,即使是充滿友善的國際友人,也對日本充滿了無知——一位教授在演講中介紹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舉了個例子“(日本已經進化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現在武士已經很少了,不去鄉下看不見了……”
更讓高橋他們不能接受的是,當他向身邊的人吹噓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工業強國的時候,居然只有一位古巴朋友認同,而這位朋友認同他結論的同時,又進一步闡釋了自己強悍的理由:“世界第一強國是抗擊美國并且取得成功的古巴,世界第二是把美國拖得狼狽不堪的越南,世界第三就是被美國蹂躪了四年(戰后)還沒有趴下的日本……”
如果僅僅就是如上內容,那么高橋的這本書似乎更像是域外笑談。但讓我在時隔多年之后能夠準確回憶起它的,卻不僅僅是一個民族過去的心酸笑料。在那個時代,日本人中獲得諾貝爾獎的,僅有湯川秀樹一人,以至于高橋在向洋弟子們宣傳日本在物理方面做出貢獻的時候,會招來洋弟子們抗議感到他過度吹噓日本,要他“下課”。
于是就有了這樣一段著名的危機演講:
“我是一個熱愛日本的日本人。正因為如此,我才能熱愛秘魯。為什么呢?那是因為今天的秘魯與幾十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如果說有不同地方的話,那就是你們還擁有自由。然而,我卻要在這里描繪日本的未來。我隨時都想回日本去,但是,作為紀念,我希望諸位牢牢記住兩件事。
“第一,無論你們相信與否,現在,日本的科技水平已經躋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再過十年,也許諾貝爾獎就都要集中到日本了。盡管如此,我還是要請諸位正視一個現實——在一百年前,日本的文盲現象遠比秘魯的印第安嚴重。那時,日本從與你們有血緣關系的西班牙、荷蘭以及許多國家邀請教師,前來講授物理學、解剖學和地震學等課程。可是,這些教師根本就不懂日語。況且,當時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找到一本與日語對應的辭典。為了弄清一個個詞匯的含義,他們通宵達旦地研究。有時,為了弄懂一個單詞,甚至要反復討論一個星期之久。有時,學生們好不容易弄懂了某個單詞之后,竟然會緊緊地握著手,激動地流出眼淚。解剖新書就是這樣經過八年時間而被譯成日文的。當然,大家也有感到苦惱和遺憾的時候,但他們相互鼓勵道:‘只要這樣干下去,將來日本就一定會超過那些老師們的國家。終于,他們創造了今天的日本。雖說在日本充滿著丑惡的東西,但是,在研究學問方面這種百年來的不懈努力卻絕非謊言。就我個人而言,隨時都想高高興興地辭去教職回日本。我在等待著你們對我說:‘你講的東西我們都懂了,不需要再講了。
“可是,你們說不出這句話。”
研究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軌跡的時候,將兩個國家相似的歷史階段作為比較是很常見的手段——比如說起當下中國經濟,人們就常常說起二十年前的日本,討論升值貶值的時候,就會說起歷史上的“廣場協議”。類似的,在觀點與角度上的討論或許永遠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果,但是我仍然想在這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宣布之后,追憶一下多年前的那本書——回憶,卻并不僅限于過去。
編輯/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