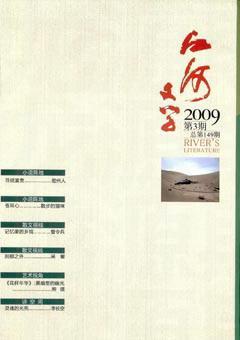漢族妹和布依哥
王寶玉
那年春天,他們偶爾相識,彼此間都留下良好的印象。
1973年初春,高原上的清晨,凜洌的寒風仍呼呼地刮著,吹到臉上,像刀割一樣疼痛。握著打狗棒,背著稅務包的張銳,壓抑著離別親人的憂傷,走向大山深處征稅。她正縮著脖子靠近城關稅務所側面那棵百年榕樹,剛向河坎下了幾步,布依老所長急促地在她身后喊道:“小張,你昨天剛探親回來,休息幾日再進山,要不等明后天小莫小姚從山里回來,你再同他們一道出發,山頂有一段路太荒涼。”望著老所長那副憐愛擔心的表情,張銳心里涌過一股暖流,她答道:“你老放心吧,我要盡快將年前年后的這段稅收上來,再往后就春耕農忙了,我會小心的。”
是啊,河坎邊這根深葉茂的古榕樹就是所長感嘆的見證,今日,它仍然立在河邊上向美麗的婀麗河伸著臂彎著腰,歡送著張銳走上渡船,又望著她隨船橫渡到對岸,然后在對岸那片田野上行走,直到看不見蹤影。
走完那一段唯一空曠平坦的沃野,張銳眼前橫亙著無邊的崇山峻嶺,她抖擻精神,拄著竹棍,時而在螺旋上升的盤山路上踩踏,時而又在公路邊的小道上攀爬,終于渾身冒著熱氣登上了離縣城最近也最高的山頂。她看了看手表自言道:“快走吧,還有二十里路呢。”是呀,這山頂就是新的起點,從這里還要爬一道坡又一道坡,繞一個彎又一個彎,隨著陡峭的山路走向各個隱蔽在叢林中的山寨向村民收稅,這就是讀完五年大學,畢業后到部隊受兩年再教育,又下到基層的女大學生張銳的工作。
她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頭發,轉身向山里趕去,來到一片灌木地,聽見背后發出“唰唰”的聲響,她急忙回頭,環顧四周,除了在風中不停晃動的草和樹什么也沒見,她驚嚇地問了聲:“誰?”無人回應,她的眼睛一下盯住了身后那一簇簇高大的蘆葦,耳邊頓時想起了小莫小姚路過此地時對自己說過“那蘆葦里最藏老虎”。“老虎?”張銳背脊立刻掠過一股涼意。她一邊后退一邊四處恐慌地張望,然后使出全身力氣,快步轉彎奔跑,同時大聲吼道:“我不怕。不怕,就是不怕……”不怕不怕的聲音在四周的山巒中此起彼伏地回蕩。
這時,正在附近山道行走的岑大權聽到了喊聲。這位六十年代的軍人、七十年代的民兵。有一種本能的應戰準備意識。他邊跑邊喊:“誰?你在哪里?快說啊,是誰?”聽到有人接應。張銳心里一陣高興,恐懼感頓時消散一半,她仍然一邊跑一邊大聲喊著:“在這里,在這里,蘆葦叢邊!”說了兩次,應聲而來的岑大權快速向張銳奔來,遠遠地看見張銳手持著竹棍,驚恐地跑著,但并無險情,便松了一口氣,大聲問道:“你是哪個隊的知青,為什么在這兒呼叫?”張銳喊道:“那,那個里面!有老虎!”“老虎?”聽到此話,赤手空拳的岑大權先楞了一下,然后疑惑地問:“先別怕,你親眼看見的嗎?”張銳說:“沒,沒看見,但我正在走路,聽見里面有唰唰的聲音。”張銳說到此,全身仍感到毛骨悚然。聽到此話,岑大權眼睛密切地凝視著蘆圍叢,并一步一步地向蘆葦靠近,只見蘆葦不停地搖動,他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用力朝蘆葦叢中扔去,嚇得張銳一邊往遠處跑,一邊喊:“你怎么扔石頭,老虎出來怎么辦?”岑大權道:“不弄個明白,萬一過路的人真闖到怎么辦?”張銳嚇得加快速度跑起來,“撲通”一下,摔了個嘴啃泥。岑大權又朝蘆葦里扔去幾塊石頭,仍然未見老虎。于是,他拍拍手上的灰,回頭朝著張銳喊:“別怕,沒有老虎。”見張銳摔倒在地,趕緊跑了過去,一邊扶起張銳,一邊說:“你看,再往那邊去一點,就是懸崖了,不小心滾下去,就真的沒命了。”張銳哭喪著臉說:“完了,我的腿斷了,我已經站不起來了。”岑大權扶著她,憑著經驗說:“你把腿踢一踢。”張銳踢了兩下,岑大權松口氣說道:“骨頭沒有斷,是筋被扭傷了。”岑大權老練地在她腿上幾推幾拉,不一會兒,張銳感到疼痛感減輕了許多。他倆慢慢地走著,岑大權說:“還是解放初期,這里出現過老虎,但這幾十年都沒聽說過老虎的蹤跡了,倒是偶爾聽說過有兇猛的野豬與人不期而遇,不過,遇上野豬,你不搭理它,它不會主動攻擊人:倒是野兔經常出現,剛才你聽到的唰唰聲,估計就是野兔,它見到人就會象箭一樣從草叢中竄跑。”張銳仍心有余悸地說:“如果真有老虎,我今天就犧牲了。那我再也回不了湖北,見不到可愛的女兒了。”岑大權好奇地問:“你已經有孩子啦?我還當你是知青呢!穿著簡樸,兩只小辮,這么年青。嗓子又清脆、響亮,還真沒想到哇!”張銳微微笑了一笑,說:“你真勇敢,今天遇到你真幸運。”岑大權問:“你在縣里啥單位工作?是下鄉來幫助修水利的?那可受人歡迎呢!”原本沒有弄清對方的身份,張銳是不會告訴自己的真實情況的,但眼前這位看上去衣著整潔、相貌平平、中等個子、黝黑的四方臉上嵌著一對精明眼的壯年漢子,那莊重、成熟的表情,樸實、熱情的舉止,勇敢、無畏的行為足使她產生好感,出于信任和感激,張銳就直說了:“我是城關稅務所的,下鄉去收稅。”聽到此話,岑大權先愣了一下,急促地問:“你現在去唐牙隊嗎?唐牙大隊那七個小隊是你的責任區嗎?你姓張?”張銳奇怪地問:“是呀,你怎么知道的?”岑大權興奮地說:“知道,知道,幾個月前,就聽說過你了,你還去過茂烏隊呢!”張銳說:“那是去幫助所里面的其他同志完成任務。”岑大權說:“對呀,提起你,村里人都夸獎呢!你比下鄉搞農田水利的同志還受歡迎。都說你人長的好,心善良,是我們少數民族的貼心人,到哪家就幫哪家干家務活、帶小孩,還到田間地頭參加勞動,說你是大學生,但一點知識分子的架子都沒有,只要你開稅務會,那些沒有錢的村民借錢也要把稅款交到你的手上。”張銳聽了此話,心里熱乎乎的,忍不住感慨地說:“是呀,想起這兩年,這里少數民族兄弟姐妹對我的工作大力支持,我十分感激,每當餓了,都有熱騰騰的飯菜送上手,晚上,有頭上擦滿了青絲油的姑娘陪我說話,與我同枕共眠。我就在這方圓幾十里的地方,走鄉竄寨,挨家收稅。”岑大權認真地問:“你在我們這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的大山區,真不覺得苦嗎?”張銳淡然一笑:“苦什么?貴州不是有個順口溜:畢節、興義苦喬巴,遵義、黔南一枝花。我工作在黔南這個花鄉,還叫苦呀?”岑大權又笑著說:“你這每天翻山越嶺幾十里,也不覺得累么?”張銳道:“累什么?我看你這樣子,不是也下鄉來工作嗎?”岑大權說:“可我們是在這里土生土長的男同志哦!我們少數民族的人個個都是登山能手。”張銳說:“那紅軍長征中的女兵,不也是一樣,跟著毛主席走到了陜北嗎?”聽了此話,岑大權不住地驚嘆道:“你背井離鄉,來到我們大山中,吃苦受累,不但沒有絲毫的埋怨、委屈,反而樂觀向上,令人佩服!”張銳憤憤不平地說:“我就是要讓人們改變對知識分子,對女人的偏見。這幾年到處都在罵臭知識分子,我們簡直被淹沒在……”張銳的話還沒講完,岑大權微微皺著眉頭,搶
著說:“這種漫罵是錯誤的,沒有知識就沒有人類的進步,知識本身就是力量,你工作這么出色,不就是因為你有知識,有能力嗎?可惜我們這窮鄉僻壤太缺少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了。幸好,我曾在部隊學過不少知識,否則搞農村工作是很困難的……”張銳邊走邊聽著岑大權滔滔不絕的講述,心想:一個少數民族的農民,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認識尚能人木三分,相形之下,那些咒罵知識分子,輕視知識的人是多么渺小、悲哀啊!無形中對這位曾經當過兵的民兵敬佩感更進了一層。
張銳和岑大權走著說著,不知不覺到了一個岔口,張銳指著右前方的公路說:“我該從這邊去唐牙了。”岑大權熱情地說:“從這里到唐牙有一小路,比走公路可節約近一大半時間的路程,你腳扭傷,行走不便,今日我給你帶路,往后,你就從這里去唐牙吧。”他倆在蜿蜒曲折的山徑上一前一后地走著,每到一轉彎處,岑大權都提醒張銳注意路邊的特點。不一會,到了一個斜坡上,岑大權用手一指:“你看,對面半山腰那個寨子,不是你今日要去的唐牙么?”順著他的手尖望去,幾個背著背蔞的婦女帶著銀鈴般的笑聲在山崖邊割著秧青,她們腳下那片被青山環抱的木樓群在翠竹林的不斷晃動中時隱時現,一群頑童在小溪邊嬉鬧,從寨子里延伸出來的青石板路直達大隊辦公的大木屋,它側面的幾棵樹下栓著一大一小兩頭水牛,那頭長著長彎角的大牛似乎看見她,朝著她“哞,哞”叫了兩聲。面對這熟悉、親切而又充滿生機的山寨,張銳高興極了,她連連對岑大權說:“謝謝,謝謝你帶我走這個捷徑,以后,到唐牙來會更快更節約時間了,也謝謝你幫助我趕走了未見著的老虎,還謝謝你幫我治好了腳傷,更謝謝你的是,你正確評價了臭老九。”岑大權微笑著說:“該說謝謝的是我們,謝謝你不辭勞苦在這里為我們少數民族作貢獻。”兩人揮手告別。未走幾步,岑大權又急忙返回,對張銳說道:“如果你的腳還在疼,就到寨子里面用酒揉一揉。”張銳昕他這么一說,感激地朝他點點頭。
張銳在唐牙幾個隊巡回奔走,一段時間后,經常感到渾身不適,這天她實在忍受不住病痛的折磨,決定回城里看醫生。跨進稅務所大門,同以往一樣的是首先把稅款交到所長手里,同以往不同的是沒有急于燒開水燙洗讓身上發癢的沾滿虱子的內衣和毛衣,而是匆匆往醫院跑去,醫生給的診斷書使她更加憂心忡忡,她回到稅務所自己的房間。關上門,吃完藥,便蒙頭睡覺。毫不知情的老所長在門外喊道:“小張,小張,你休息一會兒到我家吃晚飯。”張銳有氣沒力回答:“不了,我有吃的。”老所長又接著說:“老孫病了,你明天不用急著進山,到城關五隊幫老孫收一天稅,剛好明天五隊有人結婚,趁機把以前隊里拖欠的稅一起收上來。那個隊有幾個村民蠻不講理,老孫就是被他們打了的,你看行么?”躺在床上的張銳心想,城關不用爬大山,且當日就可返回,就咬著牙說:“行。”“那你明天就下五隊去了。”屋里張銳又答道:“好。”
第二天早上,張銳吃完老所長媳婦端來的面。又吃了藥,背上稅務包,提著打狗棒,用意志堅持著向城關五隊走去,她穿過集貿市場那塊黃土地,又經過兩條小巷來到城郊,左邊就是通向湖北去的那一圈比一圈高的盤山路,她停住腳望著左邊想了一陣,便又毅然朝右邊那條公路走去。經過一路打昕,終于看到大山腳下那依山傍水的五隊,它被茂密的綠樹重重環繞,進寨的那條路似幽深的古道,兩邊幾棵古樸蒼健的青松像衛士一樣把守著進寨的路口。張銳正在路口張望。幾條兇猛的大狗向她叫著撲來,她一邊揮舞打狗棒,一邊呼叫著。一位老太婆和一個背上背著幼兒的八九歲男孩趕走了群狗,張銳正向他們道謝時,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挑著水向這邊走來,這不是那次在山里遇到的那位民兵嗎?與此同時,岑大權也認出了張銳。當岑大權得知張銳的來由,贊嘆道:“你真是稅收及時雨啊。這位新郎是我內侄,也是退伍軍人,走,進寨熱鬧熱鬧,我擔保該交的稅一分也不少。”張銳慶幸地對岑大權說:“哪里需要幫助,哪里就有你的身影。”
新郎門前的場壩上,一片喜慶氣氛,穿著盛裝、興高采烈的村民們,隨著鑼鼓喇叭聲,載歌載舞。身體不適的張銳隨岑大權在人群中勉強歡笑一陣后,便和隊長、新郎站在僻靜處商討稅收問題。岑大權關切地走了過來,張銳委婉地對新郎說:“看這個熱鬧場面,你至少釀了三十缸酒。殺了兩頭豬吧?”新郎正想討價還價,岑大權立馬搶先說道:“小張同志不會給你多算的。你還是當過兵的人,應該支持國家稅收嘛!”新郎嘟著嘴,用服從長輩的眼神看了看岑大權,然后笑著對張銳說:“等吃了飯,喝了酒再交吧!”岑大權又敢緊說:“早聽說過。小張是寧可不吃飯,也要先收稅的。”無奈之下,新郎只好如數交了稅款。此時,聽見有人大聲喊:“鬧席了!”隊長、新郎和岑大權說:“走。上桌吃飯。”可張銳卻指著花名冊說:“這還有好些拖欠的稅沒交,尤其是那個動手打老孫的,去年就建了房子,至今不完稅。”隊長說:“沒關系,喝完喜酒,我召全寨開稅務會,會上收。”張銳著急地說:“那樣天都黑了。我還要帶著稅款趕回所里。”隊長指著岑大權說:“這位城關鎮里面赫赫有名的民兵連長護送你回鎮還不行嗎?”
暮色已降臨了,山寨一片幽暗,村民陸續從會場走散。張銳收拾好稅務包,又吃了幾顆藥,在岑大哥的護送下,匆匆往鎮里趕去,夜幕中,四面八方的山峰象頂天立地的巨人,溫柔的月光照著河邊那條直達鎮上的蜿蜒曲折的公路。張銳和岑大權即便沒有電筒,也能在滿山不知名的昆蟲的交響進行曲中借著星月光步行。“原來你是鎮民兵連長,可所有的人都尊稱你為岑大哥。”張銳敬佩地說道。岑大權說:“這還讓我感到親切些嘛!”張銳說:“今天沒有岑大哥的幫助。我的稅務包不會裝得滿滿的。”岑大權說:“這都是因為你有知識,有能力,能說會道呀。剛才在會場上,那個有名的劉老大,一開頭就沖著你吼道,‘我是貧下中農,命有一條,鍋有一口,錢可沒有。但你沉著冷靜,幾席話使他口聲軟了,愿意給你打欠條了,在你繼續說服中,他再次退卻,愿交稅款的一半,可你仍然窮追不舍,層層逼進,最后,他只好全部交清。哈哈哈……換另一個簡單粗暴的稅務官,恐怕就沒這個能耐了。開懷大笑的岑大權又接著說:“還有你在會上用城關鎮集貿市場旁邊那一口大井為例。把共產黨與國民黨時期的稅收相對比,使廣大村民真切地明白了,共產黨的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深刻道理。所以那些長期拖欠稅款的人。紛紛掏錢納稅。這一切都說明,你有知識有才干,我挺佩服你的,真的!”張銳卻笑著說:“如果沒有你這位有威望的民兵連長坐在我旁邊。時不時地用表情、神態對群眾作出警示,今日單憑我,效果也不一定這么好呀!我真正應該感謝你喲,真的!”
一陣冷風從山谷中襲來,張銳原本虛弱的身體不禁打了幾個寒戰,順口說了句:“嗨,這夜風還有點冷嗖嗖的呢。”岑大權關
切地問:“你是否生病了。今天見你的臉色較前次差多了,也瘦了不少,精神也象不太好,十分憔悴。又看你在吃藥,你可要注意保重身體呀!我看你胃口不好,不如明日上我家喝喝我家媳婦親自磨的豆漿,吃點二面黃的豆腐,我媳婦是隊里豆腐坊的能手。你上我家來,我還想請你幫我大女兒梅梅找找學習差的原因,你看行嗎?”張銳十分樂意地答應了。
張銳看見前方一片閃閃爍爍的亮光,高興地說:“你看,縣城到了。”剛到集貿市場,遠遠地看見老所長站在稅務所大門那微弱的燈光下,焦急地朝這邊張望,也許是看見了兩個人影。便試探地喊道:“是小張嗎?”張銳急忙答道:“所長,是我!”所長喃喃自語道:“終于回來了。”
所長和張銳站在稅務所大門前,感激地目送著岑大權漸漸遠去的背影。
張銳回到稅務所辦公室,所長立刻歉意地對她說:“小張啊,今天你到五隊以后,我才知道你的情況,你早沒有告訴我呀,從現在起。你不用下隊收稅了,就在城關鎮收,等生了孩子再說。”
第二天,張銳提著一瓶酒,一袋五香花生,尋著城南三隊縣中左側一百五十二號找去,相隔大約十五米遠的距離,她就看見象是剛從地頭回家的岑大哥正在自家放著鋤頭的門邊,用水沖洗著沾滿黃泥的雙腳,同時嘴里唱著:“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張銳暗想,岑大哥不僅大膽勇敢,正直熱情,而且還樂觀開朗。想到此,張銳便喊了聲:“岑大權!”岑大哥回頭看見張銳驚喜道:“小張來啦!我還以為你昨晚隨便答應一句,沒想到你還真看得起農村人喲。”岑大哥話剛落,隨即從里屋走出一位穿著少數民族自織自染的藍白相間的上衣、眉目清秀、俏麗苗條的婦女。她一面摸著自己烏黑閃亮的頭發,一面笑瞇瞇地對著張銳問道:“你就是稅務所的張同志吧,快進屋坐,快!”
張銳跨進高高的木門檻,眼前見著一個大天井,天井右側是廚房、柴房、豬圈,左側有兩個一大一小的房間。岑大權把張銳領到一個小房間說:“那間大的讓給我前年結婚的弟弟住,他還在部隊未回。我家六口人住這間小屋。”屋里除一架破舊的寬木床、一個舊書桌和兩口朱紅色箱子,就只有屋中間地爐上的鐵鍋。張銳奇怪地問:“這屋子里能住下六口人嗎?”岑大權笑呵呵地指著頭頂:“晚上大女兒梅梅和二娃、三娃爬上去睡,四娃和我們就睡這里了。”張銳看到岑大權如此簡陋清貧的居室,想到昨晚在五隊稅收會上。他從身上掏出錢來借給別人納稅;想到他寧愿自己一家六口擠成一團也要讓弟弟住得寬敞舒適的長兄情懷;想到自認識他以來從他身上看到感到的各種優秀品質,張銳欽佩不已,她嘆道:“岑大權真是難得的好人難得的好兄長,如果我有這樣的大哥,該有多好!”岑大錢權欣喜地說:“如果,你不嫌我這布依族的農民又窮又少文化,你就把我們當你哥嫂吧!”一家七口人圍坐在地爐。看著爐邊木墩上的七碗八碟香噴噴的肉和菜,張銳舉起一杯酒,對著岑大權真真切切地說:“我在貴州舉目無親,從此我把你們當成我的大哥大嫂,請你們受我一拜,認了我這個小妹子吧!”
又是一個趕集日,張銳在水泄不通的市場上轉來轉去收稅,突然發現十字路口圍滿了人,她急忙走過去,見一位七十來歲的駝背老太婆背對著一個約三十多歲高個男子哭喪著臉說道:“這是我趕夜工做刺繡的錢呀。”那男人吼道:“你再不拿出來我要搜身了。”說完他倆便拉扯起來。當張銳得知他們是母子倆,那男子名叫吳明,是貴陽大學畢業分到縣中的教師時,心里充滿憤怒。她沖著那教師呵叱道:“你像是老師嗎?”此話一出口,圍觀者紛紛指責吳明,吳明將一雙兇狠的眼睛轉向張銳:“你收你的稅,管閑事干嘛,不看你是個孕婦,老子今天對你不客氣。”說完在眾人蔑視的目光中灰溜溜地走了,那老太婆對著張銳千恩萬謝,并一定要送一雙精巧的小虎頭鞋給張銳,說是給未出生的寶寶穿。此時,正巧岑大權給張銳送豆腐來,得知剛才發生的事,便對張銳說:“銳妹,你做得對,對這種缺乏道德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批。”張銳把大哥送來的豆腐分一半給老太婆,懷著連自己都理不清的心緒返回稅務所。
轉眼進人炎熱的夏天,火辣辣的太陽烤焦了稅務所門前集貿市場的泥土地。剛從街上收稅回來的張銳氣喘吁吁地走進自己房間,脫下發燙的球鞋,光著腳丫靠坐在床架上,扇著扇子歇息,一扭頭看見窗外大嫂手里提著口袋向稅務所走來。大嫂一進門就奪過張銳手上的扇子,坐到張銳床邊說:“來。我們一起扇!”她邊扇邊說:“你大哥催著我給你帶些糯米耙來,吃了可養人,你多吃點呀,你一個人吃的是兩個人的飯啊!”扇了幾下,大嫂站起來,“我今來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給你把床單、蚊帳拿到河里去洗,這是大哥的命令。…‘你大哥說夏天汗水出的多,你們城里人愛干凈,你在這山溝里面,身體又不方便,愛人又不在身邊,還要忙工作,真是夠苦的,咱哥嫂不心疼你誰心疼你呀”。聽到這樸實真摯的話語,張銳心里酸甜酸甜的。
張銳站在高高的河坎上,低頭望著河邊使勁捶著衣物的大嫂,心里感動地喊著:“我的大哥,我的大嫂,我在貴州的親人!”
嫂子晾好了衣服,臨走時,東張西望看看周圍沒人,便拉著張銳的手輕聲說:“銳妹呀,我想給你說點事,你就不能夠調到縣中去教書嗎?梅梅和二娃不是你,他們這學期考試會有這么大的進步嗎?連周圍鄰居的孩子都說你講的課比學校的老師還好,你會講語文,還會教物理、化學,而且當老師又有兩個假期,到縣中離我們家又很近,咱哥嫂也可以更好地照顧你和小寶寶,你總不能生了孩子以后又背孩子去大山收稅吧。”
傍晚,張銳吃著嫂子送來的糯粑,獨自坐在稅務所側面的河畔上乘涼。落日的余暉灑在河水中,照亮著她的思緒,左思右想后,張銳決定向縣委組織部申請調動。
經過反復周折。稅務局終于同意了張銳的調令,但誰也沒有想到,進入縣中的那幾年競成了張銳這一生中最凄苦最憤慨,也是最自豪的幾年。
張銳到縣中上班的第一天,中午時分,大嫂已做好了飯菜等她吃午飯,左等右等也沒看她回來。大哥正準備叫梅梅到學校找姑姑,就見張銳滿臉怒氣地進了門,哥嫂急忙上前問究竟,張銳“哼”了一聲說:“真是冤家路窄,大哥你記得那次在集市上被我當眾指責的吳明老師嗎?”大哥應道:“記得,他的媽常到店里買豆腐。每次趕場,她都要從我家門口經過,她見人便說吳明對她不孝。”張銳輕蔑地一笑說道:“這種人竟然是我們綜合教研室的主任”。大哥一家十分詫異。張銳接著說:“他想給我下馬威,第一天就刁難,把學校給教研室批林批孔的講座任務放到我頭上,而且時間就在明天上午。就一個晚上的時間準備。我找辦公室打聽,除了幾張報紙,什么參考都沒有,我總不能憑空亂講呀!”大哥大嫂聽了也傻了,見大哥大嫂著急,張銳反倒安慰說:“怕什么,我就要他們知道巧媳婦能為無米之炊。大哥,你下午幫我到鎮上借今年的紅旗雜志,我手上借了幾本歷史書,再加上報紙上的觀點,我今晚就
下,流出的滾熱淚水;而面對假丑惡,張銳卻呈現出另一種迥然不同的形象,她憤怒呵斥,百折不撓,頑強抗爭,誰在她臉上也看不到一滴淚水和屈辱的表情。這一天晚上,因為春兒生病。張銳便背著她去參加批判會,不料天空下起雨來,散會后,雨落得更大了,老師們打著家人送來的雨傘回家了,有的家人沒送雨傘來也被有傘的老師一起帶走了,可誰也不敢叫張銳同打一把傘,誰也不敢對她關心的問上一句話。她背著春兒孤零零地站在會議室的大門口,望著茫茫的雨地。突然,不遠處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她的視線里。隨即聽見“銳妹”的喊聲,“我的大嫂送傘來了”,她急忙上前接過大嫂給她撐開的雨傘,淚水長流。
一天傍晚。大嫂和張銳正在給哭得喘不過氣來的春兒喂藥。望著春兒那張蒼白的小臉,想到這些日子飯沒有給她喂飽,藥卻灌了滿肚,張銳心如刀絞。這時大哥進來了,張銳欣喜道:“你回來了!”大哥說:“回來辦點事,明天又要下工地。”說話間,他一眼看見床上的春兒,心疼地問:“怎么這幾個月,春兒瘦成這個樣了?”又回過頭問大嫂:“你是怎么幫著照看她的喲?”大嫂不說話,只是撩起衣角擦眼睛。
當大哥得知情況后,氣得把桌子一拍。說道:“真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這幾年學生經常開會勞動,學了些什么科學知識?已經這樣了,還在鼓吹考試打零分的張鐵生,大呼小叫教育形勢大好特好,反而說實話的竟成了右傾翻案典型,太不象話了”。這時,梅梅突然進屋來,對著張銳說:“姑姑,吳明帶幾個學生來叫你去開批判會。”張銳對大嫂說:“嫂子,請幫我看一看春兒,我去開會了。”大哥一下站起來,說道:“不去,今天你就在家照料春兒。”然后走到大門口,目光如炬,沖著一群來者吼道:“誰來叫張老師開批判會?”吳明見學生嚇得躲躲閃閃,不敢吭聲,便大模大樣走上前,答道:“學校領導!”又接著說:“學校領導也是奉教委的指示。”大哥說道:“什么領導,什么教委,明明是你想落井下石,以泄私憤,你們回去告訴學校,張老師根本就沒有錯,該受批判的應該是你們。”同時又指著那幾個學生說:“你們不好好學習,沒有知識,沒有文化,憑什么去喊超英趕美。”
學校認為張銳態度太頑固,太放肆了,決定第二天在大操場召開邀請縣教委領導參加的全校性的批判大會,對張銳的右傾思想進行公開批判,并宣布對張銳的處分意見。
張銳認真地對大哥說:“哥。你明天一定要參加大會后再去電站哦,我馬上到縣城的大街小巷去貼昨晚我寫的幾十張大字報。公布今日下午縣中公開召開批判張銳的大會,敬請全縣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尤其是學生家長,務必參加,因為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要呼吁全社會的人都來關心教育,評判教育,一定要把這個錯誤的批判大會變成激烈的辯論大會,把被審判的人變成審判者。”
果然,社會上的群眾看了張銳的大字報和海報,有的懷著好奇心,有的憑著正義感。紛紛聚集到貼滿大幅標語的批判現場。會上,張銳看著象鐵塔一樣站在人群里的大哥,心中又踏實又興奮。她胸有成竹,侃侃而談,擺實情,講真理,用正義言辭把批判者們的發言駁得體無完膚。全場群情激憤。教委領導當場責令校長宣布散會。
這次批判和反批判大會驚動了縣委,縣委領導肯定了張銳的言行。從此在縣中,誰也不敢再提張銳是右傾翻案典型的話語,也再沒有誰敢說批判二字。
為了骨肉團集,張銳要帶著春兒調回湖北了。
九月的夜空,滿天星斗,大嫂坐在高高的木門檻上,抱著熟睡的春兒,張銳坐在大嫂身邊,望著縣中操場上開批判會時掛著大幅標語的白楊樹和樹后面那排她與春兒住過的平房,思緒萬千。看著屋里忙著給張銳收拾行裝的大哥,大嫂難過地說:“你們回湖北了,我和你大哥會很不習慣的,會很想念的。”張銳含著眼淚說:“我也一樣。春兒長大了,定不會忘記是大舅媽的豆漿把她救活養大。”
夜深人靜,張銳悄悄從床上坐起,從行李包拿出筆和紙,打著電筒寫道:親愛的大哥大嫂。我和春兒要回湖北了,但心里實在舍不得你們,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幾年,你們對我象親人般的關懷體貼,忘不了你們在我最困惑的時候給我勇氣和力量,讓我和幼小的春兒重獲新生,分別之際,我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這塊手表就留給大哥出門工作時用吧,愿大哥大嫂全家幸福快樂!張銳寫完信后,就把手表從手上取下來,和信一起放進牛皮信封里。
長途車站的汽車頂上,大哥正在給張銳捆綁行李,大嫂帶著離別的憂傷,不斷撫摸著春兒那枯黃的頭發。此時,聽見司機大聲喊道:“上車了,要開車了!”只見大哥從車頂上跳下,向張銳這邊走過來,張銳想到與大哥大嫂這一分別,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見,她使勁地盯著大哥大嫂,想要把兩個親人的面孔印在腦海里,盯著盯著,無法再鎖住的淚水象大壩決堤一樣沖了出來,她把那裝著感恩的牛皮信封遞到大哥手中,從大嫂懷里接過輕瘦的春兒,激動地喊道:“大哥大嫂,再見了!”
車徐徐開動了,張銳拉著春兒那細小枯瘦的手,向站在窗外的大哥大嫂喊道:“大舅舅,大舅媽再見!”這一瞬間,張銳清晰地看見,流著淚水的大嫂和紅著眼圈的大哥揮舞著手臂,異口同聲地喊道:“路上不給春兒喝冷的,吃糯的,到湖北后,趕快來信哦!”車加速了,爬山了,張銳回頭望去,見大哥大嫂還依然揮著手,呆呆地站在那里。汽車沿著盤山路,越轉越高,直到駛進茫茫的群山之中。
“鴻雁”不停地飛落在黔南山脈和長江三峽兩地之間,將漢妹和布依哥嫂的親情頻頻傳遞……
同樣也是三月的一天,寒氣未盡的春風一陣陣掠過那所幽靜的綿羊山學校,正在看書的張銳突然聽到喊聲:“張老師,快去取掛號信,貴州來的。”一聽是貴州來的,她欣喜地放下書,自語道:“布依哥的信,肯定是四娃真的當兵了,有剛入伍的留影,不然,怎么會寄掛號?”
信封上并不是大哥那熟悉的筆痕。卻是梅梅那歪歪扭扭的字跡。她急忙打開信看:親愛的姑姑,您好!寄來的掛歷和糖果收到了,媽媽催我給你寫信,你和我們分別十幾年了,可一直都想著我們,我們實在太感謝了,只是今年過年,爸爸沒有象往年那樣吃著你的糖。他老人家年前因公犧牲了……讀到此處,她不相信自己眼睛,又反復讀了兩遍,腦子里轟轟直響。睛天霹靂!她喃喃道:“不,這不是真的,不會這樣,大哥才59歲,還要為寨子里的父老鄉親做許多好事,為山鄉四化建設作許多貢獻,還答應過到葛洲壩來參觀呢!”
站在高高的綿羊山頂,望著西南方向,張銳淚如雨下,她透過翻滾的云層尋覓著黔南山脈中的恩人布依哥。
責任編輯: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