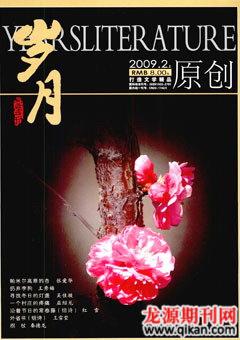風,刮在記憶里
路來森
1
抬起頭,就能看到對望的山,再拉近,是一塊平展展的土地。我知道,在山和土地之間,還有一條河,一條不大的河,優雅地在那兒淌著。
山的名字叫“藥王山”,據說,是藥王孫思邈途經于此,脫履叩土而成,傳說很迷離,很美麗,像所有的傳說一樣。山并不高,但它躺在一塊平原上,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山了。
很多事物是相對而存在的。
那幾年,在S中學工作時,我常常會凝望這座山。不是因為憂郁,而是因為我臨窗而坐,抬頭,即觸目可及。窗口的玻璃很亮,若是稍蒙塵埃,我便會趕緊揩拭,所以,我總能透過明亮的窗口,看到一座明亮的山。
那一個個的初春,太陽總是懶洋洋的,像剛從昏沉的夢中醒來,光線,慘白中透著一種淡黃,軟綿而又無力。可它,竟也把滿山的積雪漸漸消融了,它是用一只少女般柔軟的手去觸摸的,觸摸的柔情感化了經冬的積雪。山便露出一些斑駁的影子,便瘦削下來,靜靜地孕育、滋長著一場潮涌的綠。
山綠了的時候,我會常常上山,只是因為喜歡攀登,喜歡那種攀上山頂后,優游的感覺。浮云,樹木,飛鳥,清風,人行山上,像風一樣輕;心,比風還輕,有一種飛揚的感覺,濁氣從腹腔中逸出,丹田沉下的是一種綠意濃濃的清新的力量。
那一年的春天,好像是剛剛給學生教過張潔的《挖薺菜》,我上山,也挖回了一兜薺菜,綠瑩瑩的,很肥碩,我很得意。同事走近,說不是薺菜,只是形似,不信嘗一嘗。我拿一棵,放口中一嚼,苦不堪言,只好牽障然扔掉,我知道薺菜是不苦的,苦的當然就不是薺菜了。后來我知道,薺菜喜歡濕地,山上不濕,山上難以生長薺菜。
可不知為什么,我后來總是把這座山和薺菜聯系在一起,當這座山綠著的時候,它青靈靈的,是一棵正在生長著的大大的薺菜。真相和假象,你怎能徹底辨清?
又一年的春天,我工作的這個地方隨著時風,興起了一陣“造神”運動,各地的廟宇、祠堂,云一般紛然涌起。據說,藥王山上原先是有一座廟的,就叫“藥王廟”,文化大革命時被拆了,被砸了。藥王死在了山上,可并沒有在人們的心中完全死去,所以當“神風”刮起的時候,山下村民的心也被刮活了。他們自動籌資,想在藥王山上重建藥王廟,重塑他們心中的神。
終于動工了,一天的時間廟宇的屋墻就建得很高,可一夜過后,建好的墻基就又被拆除了。后來知道是鄉政府派人拆的。當時的政策尚不明朗,鄉政府既怕上級政府的斥責,又不敢觸怒民意,于是只好出此下策,現在想來,只是一個成為談資的笑話而已。村民不服,又建,于是,又拆,像扭麻花一樣,扭來扭去,幾經周折,到底沒有建成。畢竟,建的不如拆的快。
廟宇最終沒有建起來,藥王山的山頂只留下了一堆落寞的磚石。山上還栽E了幾棵火炬樹,秋末,經霜的火炬樹葉,丹紅如血,流淌似霞。
藥王沒有了家,只好成了一位“游神”。可“游神”也是神,他到底還是在民眾的心中“活”了。
于是,這座山上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了“廟會”。每年的農歷四月初八日,四鄰八鄉的人家,甚至遠至百里之外的人家,都會聚集到這兒“趕”廟會。向藥王叩頭膜拜,祈求一生無病無災,平平安安。我的一個遠房嫂子常在廟會上“跳神”,手舞之,足蹈之,口中念念有詞。驚得那些年老的婦人,匍匐于地。每個人,都應該有自由表達的權利,相信的,看作是神;不信的,看作是“戲”。戲是人演的,人生本如戲。
山上,人山人海;路邊,坐滿了擺地攤的人家。火了藥王,火了山,也火了生意人家。一派升平的祥和景象。
人們終于明白:神是不需要家的,神的家就安在人的心中。
山不在高,有“神”則靈,則名。藥王山成了一座“神山”。
有鷹在山頂上盤旋,是“神”的昭示嗎?
2
“藥王山”下,就是那條小河,小河在山腳下拐了一個彎,形成了一片灘地,灘地歷久年深,就長成了一片小樹林。
所以,沿河灘散步,在那幾年里,就成了我和幾位同事的確定生活方式。
河的名字叫“朱河”,它究竟發源于何處,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它最后是流入白狼河的,而且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它那深邃的河水中,或許還流淌過戰國的風云和秦漢的嘆息。這是有歷史遺存可證的。沿“朱河”—溜河沿,分布著七個“淳于村”(依次為:楊家淳于、秦家淳于、趙家淳于、丁家淳于、龐家淳于、尹家淳于、孟家淳于),民間傳說,這七個淳于村,是戰國滑稽之士淳于髡的七個女兒,下嫁于此而形成的。河的上游,有一座不大的小山,名為“夫子山”,據說就是淳于髡的墳墓,“夫子”是對淳于髡的尊稱。至今,周圍的鄉民仍不會從“夫子山”上取石蓋房,就因為那是墓石。而淳于髡,史上是確有其人的。《史記·滑稽列傳》的第一個人物,就是記載淳于髡的。并且對其評價極高,傳曰:“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且有“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的豪氣。
所以,每次散步于河岸邊,我都感受到腳下土地的厚重;篤篤的腳步聲,似在聲聲叩響戰國的門環。仿佛輕輕一拉,你就能走進歷史的風煙深處。
河沿散步,理想的季節是春、秋兩季。
河沿,河灘,栽種的大部分是楊樹和柳樹,它們是對季候最敏感的樹木。當春風吹拂的時候,你透過辦公室的亮窗,就能看到春天在枝頭發芽、生長。鵝黃,嫩綠,生命蓬蓬勃勃,很快就變成了濃碧的蒼翠,就成為了一種溫馨的誘惑。
于是,我和幾個相知的同事,便常常在課外活動的時間,欣然接受這種誘惑,散步于叢林、河畔。其時,晚霞斜照,嫩碧的樹葉,跳動著暈黃的光圈,迷離恍惚,仿佛正在努力編織一個金色的童話。河水潺潺,如人在私語。路上行人稀少,間或有農人牽著下地的黃牛走過,黃牛扭起大大的腦袋,發出哞哞的叫聲。人行其中,內心一片寧靜、祥和。
于是,這個世界就成了你的了,你把春天摟進了自己的懷抱之中。
有時,你會覺得,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你的身體中涌動,你直想張開口,發出大聲的呼喊,像魏晉名士那樣,作一次林間長嘯,縱不能聲震寰宇,響遏行云,也可一抒心中塊壘,讓春天,帶走心中的不快。所以,每次散步,就是一次心靈的愉悅,就是一次精神和靈魂的洗禮。
于是,我把這一條小河,這一片小樹林,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散步,成為了我生命的舒緩的節奏,小河、樹林、散步,共同構成了我生命之中,一副情景交融的畫面。
有一年的秋天,忽然流傳開一個消息,說是要在“朱河”岸邊的土地上,沿河挖水池,栽種蓮藕。我知道,這又是在搞一個“政績工程”。那一個時代,各地的鄉鎮領導熱衷于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前任書記剛搞了“大棚工程”。新上任的書記,絕不重復,標新立異,又要搞“蓮藕工程”,于是,當地的老百姓形象地,順口溜道:“一個要上天,一個要入地。”
現在可以公正地評價,“大棚工程”是很成功的,后來,老百姓受益頗大。但“蓮藕工程”卻不了了之,只在“朱河”下游,留下了幾個破爛的
池塘,里面堆滿了干裂的淤泥,像是張著幾張扭曲的嘴,在向天哭泣著。但遺憾的是,天道不公,真正留下政績的書記英年早逝,而那個“爛攤子書記”卻依然健康地活著。這極易讓人想起,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中為伯夷、叔齊鳴不平的話:“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矣?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信哉,斯言!
值得慶幸的是,學校前面的一段河沿,安然無恙,或許是得益于兩岸沒有肥沃的土地,只有裸露的石山,砂石灘地。不管怎樣,這段河流,這一片小樹林,還是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也保存下了鄉民們那祖祖輩輩的記憶和往事,那塵封千年的風云和歷史。
我可以繼續散步于河沿邊,享受那熠熠秋陽的朗照。看秋風里,落葉飄零的景象,感受“風蕭蕭兮木葉下”的無際的蒼茫和凄涼;看夕陽之下,下坡的農民,拖著疲憊的身體,行走在河沿邊,鋪下長長的憂郁的影子。可以仰躺在松軟的枯草上,聽秋風穿林渡水,聽落葉低吟嘆息,聽秋蟲婉轉鳴唱,品味天籟的絕響;我還可以,靜靜地坐在小河邊,看水中的游魚,逆流而上,用力地擺動著自己的尾巴,旋起蕩漾的漣漪。觀賞水中荇萊,那幽幽的生命的碧色。
總之,這一切,都會帶來身心的安靜、自由和喜悅。說“天人合一”有點冠冕,但確是有,-一種人與自然交融的至高享受。在這樣的情境下,你還會有什么煩惱可言呢?你還會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呢?你怎能不感謝生活對你的恩賜?
所以,當我已離開那一條小河,和那一片小書對林若干年后,我依然記著它們,我要捍衛自己的記憶,捍衛記憶中那些往事。不是說:捍衛記憶,就是捍衛歷史嗎?
3
—塊土地,是有自己的話語的。
它的話語,只對知己去談。那些終日面朝黃土背朝天,臉色黝黑,弓腰駝背的人就是它的知己;那些在土地上流的汗水最多的人,就是它的知己,它會用豐厚的果實作出殷勤的回報。它和他們總有一種心的交流。
在有些季節里,土地是沉默的,無語的,但我知道,皇天后土,沉默和無語也是一種話語,先人說:大音希聲。
可沉默不會是永久的,當春天到來的時候,土地就會發出生命的呼喚。
于是,它的知己——那些勤勉的農人,來了。他們,拖著兒,攜著女,牽著黃牛,扛著犁鏵,來到了這塊土地上。
黃牛套在了犁鏵上,女人在前面牽著,漢子在后面手扶著犁鏵。咿喇阿拉,吆喝一聲,黃牛就走動了,女人就走動了,犁鏵就翻滾了。也許旁邊會跟著一個孩童,或者后面綴著一頭牛犢,一條黑黑的狗子前躥后跳地環繞著。于是,土地就被翻起了,新鮮的泥土散發著一種春天的味道,是土地醒來后打著的呵欠。扶犁的漢子,一邊前行,一邊還不時地低下頭,用他那粗糙硬實的大腳,踢碎板結的土塊,咔啦一聲,你就聽到了大地碎裂的聲響。
一段時間之后,翻起的土地就連成了片,迎著陽光看去,明晃晃的,土地睜大了它明亮的眼睛,敞開了它寬廣厚實的胸腹。犁地的漢子禁不住俯下身子,用手攥起一把土,然后又松開,土便從他的手指間流下。漢子笑了,“多好的墑情啊!”他心里默嘆道。土地也笑了,它在為自己的知己而笑。
累了,漢子便把犁鏵停了下來。犁鏵插在了地頭上,黃牛伏在了地邊上,漢子歇在了田埂上。土地上插起了一幅雕塑。漢子裝上一袋旱煙,吧咋吧昨地抽著,女人順著陽光,幸福地看著自己的漢子。煙鍋里的煙,悠悠地飄著,飄著,一絲絲,一絲絲,女人順著煙絲看去,看去。她看到了高高的天空,她感到,天空好大好大。
那幾年里,我就常常走出校門,站在這塊土地的邊上,看這幅動的畫面,觀這幅靜的雕塑。
這讓我常常想起我的父親。每當他耕地休息時,他總是習慣性地取一塊石塊,去刳犁鏵上的泥土,一邊刳一邊還不停地告誡我:“記住,讀書如犁地啊!”是的,我記住了父親的話。
以至于后來,我覺得,我的耕耘始終是扎根于泥土中的,總有一種泥土的味道。
這讓我變得越來越親近土地,更加經常和用心地去凝視土地。
站在這塊土地邊上,我不僅看農人對它的耕耘,更看農人對土地的收獲,收獲時,土地的那種飽滿、豐盈,農人臉上的燦爛和張揚:我甚至于更喜歡土地收獲之后的那種蒼涼,一種干干凈凈的純粹。
赤裸裸地,土地現出了它最本色的一面。
但我更愛,愛一塊土地是沒有理由的,只要它是土地就行了。
若干年后,我還想著那座山,那條河,那一塊土地。像風一樣,刮在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