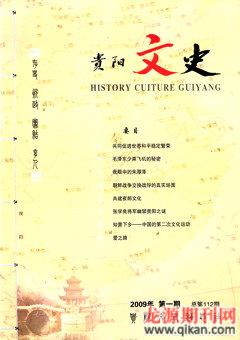送錦濤去西藏
葉 辛
月初那幾天里,聽到一些隱隱的傳言,說錦濤最近在西藏,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心頭便猜測,錦濤是不是要調往西藏去。僅僅過去十來天,消息傳出,錦濤正式調任了。
在他臨行之前,作為普通朋友,我和由青海調黔的全國青聯常委廖泰泉同志等去駐地看他,表示一點相送的意思。他來得匆忙,1985年5月,我赴京參加國際青年年活動,團中央盛傳他要調動的消息,我問他,他說至少還要穩定半年。但是7月初,就有消息傳到貴州,說他將出任省委書記,不日即要上任。
這一回,他去得也匆忙,中央決定他調任西藏工作。于是,他便要走了,不日就要啟程。
從他那里回來,和他交往短短幾年中的一些往事,歷歷在目。夜寧靜,屋內沒有火,久坐便相當冷,但還是忍不住提筆寫下這篇文字:送錦濤去西藏。
記得是1983年的夏天,我去參加全國青聯和全國學聯的代表大會。氣候炎熱,列車上休息不好,到了北京國家民委招待所,匆匆吃過飯就想沐浴睡覺。這時候錦濤和團中央的幾位書記到各個房間來看望各省來的同志。我這才知道團中央也完全是一套新班子。經介紹,我和錦濤相識了。那時他比現在清瘦,顯得精明強干,年輕英俊卻又平易近人。來自新疆的尼相同志告訴我,他們沒顧上吃飯便趕來看望大家。會議期間,可能是職業習慣,我觀察新上任的書記們。我發現錦濤開會簡明扼要,講完就散會。個別有具體問題的同志,可以留下來與他繼續交換意見。第一次開青聯常委會時,他那樸實干練的作風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在這次大會上,他繼胡啟立同志之后,出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
1984年秋天,一個星期天的黃昏,團省委一位同志跑到我家里,說錦濤下午剛到,并提出去“葉辛家看看”。團省委的同志建議我主動去賓館看他,晚飯后我便匆匆去了云巖賓館,服務員同志說他出門散步去了,讓我稍等,隨即又告訴我,給他安排的大套間,他沒住,提個包,主動和秘書小葉住兩人一間的普通客房。正說話,他和小葉回來,見面便說不是講我去看你嘛,怎么你來了?說著還是執意要去我家看看。講話時省委書記朱厚澤同志到了,他們是中央黨校的同學,聊了片刻,朱書記便用他的車送錦濤去我家里。那年我的孩子不到5歲,他看見長沙發上坐了兩個客人,先是在小葉身上爬,然后又爬到錦濤身上,弄得坐在對面的我感覺很狼狽。不料錦濤把孩子抱在膝上道:“你這一爬,爬得我不好意思了。伯伯應該想到,還有這么個小主人,給你帶點禮物來。”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我略顯拘緊的神態也隨之消失了。
這是他第一次來貴州。以后的一個多星期里,他坐著車一直在苗鄉侗寨、在地州縣跑,和基層的團干部們座談了解情況。國慶節那天,省青聯有個聯歡晚會,他從黔東南風塵仆仆趕回貴陽來到會上。我問他對貴州有什么感想。他說:山水很美,各族人民勤勞樸實、熱情好客。當然也窮……
我心里說他看得很準……
1984年冬天,照例開一年一度的全國青聯常委會。由于航班原因,我遲到了一天。夜里趕到會議駐地,全國青聯秘書長告訴我:錦濤今天是抱病來發言的,他問過兩次了,你來了沒有?這不是他對我特別關照,常委們的臉他都記熟了,開會時目光掠過會場,發現有缺席的同志,他都要關心地問一聲。
在青聯常委會里,有很多全國著名甚至馳名世界的學者、科學家、教授、作曲家、專家、演員、表演藝術家、畫家……要讓這么些人由衷地從心里真正敬佩服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錦濤離開青聯幾年了,不少常委們一年一度相見時,仍要懷著感情談及他,對他樂與各界人士真正地交朋友,對他的為人和作風,表示衷心地欽佩。其實豈止是青年朋友,前幾天遇到一位幾十年在組織人事部門工作的老同志,感嘆地對我說起:“有些時候,把一個同志從這里調到那里,我們都要費老大勁兒。看人家錦濤,到西藏,說走就走了。在這方面,錦濤同志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1985年早春,我將出訪斯里蘭卡,到京集中的時候,發現代表團里人數多,且有好幾位比我年長的同志,有的已有八次出國的經歷了。我便想找找他,辭去團長職務。不料他聽說后,馬上表示:我來你們房間,我來我來。我們剛吃完早點,想上樓去他辦公室,他先來了。我說了自己的想法,他不以為然地一擺手:“正因為年輕,才需要鍛煉嘛。你怕啥?”接著他給代表團全體同志介紹了自己剛出訪日本回來的一些感受,并且說:大方一點,時時想著你代表的是中國當代青年,身后有祖國撐腰,沒什么可擔心的……
他和我們交談,沒有領導的架子,沒有領導的口吻,完全像一位朋友似的,推心置腹。代表團里幾位北京歌舞團的小青年,等他一走馬上急切地向我表示:你們青聯收不收新成員,我們要參加。
好幾位青聯委員都笑了,朝鮮族長鼓舞演員許淑說:“瞧,好的領導干部,短短的一席話,就能打動年輕人的心,吸引青年人。”
1985年7月,正值盛夏,錦濤到貴州上任了。記得他好象是7月19日到的,7月22日給我們掛電話,說他住下了,讓我有空過去坐一坐,聊聊。
幾天后的8月3日晚,省青聯的一個夏令營開營式那天晚上,省軍區大操場上坐滿了青少年,錦濤和一些領導同志到了。好些同志都列隊站著,想看看新來的省委書記什么樣兒,我和貴大校長李祥站在一起,耳朵里灌滿了“年輕,真年輕”的嘖嘖之聲。
他一眼看到我,嘴里“唷”了一聲走過來,我趕忙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向他表示歡迎。他說:“咱們是朋友。”我說:“不,這回是名副其實的領導了。”大伙兒都笑。
這以后,我在貴陽就時常聽說錦濤的行蹤了。在我記憶中,初來乍到那段時間,他經常在下頭跑,坐著一輛面包車,邀上當地的縣委書記,在車上一邊聽匯報,一邊就隨處觀察,熟悉民情,了解情況。到了哪里,就住在那里;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吃頓飯。他身邊的先后兩位秘書都跟我說:隨便得很,弄得我們反而緊張,怕在安全上出問題。
剛來那兩三個月,去他那里聊天,我還可以向他介紹貴州的情況;幾個月之后,又和他見面,往往都是我聽他介紹貴州的形勢和近況了。而且了解到的情況往往很細致、很真切。他同我談得最多的,就是治窮、扶貧、貴州的開發這樣幾個問題。當然有時也談點諸如文學、我在寫些什么一類話題。從我這方面來講,和領導同志相處,當一個下屬是最容易的,只需要帶雙耳朵去聽就行了;當一個朋友卻不易,既要講知心話兒,又不能借機去說三道四。不過,只要在群眾中聽到正確的意見,我還是及時通告他。比如有一回,一張報紙上出現“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胡錦濤……”怎么怎么,群眾中有議論,我對他說了。他沉吟片刻,
說:“這個意見是對的。以后不能這么登,我給他們說。”
我記得,那次全國的兒童文學座談會在花溪召開。上海少兒社的同志半夜找到我家里,希望錦濤同志去會上說說話。第二天一早,我硬著頭皮去闖他的辦公室,還想好一點措詞:這次來的有《小朋友》雜志創始人陳伯吹,有在全國少年兒童中影響很大的《少年文藝》、《故事大王》、《十萬個為什么》的主編和編輯,有老中青三代的兒童文學工作者,有幾個你的老朋友,你是全國少工委主任,又是省委書記……他聽完以后笑了,說:“你這么講,我去。明天下午去。不過不去開會,不要約電視記者,就是和大家見個面,隨便聊……”
第二天下午,他果然去了,在大家熱烈鼓掌催動下,他講了幾句和少兒工作、兒童文學有關的話。講在點子上,后來省報和全國好幾家報紙都全文發了他這篇簡短的講話。
一晃眼三年過去了,我正寫作一本當代中國農民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命運及遭際的長篇小說。他下去視察機會多,幾次我都想隨他一起去走走,以彌補我面上生活的不足,他也同意。但我仔細一想,還是沒跟他去,不給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像這篇文字,如果仍在貴州,我是決不可能寫的。
作為普通朋友,我知道錦濤的一些難處,是不為一些人所理解的。比如,錦濤的家屬沒有來貴州,人們總是有看法的,總認為他干不長、不安心,不是真正扎根。但我知道,他的家剛剛搬進北京,老岳母有病,兩個孩子,一個面臨考大學,一個面臨考高中,總得設身處地替人家想想。再說,到了他這一級干部,一切聽命于中央。中央讓他在貴州干一輩子,他家屬不來,也得在這里干一輩子。中央要調他,他的家屬來了也仍1日得走。
聊以自慰的是,錦濤到貴州的三年多時間里,我從來不曾利用自己和他相識這層關系,謀過任何私利。倒是從他那兒,我學習到不少東西,受到過不少教益。和他相處,我更多地感覺到他是一位兄長,一位良師益友。
錦濤要走了,在那間我們時常坐著聊天的客廳里,堆滿了二十幾只紙板箱,全部都是書。來送行的同志很多,一個多小時里,幾乎是川流不息,我們不可能像以往一樣長談。他的肩上卸下了一另擔子,又挑起了另一副擔子,在某種意義上說,新的擔子更為沉些也重些。談話中,他已習慣地講起西藏一百二十二萬平方公里迷人和奇妙的土地,講起二百多萬人口的那片土地上的生活。如同初來時講起貴州一樣。作為一個朋友,除了愿他“保重”,我想不出更多的話來講,他囑我們代向青聯的朋友們辭行,他送我們到門口,握著我們的手說:“咱們后會有期。”
責任編輯:管遠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