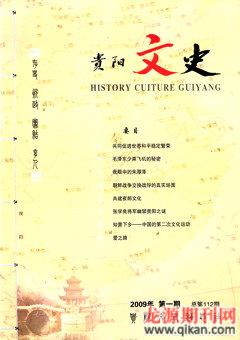我眼中的朱厚澤
(四)
朱厚澤作為省委書記與省委機關報的關系,在他跌宕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我躬逢其盛,在我一生新聞實踐經歷中卻占了重要的有意義的一頁。
朱厚澤堪稱是一生從事思想理論工作的宣傳家。他的新聞觀點是他的政治、人文總體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指導省報工作,固然也常有指示、批評、表揚等日常性的及時指導;但他更重視給報人以思想指導,重視啟迪報人領會中央指示的精神實質,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宣傳。他最反對報紙只會照抄照套,人云亦云,隨風轉向,忽左忽右,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比如,1985年有一段期問,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某種“過速”和“失控”問題。中央加強宏觀經濟調控,有些基建項目和企業要下馬,強調“令行禁止”。省內外報上一片“剎車”聲。朱和我談話時說,報紙宣傳不要一陣風,要有穩定性、連續性。比如“令行禁止”,要區別什么是中央的改革開放總號令,什么是一時一地的具體指令。他比劃著手勢著說:像水龍頭一樣,水大了要關點閘,但不要關死總閘。應該是哪個“龍頭”漏水就關哪個,不要再“一刀切”、“一鞭子趕”,來個全體“急剎車”。西南大部分地區是中國的內陸淺腹地,它的開發能緩解全國尤其沿海能源、原材料等的緊張。能源、交通仍是中國經濟的“瓶頸”,因此貴州與西南的能源、交通發展不是過快而是不夠。貴州的問題就不是什么“過速”和“失控”,而是如何繼續搞活經濟,并盡可能加速資源開發和充分發揮現有經濟技術基礎的潛力。這是貴州的省情。他希望報紙宣傳要把握這個指導思想。他較少給我布置具體報道題目,常常循循善誘,讓你自己去思考,把報紙辦活。
時間隔久了,往事多已淡忘。近日翻出舊筆記本,忽見1984年9月9日的幾頁筆記,細讀一遍,好像發現“新大陸”,原來朱厚澤還說過這么系統的辦報意見,我竟讓它沉睡在舊紙堆中整整20年。現特全錄如下:
“最近厚澤同志找我談了兩次,一次二小時,一次四小時,探討報紙宣傳和思想戰線問題。沒有紀錄,漫談式的,據我個人理解,大體涉及以下若干問題:
一、報紙要堅定不移地抓住主題,無論如何不要沖淡主題。
在這方面,要善于把省委許多部署和要求,有節奏地、有機地安排好,掌握好宣傳藝術、宣傳火喉。注意讀者心理和情緒。不要來什么就突出什么,畸輕畸重,忽起忽落。宣傳的主脈絡、主線,應當一直貫穿著黨的總目標,總任務,黨的工作重點和主題。
比如。宣傳徹底否定“文革”,與宣傳主題,不矛盾,但不能形成造輿論的感覺,宣傳節奏要拉開些,不要搞連篇累牘。(筆者按:回憶當時談話時,他還舉本報發的省委清查辦公室撰寫的清查“三種人”的評論,連發了三篇,他認為應拉開些。不應造聲勢。)
又如,有些好事,可以做,不宜公開宣傳。8月24日,他在黔府(1984)67號文件上批了如下意見:
‘是哪個通知電臺和報紙廣播、登報的?這類地區性的作法,何必要弄到天上、報上去唱呢?請德政(注:當時省廣播電視廳廳長)、學洙把好關。(按:是指貴州對離退休干部增加補貼的事)
二、報紙宣傳如何適應商品經濟大發展的要求,大幅度地調屁股,搞好新聞改革和報紙改革。
研究貴州發展戰略,要研究一個縱的方面,一個橫的方面。從縱向看,貴州經濟發展究竟處于什么階段,什么情況。落后地區要實現四化,更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從橫向看,即地區經濟和全國經濟、世界經濟的關系問題,我們處于什么地位,這就必須樹立敞開大門對外開放的思想。一個是樹立商品觀念,一個是樹立對外開放觀念,這都是發展戰略問題,關乎黨的總路線總目標問題,不是具體路線問題。
從這兩點出發,就必須提出知識和人才問題。什么人能搞商品經濟,能打出去對外開放,他就是人才,就是能人。不能用一個標準看人才,要敢于起用所謂‘不三不四的人。
而組織這樣的戰略轉變,決不是短期的事,因此,還要樹立長期改革思想。
以上幾條,如何為黨政干部接受,如何組織落實,變成千百萬人的生動活潑的實踐,又如何從實踐中檢驗、豐富、發展這些正確的戰略思想,應當是我們報紙宣傳認真研究和充分反映的重大課題。
有的同志說我們黨報商味不足,這里涉及一個重要問題,我們現階段的黨報,要辦給誰看,專業戶喜不喜歡看,商人看不看,訂不訂,報紙多大程度上可以滿足那些活躍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新事業中的人們的需要。過去報紙充滿火藥味,人家看了都怕,‘階級斗爭為綱的弦拉得很緊。現在是否應當充滿著四化味、商味,即發展商品經濟、新科技、新信息味。
《貴州青年》改名《青年時代》,這改名的本身就是一種氣魄。改名后發行量突增。它的‘紅綠黑白青藍紫文摘名稱就是雜味。青年為什么喜歡《青年時代》,很值研究。
三、利用報紙的優勢,把黨報當作黨委促進經濟發展,促進各方面事業發展的大工具,開展各種事業。
這也是外報提的‘以報為主、多種經營問題。外報提出‘盡快致富,這僅限于報社的富。其實,著眼點還要高些,即這么一張黨報,應當是有很大優勢的,許多部門比不上報社優勢。報社要敢于拿出氣魄,手伸向許多事業領域,利用我們的新聞機關的特點,舉辦許多事業,應當可以舉辦技術交流中心,經濟信息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文化學術交流中心。不要事事跟著有關業務部門轉,報社自己可以打開活動門路。都等業務部門,許多事就干不成。現在業務部門框框很多,如果報社能把這些事業發展起來,就可以突破一些領域和部門的沉悶局面。
這里,有兩點重要指導思想:一是多種經營主要是利用報紙的特點和優勢,與辦好報紙、使報紙更好服務社會、面向社會密切結合,而不是離開這個目的不是把報紙辦垮,而是把報紙辦得更好。二,它是報紙宣傳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辦報與辦有關多種事業是分工不同,可以根據人才多樣性的特點,有的專心辦報,有的可以抽出來辦其它事業,有的可以適當兼搞。因此辦事業與辦報一樣,都是黨的工作任務,獎懲制度應當基本一致,不是停薪留職,不能光讓辦事業的個人富起來,應當不管辦事業、辦報,誰干得好,誰都先富起來;誰干不好,誰就受罰。
四、適應大幅度‘調屁股,在報社人才培養上應當避免同一個標準看人才,要多樣化。
五、報社要多向省委反映內部信息,要了解各部門各級領導的思想情況,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情況。好的方面,存在的問題,都要敢于反映。
上面是朱厚澤談話要點,是我當時追記的,不完全是原話。當時正處在整黨的整改階段。根據耀邦同志視察貴州指示,整黨
要抓住服從服務黨的總路線、總任務,要進一步明確業務思想、業務方針和改革方向。所以,朱厚澤兩次談話后,我曾將上述內容向報社同志傳達,并提出了貫徹上述指示精神的意見(從略)。
在省委工作期間,朱厚澤對報紙工作還時有重要指導性意見。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始終強調新聞工作必須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不可把黨報凌駕于人之上,訓人、壓人、束縛人,甚至蛻變為對人的全面專政。以人為本,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靈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就有馬克思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我們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就應該談馬克思這篇經典文章。記得,他到省委工作之初,正好碰到來勢洶涌的“清除精神污染”,他對這個不是運動的運動,抱著警惕態度,持十分清醒的頭腦。他一方面向報紙打招呼,要冷靜、實事求是進行正確宣傳;另一方面,要求貴陽市委、市公安局及時糾正一些左的苗頭,如有人在貴陽街頭粗暴地剪青年人的“喇叭褲”褲腳等錯誤行為。頭兩天,貴州日報發了一條座談會消息,文中提到有人說:貴州大學一位教授翻譯出版的外國小說《教父》,是一部“打砸搶”的教科書。朱厚澤見到此新聞,立即打電話批評報社。當時我參加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泰國,回來后,見到我時,眼睛瞪著說,報紙有什么權利隨便給中外文藝作品定性?對待思想文化領域的問題,必須允許民主討論,百家爭鳴,誰也沒資格當裁判官!
厚澤十分重視報紙言論和理論宣傳,希望報紙在思想理論方面有所作為。他不贊成地方報紙傳統的單純強調地方特色,言論只講“貴州話”,不講“普通話”,不關心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他更不贊成黨報言論過分業務化,陷于部門業務工作之中。他多次提醒我,報紙總編輯思想要開闊,全國性的、全球性的問題,都應當關心。
不過,朱厚澤上述思想,對我們的言論工作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日后本報言論選題、立論、寫作中,曾有所體現。比如,1985年全國黨代表會議強調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積極維護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言論組同志分析當時情況,撰寫了一篇《權威從何而來》的評論員文章。著重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權威首先來自你講的是真理,更來自黨員、干部的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狀態不理想、權威不夠,原因之一,就是有些領導同志“說一套,干一套,對人一套,對己一套,言行相悖”,“這種搞法,權威從何而來!”文章進而指出,“思想政治工作部門不同于政權機關,解決思想問題不能靠發布政令、采用強制手段。”“如果靠強制、壓服,或是靠欺瞞哄騙,那就不僅是濫用了權威,而且遲早會喪失權威。”這篇言論,實際上是針對某些人以為維護權威,就要回到“左”的時期“突出政治”的老路而發的,涉及的決非地方性的問題。所以,《人民日報》曾全文轉載了。后來,在宣傳十二屆六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決定》時,本報又發了一系列言論,大都有共同針對性,其中《一切積極的思想與精神都應該保護發揚》也為全國性報刊所轉載,并選人《中國新聞年鑒》。報紙抓住重要問題作文章,是從梁啟超《民報》、張季鸞《大公報》、我黨建國前的重慶《新華日報》、延安《解放日報》等報紙言論的優良傳統。言論要大氣,不能小里小氣,陷于業務性或畏畏縮縮。我認為,朱厚澤對報紙言論工作的觀點,是符合現代新聞言論帶規律性方向的。
朱厚澤非常重視報紙的作用,但最不先贊成自己成天在報紙、電視、廣播上“出頭露面”。這一點,與池必卿、胡錦濤的風格相同。回憶起來,池、胡兩位主黔期間,個人活動講話,見諸報端的,幾乎屈指可數,我曾查《貴州日報四十年》大事記,據不完全統計厚澤從擔任省委第二把手到一把手,個人活動見報的不到10次。1984年12月,他在省電視臺35周年紀念會上,傳達了池必卿對新聞工作的指示,見報與廣播時,都弄成了朱厚澤的指示。他當天早晨即以“龍飛鳳舞”似的潦草鉛筆字,寫于一封信給省廣播電視廳廳長楊德政與我,那不留情面而帶諷刺性的文風,也許是一篇報史上的不可多得的佚文。不妨原文抄錄,以饗新聞界朋友:
信封:“急送/楊德政、劉學洙同志親閱/朱厚澤”全文:“德政、學洙同志并兩家編委、黨委:聽了今晨廣播,看了頭版要聞,不能不向你們提出抗議。
我清清楚楚說了,把池必卿同志在報社三十五周年會上提出的三點轉達給廣播電臺的同志,怎么你們變成了朱厚澤對廣播工作提出了三點要求呢?電臺還在今晨播了評論,提倡要堅持新聞的真實性。這種類似‘換頭術的作法,屬一種什么樣的真實性呢?!我對新聞報刊廣播工作不懂,是外行,我想請教一下兩位負責同志和你們的編輯、記者,這種做法,符合廣播、報刊、新聞工作的那條戒律呢?還有沒有別的報道中用了這類手法呢?……如此等等。希望能向廣播、報紙的編輯、記者同志們都說一說這件事,請大家議一下,對不對。然后把結果和今后準備怎么辦通知我一下。
敬禮
厚澤
12.29”
這封隨手寫下的書信,真是太精彩、太傳神了。這完全是朱厚澤的風格。當年黨內上下級關系,似乎還比較寬松,他的這封信,我和楊德政都不覺有什么壓力,他也不再過問。信里所謂“換頭術”,是新聞史上一則丑事,發生在“文革”初期,新華總社發新聞圖片時,把鄧小平的頭像去掉,換上了陶鑄的頭像,時稱“換頭術”。這封信是指把池的指示變成朱的指示。因此才招來朱那封嚴詞問責的信件。這也難怪他,因為他本來就是不喜歡在報上電視屏幕上“亮相”,何況把第一把手的指示,栽到他這個副手的頭上,豈不掠人之美么?
朱厚澤有時看來很嚴厲,批評不留情面。而實際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厭惡那一套官架子,認為是低級趣味。他是高官,更像學者,喜歡務虛,談實際工作,往往從理論高度,給你神聊,好像他總是那么不急不躁。聽完后就知道,他雖似漫談卻很有中心,不僅讓你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有人說,與他談話,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不僅解渴,而且感到很愉悅輕松。有事找他,一個電話就去了,沒有那么多清規戒律,“秘書把關”之類。聽說,1985年他與剛上任的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龍志毅第一次交談工作,竟是到郊外幽靜的森林公園邊散步邊聊天。這真是可人小說的生動素材!(龍志毅暢銷長篇小說《政界》就有這個影子。)這是朱厚澤的一種風格,一種工作方法。
朱厚澤到中宣部工作后,對貴州日報仍很關心。有一回,省委常委、副省長張樹魁從北京開會回來,向我轉告了朱的意見,認為貴州日報太陳舊,翻開版面,往往比發達地區的報紙遲鈍、不新鮮。所以,1986年,我提出派記者常駐北京,搞些獨家新
聞,傳遞些新鮮信息。當時全國新聞界對新聞改革呼聲甚高。1986年9月間,中宣部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省報總編輯會議,會上傳達了朱厚澤部長對新聞改革的三點意見。總的原則是:新聞改革是在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根本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的自我完善,不是根本性改革。同時也主張不要管得太多太死,適當放點權,大原則要管,不能自行其是。管的結果,也不要搞成千篇一律。他講到:“總之,要把報紙、新聞工作搞活,使之富有彈性,不要搞得很死。把各條戰線搞得全面緊張,那不是我們的治國之道。要讓各方面、各階層的人們各得其所,這才能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各省總編從哈爾濱回京后,朱還在中宣部與我們談一次話,中心內容是要求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前后,輿論環境要保持穩定,不要引起激蕩。講了很多好的意見。都是要求維護大局、推進改革的。
(五)
時光過得真快,今年已是朱厚澤走出貴州大山,定居京華的第21年。這二十來年間,中國的變化巨大,人的變化亦大。我們都已垂垂老矣。回憶高中后期,他所在的清華中學與我就讀的中山中學兩個高中畢業班,結成兄弟班,我們常去花溪聯歡聚會。同學少年,書生意氣,評說時事。朱厚澤口才極好,文筆漂亮。他們辦的《狂飚》壁報,內容進步,精彩大氣,張貼在進校門的迎面一堵大墻上。他的時文,常常吸引我們班上同學佇足觀看。他時年十七八歲,剃著光頭,團團的臉,皮膚油黑,臉帶機智微笑,言談幽默而帶機鋒,多才多藝,足球健將,游泳選手,亦有歌喉。當年他真是我們年輕人崇拜的對象。當年清華中學不收女生,演曹禺《雷雨》話劇時,他扮演女主角四鳳,可惜我未獲一睹這位“四鳳”風采。回首當年,宛如昨日,不勝神馳。
1995年,朱厚澤回貴州,沿烏蒙山區走了許多地方。陪同的畢節專員祿智明是威寧人,彝族,自稱“烏蒙漢子”;地委書記劉也強,北方人,也以“烏蒙漢子”為榮。朱厚澤織金人,名符其實是“烏蒙漢子”。一路上,他對家鄉山山水水滿懷深情,和老鄉們一道,互相以“烏蒙漢子”自豪自勵。我與他們同行,置身其間,不禁怦然心動。“烏蒙漢子”是大山之子,應該有山一般的性格。多年前,朱厚澤有一封給上海黔籍著名詩人黎煥頤的信,題為《山之骨》他自稱那是描寫美麗雄奇的喀斯特溶巖自然造化發展史的“科學小品”。依我看,它飽含深深意蘊。不妨抄錄于此,以饗讀者。在這封信紙的頭上,他寫了一個自注:
“接南國友人書云:‘遙望京華,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鈣,而貴州多山,山,鈣之骨也,應為吾輩所珍……固有此復,戲題為《山之骨》。”煥頤兄:
大作及惠書均悉,謝。閃現于字里行間的火熱情懷,讀之怎能不為所動!
鈣,世代所珍。至于其人,乃山村野夫也。出身邊陲,遠離京華。無奈赤誠的良知乘時代之大潮將其卷入風暴旋渦。沉浮之間,身影偶現,時而入人眼目罷了,野氣未消,鈣性難移,但恐所剩無幾矣。
君不見,遮天蔽目的蒙蒙雨霧,吸附著千年郁積的瘴氣與近代生活的污煙,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蝕得滿目瘡痍。山巖挺立的輪廊,在晚霞的余暉中朦朦朧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經難以辨認了。它正消失在黑夜之中
山之骨,它還會從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現它的身影嗎?
是的,當那山之骨從溶蝕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潛流中,從浩瀚的林莽深處、野草叢里,滲過泥沙與巖縫,歷經艱辛和曲折,沉激、蒸騰、散發、揚棄了那污煙和瘴氣之后,它必將會重新凝結出來。
那潔白透明的鐘乳,磷磷閃耀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正是新生的山之骨嗎!那新生的山之骨,它將比它的母親——被溶蝕的樸實無華的野性山巖,千般壯麗,萬般誘人……
這是自然造化之所致,也符合人類歷史之規律。
對這一天,人們滿懷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來,我們難以觸及的未來。它不會出現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何如。
握手!
請代我問陳老夫婦春安。(按:指遵義籍老將軍陳沂將軍夫婦)
朱厚澤
1991年1月24日
在結束此文時,偶見一份手記,是厚澤的老同學寫的,講到:“1987年在成都一個會議上遇見厚澤,那時他已離開中宣部,之后到中央農村研究室工作。會后,厚澤應約赴樂山出席另一會議并邀我同行。我們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師為修建樂山大佛不避艱險,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海通法師是貴州人。厚澤說貴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風骨;山多鈣多,貴州人應該不缺鈣。這是他透露心跡,我們相視而笑?”
讀這傳神的幾筆勾畫,我才知“山之骨”之說,不是始于前信,1987年就有此語。朱厚澤出生于烏蒙山區,是烏蒙大山之子,“山之骨”,其為朱厚澤之自我期許與人生追求乎?!(續完)
2006年4月25日
責任編輯: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