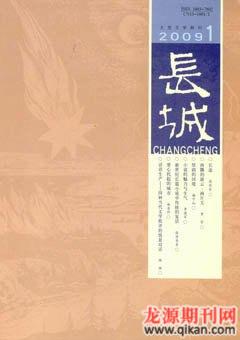和抑郁癥患者在一起
陳集益
我和馬奇坐車來到京郊的土地上。京郊的白楊樹葉子枯萎,飄零下來,寒冷的霧籠罩在大地上,隱約可見一些正在建設的樓房,搭著腳手架的,鉛灰色的,在巨大的十字架下面,從那里傳來一陣吱吱啦啦電鋸切割鋼板的聲音,像是誰的反抗。馬奇說,我們再往前走一段吧,我聽不得噪音。我想他的確需要安靜,于是又回到破爛不堪的公路上,手里拿著鐵鍬,我們用鐵鍬攔下了一輛開往更加郊區的小公共汽車。
小公共汽車是承包給私人營運的。售票的小伙子問我們:“要到宋莊嗎?”
馬奇搖頭:“我們在半路下。”
不知道為什么那人笑了,他說:“你們很像宋莊的藝術家。”
馬奇反問道:“宋莊有想死的藝術家嗎?”
那人再沒有說話。車越開越快了。我們的目光盯在車窗玻璃上,我們在尋找一塊可以將人埋在地下而不會招致異議的地方。這樣的地方,我們在一條河流和一條高速路的交匯處找到了。這是一個被人遺棄了的地方,有足球場那么大,堆積著垃圾、泥土、碎磚和工業廢料。它骯臟,雜亂,坑坑洼洼的坡地上長滿了死亡的野草。我發現,野草當中竟然有盛開的牽牛花,盡管牽牛花的葉子早就掉光了。
這里怎么樣?馬奇說他很喜歡這個地方。他說,把我埋在這一片,絕對沒有人來管。我也是這么想的。這是一個相對安靜的、適合于馬奇沉睡的地方,這里,車流的喧嘩淹沒在水流的喧嘩中,水流的落差是因為不遠處的水閘引起的。這里沒有人來管,不像在城里,也不像在鄉下,只有這里,它屬于馬奇。
馬奇是我朋友永亮的遠親。我朋友永亮性格豪爽,有很好的工作,業余參加公益活動,他助人為樂。現在永亮死了,馬奇卻活著。他把馬奇留給了我。
“你一定要多關心他啊,他患有重度抑郁癥。”那時候,永亮只剩一口氣了,他還想著馬奇如何活下去。我不理解他,沒好氣地說:“你就安心地上路吧,馬奇有我照顧呢!”我的朋友突然把眼睛睜大了,他還想叮囑我什么,但是,他抽搐起來,捏住我的手像一把鉗子一樣攥痛了我,他死了。
你知道嗎?自永亮死后,馬奇就搬到我這里住。我很快就要瘋掉了。他一天24個小時情緒低落,苦惱憂傷。
“今天又有人跳樓了。”
“是嘛?”
“電視里看的,那人還沒有跳,樓下就聚集了上千號人,他們都等著他早一點跳下去……他們竟然起哄……”
“他可以不跳。”
“可他還是跳了。他并不想結束生命的,他只是想終止痛苦。可他還是跳了。”
我沒有話說,我不想跟他談論死亡的話題。但我還是聽見了,“一個人想過一次自殺,就會總是想自殺的……自殺是經過周密準備后的結束。”他反復念叨這樣的話,就像一個死了一半的人。他想死想了好多年了。他有一個筆記本電腦,里面收藏著許多自殺的方法。有一天,他把我拉到電腦前,要我幫他選擇一種自殺的方法,我看到有一個喉結滑動的人,手里抓著一個繩套,他站在一條凳子上,踮著腳尖,他把上吊的動作重復了N遍。
無聊!你太空虛了!
馬奇卻冷笑……
我把播放器關掉了。我無法理解他。他在墻上的掛歷上勾滿了他要離開人世的日期。這些日期的間隔越來越短了。我怎么可能不害怕?我去上班,一整天心神不寧,腦子里想著下班的時候,推開房門看見的是馬奇的死……
想到馬奇的死,想到他死魚一樣的已經發白的眼睛,想到他因死亡而緊縮的僵硬的身體,我多么難過!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哪!可是馬奇一直沒有死,這倒讓我感到意外了。他會選擇何種方式結束自己呢?許多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想。
上吊的優點是操作簡單,前提是繩子不能斷掉。但馬奇很可能選擇割腕自殺,因為這是馬奇向往的“平靜而無痛苦”的死法之一。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如果他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硬要追求一種壯烈的效果,把菜刀擱在仰起的脖子上,情況會極其不妙!試想一下吧,當絕望的馬奇用刀子割開頸動脈的時候,他把喉管也切斷了!鮮血,那是香檳酒一樣噗噗冒的鮮血啊,它隨同呼嚕呼嚕響的氣泡噴射到了天花板上!
我簡直要瘋掉了!……一方面,我擔心馬奇趁我不在死在了房間里,死的無法收拾。另一方面,我又無法接受他在一個又一個周密的死亡計劃之后仍還活著!我鄙視他想死卻沒有決心,像個娘兒們似的!我真想問一問他,你他媽的隔三岔五在掛歷上策劃自殺有意義嗎?你沒有勇氣去死,你就老老實實活著!做給誰看的?但我終于沒有說,因為當我看見他的時候,我再次想到了永亮。是永亮把馬奇留給了我。
可是,我已經無法容忍馬奇在一次次“自殺”之后仍還活著。我是眼睛里揉不下沙子的人。有一次,馬奇突然把掛歷上的所有日子都打上了勾。我看見他把我的掛歷糟蹋成這樣,狠狠地訓斥了他一番,給我擦掉去!每天都是自殺的日子,晦氣!……馬奇低著頭,眼淚飽含在眼眶。第二天,馬奇臉色青白,一早在屋子里走來走去,他的樣子就像過幾分鐘就要被憲兵拉走槍斃的人。我急著去上班,但是,我被他失魂落魄的樣子所吸引。
我對馬奇說:“馬奇,我上班去了,我今天很忙,要到很晚才回家,你在家開心點,昨天我說重了,對不起。”
馬奇的眼睛里射出一束恐懼與哀求交織的光:“陳哥……你留下吧,我要走了……”
他的聲音很輕,我裝作沒有聽到,我下了樓,心里想著他會去跳樓、撞車、投水、自焚、觸電……總之,我因為想到這些,不想去上班了。我走到街對面的一個小商品市場,買了一副十塊錢的望遠鏡。付錢的時候,我真想對長著一小撮胡子的小販說,跟我一起去看自殺吧!但我覺得我不該跟一個陌生人說這樣的話,就默默地來到我住的居民樓對面。透過望遠鏡,我看到我租住的那間小屋窗戶緊閉。這多少讓我感到失望。
我是不是太殘忍了?我這樣想著,手機響了。
“喂!你他媽的到哪兒了?有兩個客戶等著你!”
“快了,快了,路上堵車。”
我不得不去上班,去見老板———那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變態狂———他不睡覺,沒有家庭,滿嘴企業文化。他要求我們穿統一的服裝,理一樣的頭發,見面的時候要像日本人一樣“嗐”“嗐”,上班之前每個人還要對著一臉橫死的肉,拍著胸脯叫喊:“我能行,我能行!耶!”下班的時候,我們還要集中起來學習“把干毛巾再擰出一把水來”的企業精神。
公司是一個禮品公司。上午見了幾個傻頭呆腦的客戶,一看就是來北京送禮走關系的,我向他們推銷“風水大師”。這是一種用劣玉做的擺件,上面刻著陰陽八卦圖,售價38000元。可我知道,其成本不到2000元。他們竟然一口氣買走了20件。中午,我向老板請假,老板問我請假干什么?我謊稱女朋友從家鄉來看我。老板說,你就讓她來公司等你吧!下午還有客戶來。我說,她第一次到北京來,我要去接他。他不同意。
一整個下午,我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以前,我從來沒有這么恐慌過。我突然想阻止馬奇去死!不是出于珍惜生命,而是因為孤獨。而現在,馬奇或許已經死去。我的頭暈暈的,一定是死去的馬奇在我頭頂盤旋。馬奇啊!我沒有等下班前的讀書會開完,就瘋了一般沖下寫字樓。
“快,快,六里橋!”
我打的往回趕,心里七上八下,果真,我還沒到居民小區,就聽見了警車笛鳴……我看見我住的那棟樓被包圍了,警察正在用喇叭疏散樓里的人,現場一片混亂。有幾個老太太從樓道上滾下來,暈過去了。
我的到來,立刻吸引了一個住在對門的中年婦女,她到處亂跑,看見我,如同看見十惡不赦的仇人,她抓住了我:“是他!是他!這些外地人!恐怖分子!要死喝農藥死,為什么要來害我們呀!”
“怎么回事?放開我!”我發火了,直想往樓上沖,但被更多的人圍住了。“找死!你想干什么?!”警察也趕了過來,不分青紅皂白將我摁在地上,直到聽說我是自殺者的同屋,才兇我:“站起來!有鑰匙嗎?掏出來!”
我把鑰匙交給了警察,我拿鑰匙的手顫抖了:“是、是不是死人啦?警察?”警察沒有理我,一個一個往樓上走。這時,回答我的是一個眼袋很大、眼球暴凸的男子,仿佛從天而降,他湊到我耳根說:“要爆炸了!滿屋煤氣!你還不知道嗎?……”
我嚇得差一點癱倒,就像身上的力氣被人抽掉了:“馬奇,馬奇,你可要想開啊!我不想你死!”
原來,馬奇在下午的時候打開了煤氣閥。惡臭的煤氣嗞嗞作響。煤氣從門縫飄到了樓道上,樓上的居民報了警。可是,馬奇終于下定決心離開塵世的一次,偏偏被我的及時趕到解救了。當我在拘留所看見他,他瘦了,兩眼發暗,他先是不理我,然后就哭了。我知道,那是因為羞愧,如果換了我,我也會感到無臉見人的。
我對他說:“馬奇,好好活著。你是永亮的表弟,我是永亮的朋友,我不會丟下你不管的,反正一個人住兩個人住都一樣的房租。有志者事竟成,做個樂觀的人,積極向上的人。你年輕,機會總要比我多得多……”
其實,這樣的話我說過多遍,都快說餿了,馬奇從來沒有反駁過我。可是這一回,馬奇吼起來了:“哼!你別假惺惺的!看我沒有死成你心里很難受吧?告訴你,我知道你討厭我,巴不得我早死,恨不得宰了我!你放心,我不會再拖累你!”他說著說著動了肝氣,喊起來了。
我一個人回了家,氣得胸口疼痛。說到厭惡他,我真是厭惡他。誰有義務撫養他?更何況,他想死的情緒多少影響了我正常的生活。我甚至懷疑他是裝出來的,他一直在用“我要自殺”來獲取他的生存權。然而昨日的事實,顛覆了我的這個想法。
馬奇為什么不想活了?關于這一點,永亮沒有告訴過我。那就讓他去死吧!一個人要想死,連上帝也沒有辦法的。但是,事情沒有這么簡單,兩個星期后,我的朋友瓦片打來了電話,告訴我馬奇三更半夜敲門,要在他那里住,并問我這馬奇平時是不是不愛說話?我說是的,他經常獨自流淚,不言不語。瓦片又問我,那他是不是還喜歡收集一些關于熊呀、刺猬呀、兩棲動物呀之類的科普知識?
我一時愣住了。我沒有記得馬奇有熱愛科普的嗜好。他平時喜歡念叨“一個人想自殺就會總是想自殺的”,除此之外,他還喜歡看一些有關自殺的影像。瓦片聽了不吱聲,我問他在聽嗎?他嘆了一口氣,他說馬奇住到他那里的第一天,就在他的電腦上下載了許多自殺的影像,他現在都不敢打開自己的那臺電腦。我心想,他來找你你就收留他,活該!
后來,瓦片又向我打了許多電話。他說他要崩潰了。他是一個著名電視劇作家麾下的槍手,他每天必須完成一萬字的劇本初稿,他的生活來源就是這些垃圾文字。那個著名電視劇作家把他的初稿交由另外的槍手再加工,直到有一天,瓦片會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東拼西湊的故事,里面偶爾會冒出一個由他設計的情節……瓦片說,那個電視劇作家批評他不該在新的劇本里插進莫名其妙的自殺……
瓦片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就是希望我把馬奇接回去,不要影響他的創作。我就是不松口。瓦片只好繼續向我訴苦,然后,他突然說:“你不接走他,我只好把他轉讓了!”
我吃了一驚:“轉讓?”
瓦片反問我:“你不就是把他從永亮那里轉給我的嗎?”
我張著嘴,不知道說什么好,我說:“我不忍心把他趕到大街上。”
瓦片說:“我想把他轉讓給胡熊!”
我的腦子終于拐過了彎。
當年,我、永亮、瓦片,還有胡熊,在網絡上相識,在聊天室里暢談人生,都覺得不能在小城市繼續呆下去,于是相約來到了北京。我們住地下室,啃饅頭,吃方便面,一個個夢想大干一場。若干年以后,只有永亮混進了報社,胡熊開了文化公司。現在,永亮過勞死了,馬奇成了累贅。我倒真希望馬奇在胡熊那里能找到一點事干。
遺憾的是,僅僅三天時間,馬奇的造訪就讓胡熊忍無可忍了。他在電話里這樣問我:“這個馬奇怎么回事,整天魂不守舍?我想安排他做點事,發現他工作效率極低,記不住事。連走路都緩慢,要死的樣子。我問他沒有睡醒嗎?他說他失眠,哪怕睡得再晚,每天凌晨四點總會醒來。我說呆會你補個午覺。他竟然說他好想睡過去,從此不再醒來。”
我只好向胡熊解釋:馬奇患有抑郁癥。沒想到胡熊大吼一聲:“什么抑郁不抑郁的!我看他是渾身發懶!天又沒有塌下來,他竟然把自己關在屋子里,還想讓我給他準備五十斤肥肉,三十斤甜食,二十斤巧克力。我問他這是干什么?他說,冬天要到了,他要儲存熱量。他媽的!儲存那么多熱量干什么?”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馬奇自殺不成精神分裂了嗎?只好叫胡熊把剛才的話重復一遍。我對他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在我們幾個人中,現在只有你混得好,你就多擔待一點吧!”
我沒有去接馬奇,接他個屁!然而可氣的是,胡熊把馬奇送回來了。胡熊給了我兩千塊錢,還提了一塑料袋肥肉、一塑料袋巧克力,捶著我的胸脯說:“陳超,馬奇就交給你了。我看他精神恍惚,不是很正常,你要多觀察,假如需要治療,錢只管到我這里拿!”
我心想:“你就拉倒吧!說得比唱得還好聽!你有錢你不會請個保姆照顧他呀!”
從那以后,馬奇又在我的生活中出現了。我僅僅得了七天清閑!我什么辦法?誰叫永亮臨死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場!答應死人的話是不能更改的。
我算是受夠了:馬奇年紀輕輕,愁眉苦臉,仍然不出去找工作,不參加社交活動,話說得比以前更少,飯倒是吃得比以前更多了……總之,他從那時起變得神秘,遲緩,像個瘟神似的終日窩在電腦前搗鼓瓦片跟我提到過的那些科普知識。這些知識都跟動物過冬有關……
面對這樣一個人,我感覺我也要犯病了:“你他媽的,一天24小時搜集這些破玩意除了讓你特別能吃,還有別的用處嗎?我早就跟你說過,你想死你就去死!”
不可否認,馬奇臉紅了。這說明他還保持著一顆羞恥心。他這樣說:“我在拘留所收獲很大,我想通了很多事情。無論我能否做到,陳哥,我都覺得……這是一次反思,對回歸正確的道路的反思。”
“反思你個鳥!”我真想罵他,但我忍了。
他還在說:“我要給自己一種心理暗示,好的心理暗示,我想活著,我們都不該死……”
“那你就不要死!”
“但我畢竟是往正確的道路前行了。以前,我也有過奮斗,我厭倦了,對生活失去了樂趣,人,有時候只想停下來喘一口氣!……陳哥,你難道就沒有這樣的時候嗎?哪怕做片刻的逃避?!”
我不喜歡一個人瞪著兩只眼睛逼問我的內心。他還想說什么,我一巴掌打了過去:“住嘴!別跟我講這些大道理!神經病!”
他站著,委屈,激動,但是沒有還手。他從那天起,再沒有和我說話,他也不吃飯了,蜷縮在破爛的沙發上,閉著眼睛。我心想,算你有種,我看你能餓上幾天?你還想用絕食來跟我對抗嗎?我不吃你這一套!
一連三天,他好像都沒有從沙發上下來。剛開始我懷疑他趁我上班,一定會起來吃東西,活動,但是我仔細觀察他躺著的樣子,碗筷的擺放,還有馬桶上的污漬,判斷出他始終保持了一個姿勢,如同一具僵尸。我害怕了。我用手指在他的嘴巴上方探了一探,幸好,還有呼吸。
“你還沒有死成嗎?”
“哦,哦。”
“那你就接著裝死!”
“我一直憋著……陳哥,我餓壞了,現在還不到時候。”
“什么意思?”
“冬眠。”
“冬眠?!”
“是的,我想冬眠。”
“我聞所未聞!”
“陳哥,在拘留所,是這樣的:我忘了說……我撿到一張報紙,大概是民警隨手扔在地上的,我還保留著。我每天看。”說著,馬奇站了起來,由于長時間蜷縮不動,他的膝蓋有點哆嗦,“你看,就是這一段文字。”
我看到一張遭到油污的報紙上,印著這樣一條簡訊:
本報訊 英國當地時間8月4日消息,據近期出版的科學雜志《地理》報道,澳大利亞史前考古學家發現了遠古時代原始人冬眠的洞穴。在洞穴中找到了一些原始人冬眠的遺跡,展示了一百多萬年以前人類冬眠的實物證據,在學術上很有價值。
一直以來,原始人沒有衣服怎么過冬的問題困擾著科學家。曾有人斷言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的重大分界線,是原始人意識到火可以取暖。當冬天來臨時,原始人就靠近火堆,對火的利用是他們御寒的手段之一。然而,科學家對人類用火之前的過冬方式始終不能作出解釋。人類冬眠洞穴的發現,反映了人類始祖具有冬眠的習性,他們以此熬過漫長而寒冷的季節。
據報道,該冬眠遺址位于阿波菲斯山西南12千米處的山腰,距地面252米,洞口朝正南,高約0.6米,寬18米左右,洞分外廳與其后的長穴道兩部分。該洞穴與原始人居住的巖洞最大的不同是該洞非天然形成,是原始人用石器挖鑿而成的,洞內干燥不通風,人只能爬著進去。據估計,該洞穴可同時容納2000人抱成一團進入不吃不喝的冬眠期。
我將信將疑,我想報紙上的東西總是可靠的。可是,這么重大的科學發現為什么媒體沒有進行熱炒呢?我問馬奇,馬奇說:“這方面的報道還是很多的,我查了一些英文網站,都有。你知道為什么這條新聞很快就銷聲匿跡了嗎?”我說我不知道。馬奇說,那是因為怕亂了。
說實話,我一點也沒有聽明白這是什么邏輯。馬奇向我解釋:“你就沒有想到現代人一旦恢復了原始人的冬眠習性(宣傳多了,自然會有人去嘗試的),是件很麻煩的事嗎?第一,生產力將受到影響;第二,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第三,軍隊戰斗力渙散;第四,罪犯將逃往寒冷地區躲進地洞通過冬眠躲避追捕……”
我想想也是,如果人類一到冬天都躲到地底下去冬眠,社會還怎么發展?不過,將人和冬眠扯到一塊去,是不是太離譜了?冬眠是某些動物的本領。馬奇說:“你就沒有聽說過東北人‘貓冬嗎?在俄羅斯,在西伯利亞,那里的居民更是一到冬天就足不出戶,長達半年,他們的過冬方式跟冬眠非常接近了。”
“可‘貓冬畢竟不是冬眠。”
“那你就沒有想到‘貓冬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那是,那是。”
那一天,我跟馬奇探討冬眠的問題。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馬奇談論起冬眠來,兩眼放光,情緒激昂,好像從來沒有這么健康過。馬奇補充說:“其實冬眠沒有什么壞處,壞處都是當官人說的。依我看,冬眠可以減輕地球的壓力,還可以讓一個人得到長足的休息;最最重要的,冬眠能夠讓窮苦人挨過一個缺衣少食的季節!”
我突然發現,我和馬奇的共同語言突然多起來了!
接下來,是一段特別繁忙的日子。變態老板照搬日本式的管理,目的就是要把我和我的同事榨干。我們剛剛賣完“風水大師”又奉命制作一種叫做“金書”的高檔禮品(“金書”有一陣子特別流行)。如果印制孫子兵法的“金書”制作成功,老板將獲利千萬。而我們,為了拿到每個月三千塊錢的酬金,晚上也要住在公司里。
我們一天18小時都在工作。在這樣的壓強下,人幾乎與外界失去了聯系。有一天,馬奇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從網上搜到了一則有關冬眠的消息,叫我一定要看一看。我按他提供的網址,輸入、打開后,讀到的是這樣一篇報道:
瑞士男子“冬眠”存活24天
一名男子在瑞士中南部登山時失蹤,在沒有進食和飲水的情況下存活24天,被醫生稱作進入“冬眠”狀態。此人痊愈后已于11月20日重返工作崗位。
這名男子名叫約翰,現年35歲,今年10月3日,他和朋友前往阿爾卑斯山脈爬山,后來他獨自下山,結果從懸崖跌落,后背受傷,只能躺在原地。當時,他身上惟一的食物就是一瓶韓國燒烤醬汁。
“我躺在草地上,在陽光下感覺不錯,最后睡著了。”約翰說,“這是我最后記得的事情。”
直至遇險24天后,救援人員才找到約翰。醫生說,他當時的體溫只有22攝氏度,“進入類似冬眠的低體溫狀態”,大大減緩了他的新陳代謝,很多器官運轉減慢,但他的大腦功能受到保護,如今已恢復正常。
然而,醫學界依然無法確定,約翰如何在身體新陳代謝幾乎停滯的情況下存活幾星期。“如果病人確實在如此低體溫下存活如此長時間,這種案例具有革命性。”劍橋大學研究冬眠的拉丁博士說。
科學家認為,人類冬眠在理論上存在可能性,如果能夠成為現實,可在治療腦出血和其他致命情況時加以運用,以減慢細胞死亡速度。
看了這則新聞,我怎么可能不興奮?瑞士男子的案例,讓我看到了現代人同樣可以冬眠的希望。有了這種希望,真他娘的睡上10年、20年才好!我立刻往家里打電話:“馬奇,你讀到新聞最后一段話了嗎?人類冬眠在理論上存在可能性!”
“何止是理論上,明明就是事實!”
“馬奇,我支持你!如果你成功了,明年我們一起冬眠!”
馬奇說:“我就等著你這句話。我這兩天做夢都夢到自己在冬眠。只可惜小區供應暖氣了,屋里溫度太高,我想到外面去冬眠。我想在樓下的草坪底下冬眠,我都看過了,又干燥又好挖,躺在下面不冷也不熱,正好!”
我倒沒想到這一點,我說:“到外面冬眠還是要慎重,你躺在地下會不會凍成冰?被狗刨出來吃掉怎么辦?”
馬奇說:“是冬眠就得挖個洞穴鉆進去,洞穴是恒溫的,就像4℃的井水。陳哥,明天你回來吧,把我埋到下面去吧!等到明年天熱了你再把我挖出來!”
我想想有點害怕:“這個……會出人命吧,小區的老太太會同意我們在草坪上挖個洞嗎?”
馬奇說:“那我們就坐車到郊外去,在玉米地上挖。躺在郊外的玉米地里,也算是回歸大自然了!”
可我還是無法接受把一個人活埋到地底下去的做法。因為在我的意識里,只有死人才配擁有一塊讓他安息的土地。我沒好氣地回答他:“你以為玉米地就沒有人管嗎?現在就連一口糞池都有人管。告訴你,你在北京只配呼吸幾口臭烘烘的空氣!你就在陽臺上冬眠吧!把陽臺上的玻璃窗打開!然后,鋪上一層細沙……你躺在陽臺上冬眠不行嗎?”
馬奇那邊沉默了。
這時,我剛要說什么,老板走了進來,我趕忙放下了電話。老板對我說:“陳超,你近段時間工作心不在焉,怎么回事?”
我低下頭,什么也沒有說。老板兇道:“你給我在三天之內拿出《孫子兵法》的銷售計劃!到現在你還沒有訂出去一本,你去看看別人,都在給客戶打電話!”
我又忙了半個月。這半個月我的價值就是賣出去78套《孫子兵法》,我幫老板賺了幾十萬。可是,有一天早上,老板親自為我們制定的銷售任務還是下來了。這是他伸伸胳膊,用一只圓珠筆在一個表格上寫下的一長串阿拉伯數字,這些數字很娟秀,像羞澀的情書。而我看了之后眼前一黑,我們的末日來臨了。
盡管老板又一次向我們承諾,誰的銷售業績最先超過制定的計劃,誰將晉升為銷售總監的候選人。但是沒有人再為一個縹緲的承諾熱血沸騰。我在此后的一個星期里廢寢忘食,連尿都要憋疼了膀胱才奔著去尿,可結果只賣出去20套。并且,市場上關于金書的負面輿論漸多,金書好像要被限制發行了。這時候,我們的老板就像一條瘋狗一樣咬著我們,想趕在禁令下達之前將金書售罄。我簡直要崩潰了!
我與老板的對抗,終于發生在一個必須喊口號的早會上。由于沒有售出的金書還很多,老板要求我們每個人想一句振奮人心的口號。在那天的早會上,口號從二十個人口中喊出:
“誓死賣完金書,與禁止金書的法令頑抗到底!同志們,讓我們以優異的銷售業績沖進2008!”“誰禁止金書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團結就是勝利,我們要挖出2007最后一桶金!迎接最后的考驗,耶!”“不要再浪費一分鐘!不要再惦記回家的路!讓我們攜起手,打倒一切阻止金書銷售的絆腳石!不做妨礙公司發展的懦夫!……”
我被震天響的口號嚇呆了,我想憋一句口號,但什么也想不起來。耳鳴像一架嗡嗡作響的直升機。漸漸地,我什么口號也聽不到了,那些跺著腳怒吼的同事如同發瘋的野獸在曠野上嚎叫……這時候,站在我旁邊的財務主管老張突然兩腿發軟,身子打晃,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老張年紀大了,瘦弱不堪,為了給獨生子買房,退休了還到外面打工……老張依靠著墻,一邊擦額頭上的汗,一邊歉意道:“對不起,打攪了早會。”他又情不自禁道:“媽呀,我好像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代。”說到這里,老張意識到他的話出格了,趕忙垂下了頭。
我忍不住說:“老張,你去休息一下吧!”
“不用,我堅持得住。沒事,沒事。”
老張話音剛落,老板帶頭鼓掌:“好,堅持就是勝利!現在,陳超,輪到你的口號了!”
“我、我,對不起,不知道喊什么……”
老板神情威嚴:“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認為公司前途不妙?”
“沒、沒有,我覺得反正賣不掉了……”
“你這是逃避!你這是帶頭當逃兵!我很失望,你為什么就不能關心企業的生死存亡?我辛辛苦苦養活你,你就不覺得羞愧嗎?……”老板的聲音很大,連落地窗都顫抖起來。我緊緊咬住嘴唇。老板罵夠了,又說:“好了,就原諒你這次。剛才聽了你們的口號,我認為都很有氣勢,我希望你們能在最后一個月創造奇跡,來吧!大家一起喊!”
不知道老板哪根筋出了問題,一再讓大家重復喊口號。我只能跟著喊,感覺特別惡心。突然,老板大呵一聲:“陳超出列,你只張嘴不發聲,是不是?你走到中間來,喊幾遍。”
我沒有喊,因為覺得太荒唐。頓時,老板暴跳如雷,大聲斥責:“我讓你喊口號,你聽到了沒有?!”
“我不想喊,今天我心情不好。”
“哼!反了你了!你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是從這里滾出去,二是給我大聲喊口號。”老板氣得臉都紫了。
早會結束后,大約過了二個小時,辦公室主任和財務主管進來了。兩人手里拿著一疊紙。老張不好意思地說:“小陳,對不起,這個月你還剩1600元……”
“為什么?!”
“你的工作結束了。”辦公室主任幫老張回答我。
我無話可說。我將1600元收下了。然后,我走進老板辦公室,一個健步沖上去,抬手就揍他。我真他媽的想殺他,把狗日的宰了!剁成塊,我扛著這狗日的碎塊爬上樓頂,一塊一塊扔下去,甩得老遠……可是,我心軟,我聽不得軟話:“陳、陳哥,饒了我、我吧!你要什么你說,我都給你!在北京,我有三套房子,兩輛跑車,還有這個讓我不得安睡的公司!如果我死了,倒是一了百了……”
我抓起老板的頭發,他的頭發有點短,我就揪住了他的耳朵,我又在他歪扭的臉上揍了幾下子,此刻,我在北京多年的奮斗只剩下了兩只拳頭!我對他說:“狗娘養的,記住,別活得像個病人!人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別把人逼到絕路上!”
老板一邊用袖子擦血,一邊哀求我,他要收回他辭退我的話。但是我早已走了出去。風,是嗚嗚作響的風,削刀一般。摻著沙子。我的腦海一片空白,雙腿如灌鉛一般沉重。我迎風行走,淚眼模糊。但我沒有后悔。三環路上依如昨日車來車往,銹色的樹在風中搖晃,顫抖,我第一次體驗到刺骨的寒冷。北京,早已被嚴寒占領。
我突然想到馬奇,想到了冬眠。
靠在公交車站的站牌上,靠了一會兒,這時,開往六里橋的公共汽車來了。是人,像倉皇的耗子出現了,每個人抱住自己的肩膀,奔跑。我也跟著往前跑。我擠在一群面色茫然、像企鵝一樣相互呆望的人群中間,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一股并不好聞的牛黃解毒片一樣的怪味。這股怪味暖烘烘的,讓人昏昏欲睡。一車人,只有司機和售票員活著,我們緊緊依靠又不說話,仿佛一群冬眠洞穴里的原始人,抱成一團,堆成一堆。想到這兒,我幾乎要喊叫起來,我也多么想冬眠!……
下車后,我迫不及待地往住處走去。
我想,馬奇此刻一定在陽臺上像原始人一樣進入深層的麻痹狀態:他蜷著身子,不食不動,幾乎不怎么呼吸,心跳也慢得出奇,每分鐘只跳10~20次。曾有人用蜜蜂進行試驗,當氣溫在7~9℃時,蜜蜂翅和足就停止了活動,但輕輕觸動它時,它的翅和足還能微微抖動;當氣溫下降到4~6℃時,再觸動它卻沒有絲毫反應;假如,氣溫下降到0.5℃呢?蜜蜂則會進入物我兩忘的睡眠狀態,舒舒服服睡上一冬。馬奇會不會真的進入物我兩忘的冬眠狀態?
我的手在空中停住了。我不想驚擾馬奇。我輕輕地開門進去,屋內黑暗,窗戶敞開,顯然,馬奇沒有像往常那樣坐在電腦前發呆。在那一剎那,我不知道心里是驚慌還是高興,我想他一定在陽臺上躺著了,頭朝里,腳朝外,身上覆蓋著厚厚的泥沙。你叫他他不應,你打他他不理,他做著自己的美夢,不被任何事物打擾!可是當我躡手躡腳走到陽臺一看,卻沒有馬奇。他沒有冬眠嗎?該死的東西!我又在屋里找,屋子也就30多平米。我找遍了廚房、臥室、衛生間,還有衣櫥和床底,都不見馬奇。馬奇消失了。
他出去買東西了嗎?或許,他找到了工作。他一個人跑到外面去冬眠了。如果是那樣,我等他也沒用,他把我拋棄了。我這么想著,就翻起了馬奇留在桌上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他的大學畢業證、身份證、簡歷、欠條,還有他抄在紙上的有關自殺與冬眠的資料。我看到他大學畢業已經三年了,干過以下職業:家教,保險推銷員,安利直銷員,實習文秘,二手房中介公司員工,醫療器械解說,超市收銀員,兼職英語翻譯,市場調查等等。他的欠條好像也不少。我沒有統計,反正有一摞,其中大部分是他為讀大學借貸的。
我翻著翻著,在一張欠款單的后面寫著這樣一句話:
我無力承當這些貸款,我找不到工作。我留不下來,我回不去,我不想死,也不想活。
我又翻了翻他的其他東西,許多上面寫著潦草的字體:
//我的心情又沉下去了,我又在找自己的借口!!!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么要來,事業、未來、人際、夢想、愛情統統不屬于我,我也不配擁有這些。我已經喪失勞動力了。混吃等死的感覺居然讓我痛快淋漓。我徹底解脫了!!!
//我一定要死,但不是現在,我還要計劃。靜悄悄地死。也許我內心中的一點理智告訴我必須將所有求助都試過才能義無反顧地離開這個世界。
//“一個人連死都不怕還會怕活著?”“你是不是覺得前途一片黑暗?”“你是不是自我評價降低?”如果你患了抑郁癥,就告訴自己,我的情緒感冒了,我的情緒正在發燒,現在很痛苦,但只要吃點藥就會好的。
//我同意醫生開藥,“博樂欣”和“阿莫挫倫”,三百多元,服用一個月,我買不起。
//……
翻著,翻著,時間很快到了晚上十一點,我給瓦片、胡熊打電話,他們都說馬奇沒有去過。并且說:馬奇遲早要出問題,叫我不要同情他。我想,馬奇要么不回來了,要么找到新的住處或者真的冬眠了。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同情他。我在關心他,那是因為永亮。慢慢地,我就睡下了。
睡下以后,不由得又想起馬奇,我也不知道這個晚上為什么這么想跟馬奇談心。我仿佛又聽到了馬奇叫我陪他去郊外挖洞冬眠之類的話。比起瓦片和胡熊來,馬奇似乎更值得我珍惜。我躺在床上,漸漸困了,這時,腦子里卻驀然出現本文開頭的那個情景(多么逼真的幻影):那時,秋天剛剛來臨,我和馬奇坐車來到京郊的土地上……我們拿著鐵鍬,揮汗如雨。洞,很快就挖好了,馬奇跳了進去,馬奇說:
“陳哥,我躺下了,開始埋吧。”
“讓我再挖深一點吧!馬奇!”
“不用了,這么深足夠了。”
“馬奇,要是你真死了怎么辦?”
“沒有關系的,反正我也不想活。”
不知道為什么,馬奇的話讓我想起了許多,我一摸眼睛,眼睛濕了。馬奇又在催我:
“陳哥,快點吧,我準備好了。”
在某個瞬間,我感到胸口一陣窒息。我說:“那……好吧!”
我說著,就舉起了鏟子,我幾乎是嚎叫著把馬奇埋掉了,埋在了像夢一樣沉重的地下!當陽春三月,鶯飛草長,他將醒來,充滿活力!
……馬奇。
責任編輯 李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