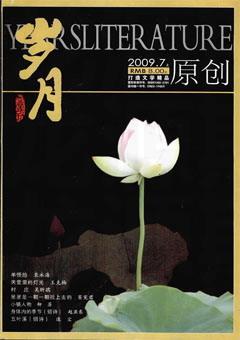紙上的故鄉
李家淳
此身為客
客家人總愛尋根,尤其是家族淵源,一代代難以丟棄。不論到哪里,都得帶上祖宗牌位,待安頓妥當之際,頭件事就是在正廳墻上,放置好先人的牌子,每日祭拜是免不了的。他們相信,逝去的人尚在冥冥中遙望著塵世。那些故人,肉體早已羽化登仙,但靈魂不會消散。冥冥中的“遙望”,即使是一個個虛擬的靈魂,卻真實到隨處可見,觸手可摸。
歷盡多年遷徙,贛南山地已今非昔比。中原先民早已遁跡,留在此地的蕓蕓眾生,拋棄了許多祖先的陳規陋習,唯有姓氏印記依然獨在。如果你有幸進入這片地域,有兩個地方值得你關注,一是方言,二是廳堂。濃郁的唐音,讓人懷疑大唐復活。而祠堂里琳瑯滿目的祖宗牌子,譬如“隴西堂上一脈宗親”,“高陽堂上一脈宗親”……地名的標志是那么明顯。無論歲月怎樣變遷,這聲音,這代表來處的神位,都在告訴你一個歷史:此地永遠是客地,此地的人——客地的人,永遠被當作客人-一客家人。
閩贛交界處,重重山地上,是客家人的搖籃。
我在這個搖籃里生活了許多年,直到我再次出發,往更遠處遷移,仍然改變不了客家人的身份。多年前,我越過那道有名的屏障——九連山脈,往更南處漂泊。北面的朔風即使可以越過大庾嶺的豁口,吹到身上已經溫和了許多。這令我身居客地之南時,夢依舊溫暖。在夢里,那片山地,那些親人,恍隱而清晰。父親說過:不管長大后去向哪里,都要記得回來看看,這里是根。一個人要是不認祖地,就像樹葉疏離了根,這個人就缺靈魂。
父親,他已經躺在群山之上、紅土地里,肉體成了一縷煙霞,留給我的,只有一份叮嚀和一種音容。我沉湎在夢里時,就是沉湎在父親的靈魂里。靈魂虛幻,進入我的世界時卻又如此真實,這種感覺逼迫著我常常透不過氣來,讓我無法釋懷,難以放下。我常常生活在現實與夢境之中。南嶺之南是我的現實,而南嶺之北成為靈魂故地。
很多走出的同鄉,都有我這種靈與肉的依附。這不奇怪,因為每一個客家人心里,總時時回蕩起父親的叮嚀,以及那些遠去的客家靈魂在影影綽綽地閃現。
是的,父親的聲音越過尋常日子,越過時空,飄忽在長天曠野。我懷疑,那就是一種祖先的呼喚,一種紅土地傳出的消息。
故地葬禮
父親、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時,似乎就在昨天。轉眼間,父親老了,山地仿佛并沒多少改變;而父親的去世,只是剎那間的變故。就像祖先們遠逝,僅僅遺留了一本發黃的家譜,不論過程多么漫長,到達我們眼前時,也只是“剎那間”的事。
送走他們的,是一個又一個葬禮。
夜色濃重,親人在夜幕俘獲下走進永恒。當第一聲哭泣撕破暗夜,山地隨之顫栗了幾下,流星很快劃過天際。一個生命,在黑夜里悄悄地走了,那撕心裂肺的哭聲,是另一些生命的悲痛挽留。淚雨滂沱之間,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明白,離世的,只是一副朝夕相伴的肉體,從此刻起,這具熟悉的肉體,很快將化作泥土,遁入無形。
哭聲里天明了。哀傷的人走出屋子,仰首長天,天空依舊碧藍如洗,不染纖塵。昨夜的哭聲驚動了鄉鄰老少,當長者們趕赴而來,古老的葬禮便拉開了序曲。
人生于土,必歸于土。“土葬”是客家人沿用千古的儀規,哪怕肉體燒成了灰,骨灰也用壇子鄭重地裝好,放入泥土。如果說死亡是瞬間,客家葬禮卻表現得隆重而繁縟。當死者咽下最后一口氣,也即客家人俗稱的“過身”,遺屬立即下跪痛哭并從河里提回清水,為死去的親人洗臉、擦身、穿上壽衣。在族人的幫助下,死者被抬至廳堂里,靈堂已經布置妥當,一盞長明燈飄動幽思。孝子賢孫們長夜守靈,焚燒紙錢。待報喪人前腳回來,遠近親友也聞訊趕來吊唁。尤其是個別至親摯交,往往撫靈哀哭,涕淚橫流,引得眾人猶增悲痛。廳堂門口,鄉村學究擬寫出幾副對聯,聯日“悲音難挽流云住,哭聲相隨野鶴飛”,或“倚門人去三更月,泣杖兒悲五更寒”,或“垅上猶見芳跡,堂前共仰遺容”等等,不一而足。紙錢在瓦盆里隨著火焰飄飛,身著玄色道袍的道士,開始了平靜而莊嚴的祭奠。哀樂聲聲,香煙繚繞,另一側,和尚們披了袈裟,手捻佛珠,閉目呢喃,口吐佛號。佛道兩家此時此際,和諧而統一地相處一室,做的都是“超度”的功課。地坪里,風水先生正在碑石上刻寫墓志銘,“入殮”(死者搬入棺內),“出殯”的黃道吉日也由風水先生擇好了,只待日子一到,祭奠完畢,遺屬們就將雇請專事抬棺營生的壯漢,此地稱“將軍”的,把死者抬到早已由風水先生勘察好的山上墓穴,讓“走了”的人入土為安。出殯時,三聲鐵銃的巨響劃破空氣,鞭炮聲噼噼啪啪燃放,只聽一聲喊,八名“將軍”把沉重的棺木抬出了廳堂,孝子孝孫們披麻戴孝,手執靈牌,躬身跟在棺木后面,哭著朝那片蒼莽的山地緩緩而行。山路間,白色孝服格外搶眼,紙錢在空中飄灑,嗩吶幽咽,悲聲穿透時空,敲擊內心,令人為之顫栗,為之動容。
事實上,斯人遠去,僅是肉體的消亡。葬禮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家中追念依舊在默默地進行著,客家人謂之“做七”。除了一日三餐必須在亡故人生前坐過的吃飯處盛一碗米飯外,廳堂神位上照例要點香。等到第四十九天,家人必準備了三牲祭品,去到墳前,燒香祭奠一番。真是“人死靈魂在,事死如事生”。肉體長眠地下,靈魂卻飄散在天空。所以,你只要看看客家葬禮的繁文縟節,儀規種種,再走進他們放滿了祖先神位的廳堂,你就會感嘆,客家這個一直漂流著的民系,對于生命的敬畏,對于根系的維護,對于靈魂的歸依,是何等的執著,執著到了形而上的境界。
紅土爍爍,墳塋累累。客地青山綠水間,靈魂飄蕩了何止千年。
清明煙云
三月小雨打濕了世界,泥土溫暖,草木新嫩,一夜間,圍屋和土樓,映襯在青黛色的畫面中。煙云之外,清明的思緒如草木瘋長。
自從祖宗離別中原古老大地,來到這大山里開疆辟土,結廬而居,歷代先民胼手胝足,把豐盈與安定留在這片山林間。那些逝去的身影,流散在山山嶺嶺、溝溝畔畔間。每到清明,摩挲著發黃的家譜,總要懷念故鄉的親人。
“風光煙火清明日,歌哭悲歡城市間”。父親,斜斜的雨絲里,我來到你的墳前。一年中,我只能來看你一次。多少年前,你固守著老屋,我遠在他處,我們之間的距離還解釋得清,可現在,我究竟與你隔開了多遠,沒有答案。如果這座墳塋是你永恒的家,此刻我佇立在你的家門外,聽風聲呼呼地穿過耳膜,感受雨水嘩嘩地瀉落下來,淋漓了這杯泥土,也打濕了我柔軟的內心。右邊的嶺上,有二姐與你相伴;翻過這座山頭,有叔叔與你相對而臥;再翻越幾條溝梁,沿著窄小的山路,通往爺爺奶奶的墓地。我想,你并不會太過寂寞,也不會太過孤獨。我記得,那年我匆匆從外地趕回,急急地奔赴你的喪禮,我們兄弟用了客家最厚重的儀式,把你送到了這里。青石案上,我題寫的“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八個大字依舊如新,只是草木已經漫過墳頭,芳草連天,我們相對無語。
在我們年少時,應是你領著我們兄弟,一處處去祭拜祖先——在清明,細雨里翻山越嶺之后,你汗涔涔地指認著手中的家譜,要我們銘記那一個個先人名字。除了姓氏,那些名字聽起來其實很陌生,很遙遠,讓我們猝不及防,也讓我們對生死漠不經心。可你執拗得從來不去廄忌我們的感受,硬是讓那些遠去的靈魂活了過來——活在我們的眼前和心里。你可能不知道史上的春秋,更不了解有介子推和晉文公,或者你壓根就不了解寒食節的緣由。你只知道,每逢清明,就該翻出家譜,去山嶺間“掛青”。在一塊又一塊墓碑間尋覓印證,印證你對祖先的敬奉與遵從。現在,輪到你成了祖先中的一員,你與他們擠靠在一起,我和你隔著生死之門——生的喧鬧與死的寂靜對視,肉體與靈魂對話,就像你時時進入夢境,溫暖得讓我這個遠在天涯的客家游子,有足夠的勇氣面對現實的冷漠、孤寂。
父親,風在樹木上翻滾回旋,雨水不停地潑灑著。山徑上,陸續有^、走來,走過他們需要面對的墳。而我站立你面前,聽風聽雨,這是我個人的清明。你可看見我手里折下的松枝?松枝在我的手上,發出窸窸窣窣輕微聲響,那是我內心的一種情緒。每年,我只能來看你一次,帶著清明追思,在山野煙云中和你對話。
風里消息
我站在小鎮外的野地上,微風像蛇信子一般舔著我的臉頰,麻酥酥地略帶涼意。大地披上春色,山野顯然失卻了那份疏朗、清澈,林梢罩上了幾許青霧,色相曖昧。春天以若即若離的畫意,獨自遺落在世外。小時作文,喜歡用“清新”、“碧綠”描述春天,多年后,小鎮變得曖昧、駁雜,相比之下,野地猶現虛靜、空茫。
鎮與野,一線之間,像隔開一道墻。世界在水泥的澆注下,眺望的視線日漸萎縮,自然的柔美越發迢遙。
這個千年古鎮,西邊是老街(有青石板的巷子),東邊是新街(二十年前是成片的水稻田),南面是河(河面有兩座石拱橋),北面是后山。水泥路從新街穿過,繞后山北行。鎮街日漸脹大,河水早已斷流,沿岸是擁塞的樓群。河道里長滿青苔、狗尾巴草。幾個大水坑里,汩汩冒出鐵銹色水泡。坑邊有動物尸體(一條發黑的死狗)、印滿字母的變形鐵盒、臟舊衣物、玻璃瓶、破車胎、生銹的鋼筋條、彎曲的鐵釘、爛木頭、豬骨頭、爛蘋果等等。樓房清一色樣子,三層,頂多四層,貼著花花綠綠的瓷磚。鋁合金窗,鑲嵌著深色玻璃,窗內永遠是隱匿起來的生活。
后山,香樟樹青綠的色相和馥郁的香味,如母親的胸脯,柔軟、溫暖。人們為了建新街,從后山取土、取石頭,眼下的后山,礫石累累,泥土裸露,粉塵飄浮。采石場掘進的深度,掏盡了后山的五臟六腑,掀開的表皮像癩痢頭上的隱憂。失血的后山,袒露出堅硬的骨頭。碩大的巖石堆在山腳,像后山被掏出的心臟,閃耀著冰冷的光芒。通往菜地,有一條小路,長滿野菊花、蒲公英、車前草,螢火蟲的微光,曾經映照出多年前的夏天。當我抵近,滿目芬芳被磚頭和鋼筋覆蓋,我無法沿著歲月的小路,回歸青草和昆蟲的世界。
青壯少年都不見。幾個老人,慵懶地圍在門口打麻將,偶爾有農用車駛過街道,發出“嘭嘭膨”的聲音(也許不準確,那是一種隱含焦灼、急躁的聲響),打破了原本沉寂的空氣。街面上,發廊、按摩店、雜貨鋪、窗簾店、服裝店、影碟店、五金店、早餐店、圖章店、紙扎店、小超市,一律大開著空敞的門,似乎在等待什么,空氣中沉淀下寂寞、冷靜。
老街被遺棄在一邊,像個風雨中的老婦,丑陋、憔悴。時光,這個庸俗之詞,把老街拋落、遮蔽、埋葬,豆腐坊、小酒館、中藥鋪、染布坊、棺材鋪、鐵器店、裁縫鋪、國營飲食店、農具店、篾器店,連同熟稔的一些人,風吹落葉一般消散。春天來時,青石板上污水橫流,腐爛的霉味襲來陣陣憂傷。
二〇〇二年初夏一天夜里,啞巴用尖刀把老婆劈成兩半,然后去了派出所自首,那間臨河的飯館就此關閉。啞巴女人皮膚白皙,四十來歲,能說會道。有人暗地里留意過,在她家過夜的男人,起碼有十來個常客,且都是鎮上吃公家飯的男人們。這都是傳說,不足盡信。而慘劇發生的那夜,有三個男子當場被啞巴抓住卻是事實。在啞巴老婆撕心裂肺的叫聲里,偷情的男人比兔子還跑得快。
二〇〇五年冬天,老瓜喝醉酒后騎摩托車去鄰鄉賭博,車子撞在大樹上,同去的三個后生死了兩個。不到一個月,新街上又有幾個人,因買六合彩起了爭執,雙方用棍棒、殺豬刀互斗,沒幾下就捅死一個。死者恰好躺倒在新建的文化活動室門口,血流了滿地。
二〇〇七年正月,遠在廣西的光頭仔回來,住了幾天后,又走了。不久,有人跑到鎮政府門前哭鬧,說是光頭仔騙走了幾十萬塊錢,被騙人家竟有幾十戶。有知情者說,他在外面搞傳銷多年。派出所長登記了情況,把人打發走。不知案子破了沒有?
小鎮——我居住過二十八年的故鄉,已是橫在我內心的一塊陌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