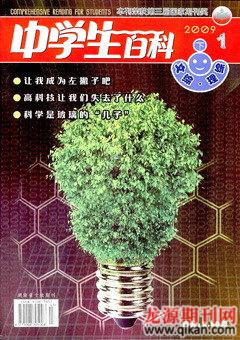校服的回憶
胡 堅(jiān)
一百多年前,開(kāi)眼看世界的中國(guó)文人游歷西歐,看見(jiàn)外國(guó)小孩逢年節(jié)穿的新衣,乃是筆挺的禮服套裝,腰間甚至還掛著一把縮小的佩劍,覺(jué)得萬(wàn)分驚奇——難道這外國(guó)小孩不長(zhǎng)個(gè)子?
早年間學(xué)生參加學(xué)校的集體活動(dòng),須得統(tǒng)一打扮,都是白衫藍(lán)褲配白色帆布球鞋,且不論男女皆臉蛋撲粉,眉心還要一點(diǎn)紅。雖然化妝毫無(wú)技術(shù)可言,各人因家境不同,白衫藍(lán)褲的質(zhì)地也各不相同,球鞋中還有涂粉筆冒充白色魚目混珠的,但趕上登臺(tái)合唱,前后排錯(cuò)開(kāi)呈波浪狀搖擺,也頗有聲勢(shì)。
再往后幾年,各家自備的“藍(lán)白配”被淘汰,制式批量購(gòu)買的運(yùn)動(dòng)衫式樣校服開(kāi)始流行。在我后半截學(xué)生生涯里,針織夾克校服基本是當(dāng)多功能服在超負(fù)荷“服役”——夏天貼肉穿,冬天套在毛衣外,正式場(chǎng)合用于接受值日生的著裝檢查,娛樂(lè)時(shí)間可充當(dāng)超人的斗篷,武斗時(shí)還能卷在小臂當(dāng)天龍盾,如果需要扮演七進(jìn)七出的趙子龍,在這衣服的懷里塞進(jìn)去一個(gè)劉阿斗也是綽綽有余……
很容易想象,要完整地履行如上職責(zé),這神奇的運(yùn)動(dòng)服至少得比正常著裝大上兩三個(gè)號(hào)——學(xué)生時(shí)代里,幾乎所有人都是如此,卻很少有異議。一個(gè)擺在禿子腦袋上的硬道理幾乎說(shuō)服了所有的人:小孩長(zhǎng)個(gè)兒,買大點(diǎn)以后能穿。而同時(shí),還有一個(gè)更隱晦更硬的道理卻被遮蓋:大衣服小個(gè)子能穿,小衣服大個(gè)子卻穿不了。為了讓一條生產(chǎn)線上的產(chǎn)品盡可能地給更多人穿上,最簡(jiǎn)單的辦法就是做大一些。
讓一件衣服,盡可能適應(yīng)更多的人。這就是現(xiàn)代成衣業(yè)避而不談的精髓所在,而為此付出的代價(jià)就是,抱著這樣一個(gè)目的生產(chǎn)出來(lái)的產(chǎn)品,很難真正地適應(yīng)每一個(gè)人。
上個(gè)世紀(jì)最后十年的學(xué)生校服,在材料選擇,款式設(shè)計(jì),穿著舒適上都可當(dāng)做是最軟的柿子,因而成為一個(gè)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這個(gè)矛盾造成了嚴(yán)重惡果:在我最虛榮,最向往寶馬華服的青蔥歲月里,殘酷的現(xiàn)實(shí)卻是一群半大小子穿著敞開(kāi)拉鏈兜住屁股的針織夾克校服混跡于錄像廳,集體羨慕香港電影里同齡人筆挺的正裝校服——海軍藍(lán)上衣,貼兜,金屬扣,卡其褲。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今天,我當(dāng)年的同學(xué)里大多數(shù)人仍不知道這種上衣名叫blazer,褲子名叫chino,但是這并不妨礙在觀看北京奧運(yùn)會(huì)開(kāi)幕式時(shí),他們能一眼認(rèn)出美國(guó)隊(duì)和日本隊(duì)穿著的就是這種玩意。
中國(guó)近代歷史上服裝的幫派很有意思:寧波學(xué)徒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紅幫”;偽滿殖民時(shí)期傳下的“日本派”;十月革命逃難帶到中國(guó)的“蘇俄派”……列強(qiáng)爭(zhēng)霸,租借殖民,講的不是西裝工藝,更像是帝國(guó)主義在殖民地扶植的代理人戰(zhàn)爭(zhēng),仿佛回到波濤詭譎的20世紀(jì)初中國(guó),前度劉郎之感油然而生。
一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紅幫裁縫還在國(guó)營(yíng)廠家里替蘇聯(lián)專家制造西裝和大衣,蘇俄派傳人則在軍工廠里負(fù)責(zé)軍裝生產(chǎn),那是一個(gè)沒(méi)有粘合襯,一件西裝要用人手千針萬(wàn)線的時(shí)代……
那是一個(gè)過(guò)去的時(shí)代,一些過(guò)去的故事,早已不再時(shí)髦了。年青一代似乎一點(diǎn)也不在意針織面料夾克式的大袍子套在身上——當(dāng)然他們或許更喜歡美國(guó)黑人的大褲襠和機(jī)器做出來(lái)蕾絲小花邊,也許他們還喜歡disco球下面亮閃閃的化纖面料?不知道,我已經(jīng)告別校園。現(xiàn)在的校服,穿的人滿意嗎?
編輯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