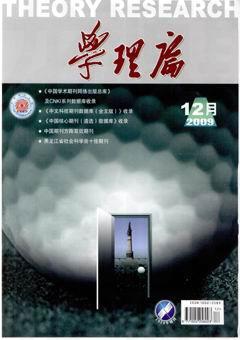哲學視野下的詞之功能論
周建梅
摘要: 哲學家把人之整體人格分為本我、自我、超我三個層面,文學是人學,文學對人之整體人格進行了具體化肉身化的表現。詞學是心學,文學部類之一的詞對人格三層面中的本我世界進行了充分發顯。隨著詞史的發展衍變,詞心與人之整體人格的交集圈在不斷地延展擴大。
關鍵詞: 哲學;文學;詞;人格
中圖分類號:B01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31—0114—02
文壇素有“文學是人學”的說法,文學可以顯影出作為“魂生命”的人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在文學各個部類中,詩文主要用來言志傳道,志向和道統關涉人的理性精神,與人之整體人格中的自我、超我層面相關。詞則多用于緣情,情感是本我世界中的主體內容,與詩文相異,詞對人格中的本我層面進行了充分發顯。哲學家有言,事物的靜止是相對的,運動是絕對的,詞之詞心亦如此,它對人之整體人格的受容范圍隨著詞史的演進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
“人是他的無意識的傀儡,只有把黑暗的無意識深層照亮,人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1] 蒙田寫道:“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2]。認識自我是將自我從蒙昧中解放出來達成自由生命的重要一步。那么人通過什么方法才能完成這一對生命來說至關重要的步伐從而成為自己的主人呢?“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姜夔《續書譜》)、諾瓦利斯說:“一種藝術品,是自我的可以看得見的產物”[3] 、“靈祗籍之以致饗,幽微籍之以昭告”(鐘嶸《詩品序》),從上引文論中可知文學藝術可以把創作者心門內的萬千氣象為自己和他人化作觀照和認識的對象,創作者可以籍此收獲整體生命的自由。“當先養其琴度,后養其手指”、“未始是指,未始非指,不即不離,要言妙道固在指也”(徐上瀛《溪山琴況》第六節),與文學相比,藝術“指月之指”的技術阻隔更難跨越一些,它對人格的顯影不如文學來得直接。臺灣著名作家龍應臺曾說,文學“最重要最實質最核心的一個作用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4],此“看不見”的“幽微”中物即人的主體精神世界,文學可以方便快捷地將之具體化肉身化,從而成功地對創作者的獨異靈魂起到照明和敞亮的作用,這便是人文學者所言之“人文合一”“文學是人學”的觀點,1928年前蘇聯作家高爾基解釋自己所從事的寫作職業的性質道:“不是地方志學,而是人學。”(高爾基《論文學》)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三中說:“人文合一,理所固然。”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見之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人論文,以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之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蘇軾《南行前集敘》)生命體充滿郁勃的精神世界滿溢而成天真自然之文,一切都是人本的真實呈現,自然界的節序變換、生命體的遭際境遇、大千社會的風云變幻都可以成為人類豐富精神世界的感發之源,文學顯影著這一切在人類精神上留下的所有印痕,且以活生生的生命體的形式在顯影,在這個氤氳著生命氣息的文學場中發露著“人的靈魂、內心世界、人的感覺、感受、情感、情緒、思維、人的無意識……以及這整個像海洋一樣豐富的精神世界的瞬息萬變的形態、有形無形的運動軌跡”[5] ,故我們可以逆文溯人,從文中觸摸和感受作為創作者人之全人的整體人格。
哲學家對人之整體人格進行了細分,將之分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go三個層面。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它是追求完美的沖動或人類生活的較高行動的主體”[6], “本我”是“精神領域或精神力量最原始的部分,它包括一切遺傳性的東西,一切與生俱來的東西”[7],自我代表著理性和常識,它監控并壓抑著本我中不為超我所許可的部分,使之不能隨意流露到顯意識層面。各個朝代的不同文學部類由于體性、文化功能、文學傳統等原因,對人格三層面的受容范圍并不相同,那么就文學部類之一的詞而言,它與哪一部分最相契合呢?
“他們在一些優秀詞作中所表現的情,已不是過去詩中常見的與是非道德判斷相關的喜怒哀樂,而是內心深處的悵惘、凄迷、孤寂等很難說清為什么而又需要表達的真摯情思和細膩感受……在表現人的內在真情方面開拓出了詩所未達到的深度和領域。”[8]……詞被眾多文論家視為各種文藝之筐中發抒真情實感的理想之筐,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鐘書先生曾說,中國文人向來是文以載道,詩以言志,而詞則用來言詩中言不得的志,詩中言不得的志即為個人私生活空間中的私密情志,創作者將之轉移到緣情之詞中表達,后漸漸形成了某種習套,“長期以來,人們為詩詞分別定位于兩種不同的功能,甚至出現了一見緣情之詩便說‘風期未上,一讀言志之詞即謂‘要非本色的偏執。”[9] “詩言志”、“文載道”、“詞緣情”幾成文體功能定論和創作者寫作時的思維定勢。
朱自清先生指出“這種志,這種懷抱,其實是與政教分不開的。”[9] 以人格三層面言之,言志傳道表達政治倫理大話語的詩文多體貼傳達著人之整體人格中的超我、自我層面。情感是詞之表達重鎮,情感是本我中的主體內容,文學部類中的“緣情”之詞對人之整體人格中的本我層面進行了充分發顯。“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劉體仁《七頌堂詞繹》),“溫柔敦厚”斯為理性世界中正平和的要求,是生命體在超我要求、自我監控下的壓抑表現,“詞中妙境”帶來的“陡然一驚”便是作者之真情對讀者之真情的興發感動、讀者之真心對作者之真心心有戚戚焉的領受。與志向道統的隸屬地腦之域不同,本我情感存在于感性充盈的心之府,故詞常被稱為“心緒文學”,模仿上文“文學是人學”的話語結構,我們可得出相對偶之命題:“詞學是心學”。
詞與人之整體人格的交集圈有一個漸變的發展歷程,“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用于應歌的無謂之詞絕大多數是無我之詞,篇中少有作者之心魂印痕和面影閃現,發軔期的花間詞即是如此,花間詞表現對象物化、客體化的主潮為南唐詞人所改變,南唐二主的不少作品中已能呼吸領會到作者之特異心魂,“詞曲起于燕樂,往往流于纖艷輕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詞來寫他凄涼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詞的意味。他的詞不但集五代的大成,還替后代的詞開了一個新意境。”[10]“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類的本我情感突破了花間艷情詞的樊籬進入到詞體之中,這一傳統亦為晚唐詞人馮延巳、宋初詞人歐陽修、晏殊所承。詞中創作主體本我情感融入的又一次新變肇始于長調慢詞對詞壇主流地位的占領,長調慢詞結構繁富,體積擴展了很多,不象小令那樣可以在靈感的助益下一筆揮就,往往需要加入更多思力的安排,這意味著詞“小道”、“薄技”的地位開始有所改變,這是詞之尊體的起始,尊體意味著詞與詞人的主體情感有了更多勾連的可能,這一可能性隨著長調之詞的普及漸成詞壇現實,詞對創作主體本我人格的覆蓋面積越來越大。
詞中創作主體人格融入的再一次新變發生在蘇軾筆下,在他筆下開始了人格三層面與詞的廣泛融合,王兆鵬在《論東坡范式——兼論唐宋詞的演變》一文中說東坡詞“建立起一種新的范式,即把題材的取向從他人回歸到自我,像寫詩那樣從現實生活中擷取主題,捕捉表現對象,著重表現自我、抒發自我的情志。”[11] 王兆鵬先生此處所言之自我非上言人之整體人格中的自我層面,而是指稱著人之整體人格。蘇軾對詞表現空間的開拓既有詞人詞學觀的影響,亦有宋朝文字獄背景下詩歌傳統表現域收縮和向詞轉移的影響.不過蘇軾“以詩為詞”、將人格三層面都收攏進詞體中的做法在當時僅為詞壇上“別是一家”之舉,尚未成為詞壇主流風尚,大多數詞人仍然籍詞表達著本我心懷。“靖康之難”后以詞言抗金雪恥壯志、表愛國復國壯懷頓成詞壇主潮,當然,詞之傳統功能域“緣情”亦不曾偏廢,兒女情長、人欲風流在詞中仍歷歷可見,人格三層面本我、自我、超我被很多詞人一并收攏入詞,詞與詞人整體人格的交集圈在不斷擴大。胡適說:“到了朱希真與辛稼軒,詞的應用范圍越推越廣大,無論什么題目,無論何種內容,都可以入詞。”(胡適《詞選自序》)[12]
“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奮末廣賁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秾艷,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后,欲離去別見其道而無由。然其寫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萬折以赴聲律,則體雖異而其所以為詞者,無不同也……進么弦而笑鐵撥,執微旨而訾豪言,豈通論乎!”(郭麐《無聲詩館詞序》)詞壇上若許詞的詞心如其作者之獨特靈魂千變萬化,詞壇的豐富多彩印證著創作者生命情調和精神世界的異彩紛呈。
參考文獻:
[1][德]雅斯貝爾斯.存在與超越——雅斯貝爾斯文集[M].余靈靈,徐培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218.
[2][德]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3.
[3]吳瓊.西方美學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7.
[4]龍應臺.為什么需要人文素養[J].書屋,2000,(4):31.
[5]杜書瀛.文學原理——創作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55.
[6][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60.
[7][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綱要[M].劉福堂,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68.
[8]詹安泰詞學論稿[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80.
[9]朱自清.詩言志辨[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5-20.
[10]胡適.詞選[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6.
[11]王兆鵬.論東坡范式——兼論唐宋詞的演變[J].社會科學研究,1989,(4):25.
[12]王易.詞曲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9:1.
(責任編輯/ 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