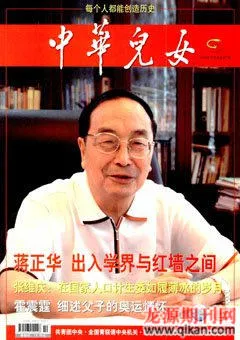我的風雨歲月
劉冰,原名姚發光,河南省伊川縣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共產黨,曾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在八路軍一二九師隨營學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據地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在豫西工作。解放后歷任共青團河南省委書記、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甘肅省副省長、甘肅省委常務書記、第八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從1964年至197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清華大學處于風口浪尖,劉冰作為清華大學的領導成員之一,親歷了這場銘心刻骨的風雨,而其中的眾多內容系首次披露,如上書毛主席。本刊從2008年第10期開始,對劉冰新近再版的《風雨歲月》一書中的部分文章進行選載。
與遲、謝的斗爭公開化
四屆人大會議之后,周總理的病情加重,聽說鄧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委托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8月中旬,學校教改處的負責同志在市委聽了鄧小平同志8月3日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講話的傳達,回校向我作了匯報。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同志講了對科技人員的政策,他說:“要發揮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要搞‘三結合’,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員叫‘老九’嗎?毛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就是說,科技人員應當受到重視。他們有缺點,要幫助他們,鼓勵他們。要給他們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地研究一些東西。這對于我們事業的發展將會是很有意義的。”聽了匯報,我認為小平同志的講話,特別是對科技人員的政策,對學校工作,尤其對知識分子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因此我決定按市委規定,于當天下午召開了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作了傳達。我在會上強調大家要認真學習,領會精神,結合實際,貫徹執行。夜里遲群、謝靜宜回到學校,他們安在黨委辦公室的“釘子”向他們報告了下午召開常委擴大會傳達鄧小平同志8月3日講話的事。第二天上午,謝靜宜來到我的辦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開會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為什么不告訴我們一聲?我和遲群都告訴過你,凡是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向下傳達時要經過我們,而你為什么不先告訴我們就傳達呢?”她滿臉怒氣,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來,活像一尊兇神站在我辦公室的中央,盛氣凌人地重復著:“我們不是沒有告訴過你,為什么你急著傳達?”這明顯是無理取鬧,以勢壓人。我壓著怒火,先請她坐下,然后說:“鄧小平同志是黨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講話為什么不能傳達?而且這個講話是北京市委在專門會議上布置讓傳達到各單位黨委的,你是市委書記,你應該遵守市委的紀律,市委規定要傳達,為什么我不可以傳達?為什么要經過你們才能傳達?難道對黨中央副主席的講話,我這個主持黨委常務工作的副書記沒有權力和義務進行傳達嗎?”在我強烈的反駁下,謝靜宜語無倫次地喃喃地說:“不是說你不可以傳達,而是說你應當先告訴我們一聲。”我回敬說:“傳達后再告訴你們也可以吧?你為什么對‘傳達’這樣惱火呢?難道就因為沒有事先告訴你們嗎?”我的尖銳反問使謝靜宜無言以對,氣呼呼地甩了甩頭發,站起來扭頭走了。
當天晚上,我向惠憲鈞、柳一安、呂方正三位同志通報了上午我和謝靜宜,當面鑼、對面鼓干仗的情況。當時我們正在緊張地研究草擬向毛主席告發遲群的信稿,我和謝靜宜的正面沖突自然得到了他們的全力支持。柳一安同志說:“你頂得好,就要她謝靜宜知道,違反黨的原則是不行的,劉冰這樣的老同志是不好惹的。”呂方正同志說:“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咱們對謝靜宜認識還不夠。”惠憲鈞同志說:“她是幫助遲群的。”柳一安說:“干脆這封信把謝靜宜也掛上。”我說:“咱們還是按原先商定的,把她和遲群有所區別,集中反映遲群的問題。”最后我們商定還是維持原議,對兩人有所區別。
策劃給毛主席寫信
關于給毛主席寫信的問題,還得從頭說起。寫信的最早發起人是柳一安同志。當時,柳一安同志受上級指派,進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后來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主要負責人,學部領導小組組長。他對于遲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惡劣品質和作風早就不滿。從1973年所謂“反右傾回潮”運動開始,遲群明顯地投靠了江青,充當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鋒,柳一安同志從社會上和干部中聽到了不少對遲群的非議和責罵。1975年,鄧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期間,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項指示為綱”(即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各行各業都要進行整頓。對這些精神,遲群非常抵觸,背道而馳。那時候,無論是學部還是清華大學的工作,都是在遲群的直接領導下,柳一安同志在遲群手下工作,要貫徹中央精神感到非常難辦,思想上很苦悶。1975年6月之后,老柳患嚴重失眠癥,經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藥后仍然睡不著覺,就把在學部辦公室工作的李兆漢(當時是國務院科教組的干部,后曾任中國教育報社社長兼黨委書記)、任彥申(當時是清華大學政治部干部,現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找來,訴說心中的矛盾和苦悶,分析政治形勢,議論對遲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種對策。在日復一日長時間的議論中,逐漸地明確了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對遲群怎么看。覺得遲群人很聰明,但心術不正,政治上越來越“左”,是個野心家。遲群是站在江青一邊,反對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的。
第二個問題是該怎么處理同遲群的關系。如果繼續跟著遲群走,不得人心,沒有好下場。如果跟遲群保持距離,進行決裂,要冒很大的風險,準備可能被打倒。但寧可選擇后者,也不能跟著遲群干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采取何種行動。柳一安同志曾經提出要找遲群當面談話,把社會上和黨內對遲群的意見統統端給他,用壓力加規勸的辦法迫使遲群改弦更張。李兆漢同志認為老--柳的辦法不可用,他說:“要看透遲群的本質,這個人心狠手毒,他如果知道你有二心,必然把你置于死地。遲群在清華大學一手遮天,稱王稱霸,單槍匹馬地同他斗爭,肯定不行。在清華領導班子內部,反對遲群的人是多數,但敢怒不敢言,沒有上級領導的介入解決不了遲群的問題,唯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反映遲群的問題。”他認為,要在中央直接過問下,才能解決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如何反映遲群的問題。當時清華大學是毛主席抓的點,是“斗、批、改”的樣板。向中央寫信要避開“方向”、“路線”問題,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為線索,集中反映遲群有野心、驕橫、搞陰謀詭計、破壞民主集中制和黨的優良傳統等個人品質和作風上的問題。
就這樣,1975年7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柳一安同志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告發遲群問題的構思形成了。對此,李兆漢、任彥申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隨后,柳一安找惠憲鈞、呂方正同志商議,意見完全一致,并決定聯合上書。
這三位同志意見如此一致,斷然作出這一抉擇,決非偶然。除了他們三人都是十幾歲參加解放軍,長期受到我黨、我軍優良傳統的教育影響這些基本方面的原因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們三位對于遲群專橫跋扈、陰一套陽一套、背離黨的原則的惡劣品質早已不滿。
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集各單位負責干部會議,會間休息時,惠憲鈞、柳一安、呂方正三位同志把我拉到休息廳一旁的座椅上,告訴我他們三人經過慎重考慮,決定要給毛主席寫信反映遲群的問題。遲的問題很嚴重,如果不反映,我們就要犯錯誤,也對不起主席,對不起共產黨員的稱號。因為我是位老同志,信得過,因此把他們的決定告訴我,征求我的意見。我雖然早就考慮同遲群、謝靜宜要進行斗爭,但一直沒想好斗爭的方法,此時三位宣傳隊的負責人“殺”了出來,真是太好了,“正合吾意”。我當即下定決心要與江青在清華的哼哈二將公開較量,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他們三位的主張,并自告奮勇,由我來牽頭。
政協禮堂的干部會后,當天晚上在惠憲鈞同志的辦公室,柳一安、呂方正我們四人,就給毛主席寫信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們的宗旨是:一定要實事求是,給主席反映問題決不能有絲毫粗心或不實。
信稿審定之后,決定由惠憲鈞把稿子交給軍代表安恩奎同志,囑咐他盡快復寫幾份,爭取盡早發出。鑒于過去寄給主席和中央領導的信件常常被扣壓的教訓,我們又議論了如何保證信能讓主席看到的方法。經過研究,認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為那樣容易落人謝靜宜、毛遠新、江青之手,信應經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副主席轉呈主席,只要小平同志能在我們的信上批寫“送主席”幾個字,即使謝靜宜、江青、毛遠新們看見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們就是扣壓了黨中央副主席報送主席的批件。同時憑著我們對小平同志的信賴,一致認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見我們的信,定會轉送主席的。接著又研究信如何能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
1953年到1956年,我曾在團中央負責辦公廳的工作,那時耀邦同志是第一書記,我經常同他接觸,深知他為人耿直,樂于幫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與小平同志來往較多。
曲折投書,胡耀邦助一臂之力
信復寫了幾份。一切準備妥當之后,我給耀邦家里打電話,他夫人李昭同志告訴我耀邦不在家,到科學院上班去了。我告訴她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談,看什么時候合適。李昭和耀邦一樣是個爽快人,她說:“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點鐘到家里來好了。”第二天,我準時去了,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老太太在他們家好多年了,我來過幾次都看到過她。老人家熱情地接待了我,說:“耀邦上班去了,你到房里休息。”她一邊說一邊領我穿過院子來到過廳旁邊的書房里,給我倒了滿滿的一杯茶水。我向她表示感謝,問:“今天是星期天,耀邦還上班呀?”她說:“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來,帶個飯盒,午餐時讓人給熱熱就吃。他呀!對自己嚴格啊!”老太太離開后,我靠在沙發上,陷入了往事的回憶:1964年我來看耀邦,那時他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因為他對農村“四清”一些“左”的東西有看法,受到批評、責難和排斥,回京呆在家里。但他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我說:“對基層干部要有正確的估計,在我們黨領導下,大多數基層組織,大多數基層干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如果遍地是虱子,到處有問題,我們黨在農村取得的偉大成績怎么解釋?!我歷來主張對人對事要公道,要實事求是。”1974年我來看耀邦,“文化大革命”中批了他好幾年,那時還未分配工作,又是待在家里。見到我,他說:“我沒事就看書,想問題。王明路線是1931年到1934年共四年,林彪從‘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講話)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是五年多一點,這兩次都使我們黨受到大損失,尤其是在干部問題上,這次受到的損失比王明路線還嚴重。這是教訓啊!”耀邦同志的深刻分析,至今言猶在耳。就是這次談話,他說到了遲群、謝靜宜,想來他不會料到,今天我來找他就是為了這兩個人的事。我看到他書桌上放著列寧和毛主席的著作,走過去翻了一下,看到書中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論述用紅鉛筆畫了圈圈杠杠,很顯然,他是在研究科學技術方面的政策問題。聯想到1974年我來看他時,他正在讀列寧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在書中畫了許多圈圈、點點、杠杠。那次他從這本書說到王明和林彪,說到他沒事就看書、想問題。現在他有事干了,更是要看書想問題了,這是耀邦的習慣,也是他的性格。
“啊!劉冰來了!”是耀邦親切的聲音,把我從回憶中拉了出來。我說:“4點鐘我就來了,你星期天還上班?”耀邦說:“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我說:“有關遲群、謝靜宜的問題。”然后我把這兩人的問題概略地講了一下,說明我們寫給主席的信想請他幫助送給小平同志轉呈主席。耀邦從茶幾上拿了一支煙,邊找火柴邊說:“記得去年我給你說過這兩個人,剛才你講的他們那些事是必然的,他們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機嘛!這種人在咱們的干部隊伍中不是個別的。”他吸了口煙,接著問:“你寫給主席的信,帶來了沒有?”我一邊回答“帶來了”,一邊從口袋里拿出信稿說:“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給了他。他戴上老花眼鏡,把信仔細看了一遍后說:“你們的信要實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實說話。”我說:“耀邦同志,你說得對,我們特別注意了要用事實說話。”“你們信中的‘裝瘋賣傻’、‘亂蹦亂跳’,這些是形容詞,是空話嘛!”耀邦回答說。我解釋說:“這不是形容詞,他當時的具體情形就是這樣,只能用這樣的詞,才能描述他的真實情況。”他說:“只要符合實際就行,切記不要說空話。”他接著說:“我支持你,能幫助就幫你。我現在是科學院的負責人,你是清華大學的,和咱們在團中央時不一樣,不屬于一個組織系統,從這一點上說,我幫你轉信不合適。我告訴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這樣更好。”我說:“小平同志不認識我,那怎么行呢?”他說:“你與南翔在清華,名字他會知道的。”我說:“事先沒有聯系,猛然到門口,讓哨兵給捉起來,那才不好呢!”耀邦笑了:“這樣吧,你從郵局給寄去,行嗎?”他問我。我說:“那樣不牢靠,我怕丟了。”他說:“這樣吧,你給小平同志的秘書打電話,問問他信怎么送。”耀邦告訴了我王瑞林秘書的電話號碼。我當即撥通了電話,正好是王秘書接的,我向他說明了我的單位、職務、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聽出,王秘書很客氣,他說:“你的信可送國務院。”我說:“我沒有中南海的通行證,送不到國務院。”他說:“你從郵局寄也行。”我說:“我怕信件遺失。”他說:“那不會的,你寄好了。”在電話上我不好意思和王秘書再講下去了,我對他表示感謝,把電話掛了。打電話時,耀邦親切地站在電話機旁邊,這時他問:“王秘書最后怎么說?”我說:“他還是要我從郵局寄。”“那你就寄嘛!”耀邦懇切地說。“不能寄,我不放心。”我回答說。他說:“我看你直接送他家里,這最保險。我告訴你他住在X街XX號,門前面是個小胡同。你大膽些,怕什么。”耀邦同志該做的都做了,對于他的真誠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6點多鐘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擾他,便說:“耀邦同志,我就按你說的辦吧!謝謝你。”和他握手告辭了。
出了大門,坐到車上,我改變了主意,覺得貿然到小平同志家里太冒失了,先回學校再說。我告訴司機回學校。在返回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辦?忽然想到通過警衛部隊是個辦法。負責警衛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隊?八三四一還是衛戍部隊?不管是哪個部隊,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復思索著。車子到了家門口,停了下來,我還坐在車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經司機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回到家里,我給惠憲鈞打電話,要他們三人晚8點在辦公室等我。在老惠辦公室,我把見到耀邦和給王秘書打電話的情況作了通報,并講了我在車上考慮的送信辦法。聽后,他們三人對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表示贊成我提出的通過警衛部隊送信的辦法。惠憲鈞說:“我給參謀長打電話問問是不是我們師負責警衛。如果是就好辦了。”接著老惠給馬清沅副參謀長撥了電話,當參謀長得知是送信的事,他熱情地告訴老惠,是他們師負責警衛。然后,他告訴司令部值班室,把惠憲鈞去送信的事通知駐地警衛部隊。為了更落實,他又親自給那里的警衛部隊負責人打電話。一切安排妥當之后,副參謀長電話告知惠憲鈞,要他第二天上午9點準時趕到,要穿軍服,軍風紀要嚴整,下車后告訴警衛人員自己是師部的,在清華支左,來這里送信,警衛員會接待他的。按照副參謀長的囑咐,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齊,格外精神,驅車從清華園出發,準時趕到鄧副主席住宅門前。老惠下車后,警衛人員禮貌地問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長同志熱情地接待了他,并說副參謀長昨晚打過電話。老惠對排長同志的支持表示感謝,把信交給了他。排長請老惠休息,他進院里送信去了。過了不久,他滿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對老惠說,因王秘書正在忙,讓他轉告清華的同志,信收到了,鄧副主席在中央開會,中午回來就把信交給他。老惠說,這時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鄧副主席今天就能看到我們的信,真是高興得沒說的了。他再一次感謝排長和警衛同志后告辭了。對老惠的送信之行,我們三人和他一樣,“高興得沒說的了”。
焦急盼望主席的回信
緊接著,我們研究了信送走后的工作。我們認為,雖然已與遲、謝公開較量了,但不能大意,要謹慎,在未得到毛主席對信的指示之前,從組織原則上不能給他們留有空隙,對這兩人即使表面團結也要注意。同時還要注意在原則問題上不能含糊,學校工作今后主要靠我們來做,一定要按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的精神抓工作。現在開始準備,一個星期后去向市委報告這兩人的問題。到市委一個“臺階”也不隔過,要按組織順序,先向科教組負責人口頭匯報,然后把給吳德同志的信交給科教組轉呈,并請科教組負責人轉告黃作珍(分管高校的書記)、吳德,我們隨時聽候召見,爭取向他們口頭匯報。一切研究妥當之后,真是如釋重負,美美地睡了兩晚上好覺。我們精神上的愉快,尤其在于對主席的堅信不移,認為主席馬上要看到我們的信了,主席定會懲惡除弊,定會使我們大喜過望。
信送出已經一個星期了,按原定計劃該去北京市委了,但主席是否看到了信呢?如果還未看到,去市委是否有點早呢?還是慎重為好,在時間上要有足夠的保險系數,做到十拿九穩,等主席看到信后,再走第二步。這樣就往后推延了兩天,第九天我和惠憲鈞去了市委。那天下午2點半,市委科教組組長肖英和軍代表接待了我們。因為遲群、謝靜宜一向就不尊重市委科教組,在工作上常給他們出難題,相互之間有著較深的隔閡和矛盾,所以當他們知道我們是揭發遲群、謝靜宜的問題時,顯露出格外高興的面容。肖英同志說:“我們也聽到了一些對遲群的傳說,那是從別的學校傳來的,好像大家對這個人都有意見。”軍代表說:“我去看看丁國鈺同志是否在辦公室,請他也聽一下匯報。”我們表示非常贊成,常務書記丁國鈺也能來聽聽,那是最好不過的。但他使我們失望了。軍代表回來說:“老丁在辦公室,他說工作忙,不聽了,讓我們聽匯報時作下記錄。”這位丁書記是真的那么忙嗎?在我看來只不過是推脫的遁詞罷了。在那個年代,一些干部用這種辦法回避矛盾是司空見慣的事,所以我們也就不介意了。在肖英同志主持下,匯報了兩個小時,我們主要講了信中寫的那些問題,所不同的是,口頭講的比文字更詳細。匯報完了之后,肖英表示,要把記錄整理一下,向市委作匯報,有什么意見和指示,他一定及時轉告我們。我們當然對肖英和軍代表耐心聽取我們的匯報表示感謝。因為這件事對清華來說關系重大,因此我又作了如下的說明:第一,反映清華領導班子中的問題,我們是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先給科教組匯報,并請你們也向市委匯報,肖英同志剛才說的,正是我們所希望的;第二,因為關系重大,除口頭匯報外,我們還給吳德同志寫了信,請你們二位務必把信轉給他;第三,黃作珍同志是分管高等學校工作的書記,請你們二位將我們的匯報也報告給他;第四,我們要求吳德同志接見我們,隨叫隨到,我們靜候通知,如果他沒空,委托黃作珍同志也行;第五,請肖英同志和軍代表給我們保密。肖英對我說的幾點,表示凡屬科教組的,他們都可辦到,至于吳德接見的事,他們只能轉告。
回到學校,我們除了負擔著緊張的日常工作,天天都在盼望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接見。我們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焦急地等啊,盼啊!日復一日,但沒有任何消息。我想,毛主席已是耄耋之年,日理萬機,對于我們的信,可能不會馬上處理,我們要耐心等待。可吳德同志尚在壯年,最多60歲,又是我們的直接領導,難道他會對直接領導下的一所全國重點大學負責人反映的重大問題漠不關心、不予理睬嗎?如果那樣還談得上有群眾觀點嗎?還像一位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老同志嗎?經過思考,我否定了無根據的猜想,滿懷希望地等待著吳德同志的接見,但一直沒有音信。
(未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