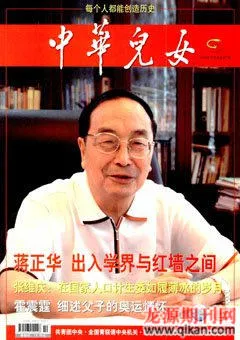懷念與施光南同學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轉瞬間,施光南同學已經離開我們18年了。
1990年4月18日,他的夫人洪如丁給我家打電話,說光南生重病了,問我們怎么辦?那時,我正好出國在外,我愛人曾曉前告訴她馬上去找文化部徐文伯副部長,并告訴了她聯系的方法。4月24日晚我回到北京后,第二天便去協和醫院看光南,但那時他已經完全不省人事了。據洪如丁說,犯病前光南在家中正陪著女兒施洪蕾用鋼琴彈著他作的音樂劇《屈原》的曲子,教她怎么唱,突然就昏過去,雖然文化部立即派人來送進醫院搶救,但再也沒有清醒過來。5月2日光南走了。他是1940年8月22日生的,還不滿50歲就駕鶴西去了。醫院診斷是由于腦血管有一段畸形,導致破裂而死亡。光南生前自恃身體很好,幾乎沒有去醫院看過病,在他的病歷上什么重要的記載都沒有。
中學同班的深厚友誼
我與光南是1949年9月在當時的華北育才小學(現已改名為“北京育才學校”)上同一個班而認識的。我們這個學校是在解放戰爭中從解放區行軍到北京的,進城后又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孩子。光南的父親施復亮,母親鐘復光,都是老革命。施復亮與黃炎培等人一起創立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建國以后擔任新中國的第一任勞動部的副部長。1960年我聽施復亮講才知道,他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組建過青年團,入黨后又擔任過黨的一定的負責人,大革命失敗后,他失去了與黨的聯系,但他仍然堅持革命,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成立的民主建國會,一直與共產黨密切合作,最后成了新中國的參政黨。施復亮是一個文化人,這個特點在光南身上也明顯地體現出來。
光南在班上非常文靜,又擅長音樂,所以有的同學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姑娘”。1951年秋,我們一一起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附中二部(現在改名叫“北京第101中學”),又被分到同一個班,一直到1957年秋高三畢業。在整個中學的六年,我們兩個人的私交是非常好的。我非常佩服他的才華。他常給我講一些我這個從農村來的孩子從來沒聽過的故事。比如他說中國的文字有諧音,過去有一位文人在湖上蕩舟時寫了一副對聯:“兩舟并行,櫓速不如帆快;八音齊奏,笛清難比簫和”,就把眼前的情景與歷史上的幾個人物魯肅、樊噲、狄青、蕭何聯系起來了。又如,一個高班同學教我講一種“瞎子話”,就是把一個字音的聲母與韻母分開,用一定的規則把聲母與另外一個韻母拼,再用另外一個聲母與原來的韻母拼,這樣一個音就變成兩個音,如“你”,聲母是“n”,韻母是“i”,讀“捏己(nie-ji)”,別人就聽不懂了。我想把這種話教給他,但他說,你看小說《鏡花緣》,其中講到一個書生到了女兒國,那里的姑娘非常有才華,他卻像一個大傻瓜,姑娘們問他的問題都答不上來,姑娘們就自嘲說“吳郡大老倚閭滿盈”,這就是中國字的切音。所有中國字的音都可以把一個音分成兩個,只要有時用一個“零聲母”,而中國字發音,韻母是沒有聲母結尾的。古代的字典對字就是這樣注音的,姑娘們說的是“問道于盲”。這才使我對“瞎子話”恍然大悟,后來我用這個方法設計了一種“雙拼方案”。這種方法后來又有很多人研究,并形成了電子計算機一種文字輸入方式。
他迷上了作曲
上中學時我們學校每周放一次電影,光南看完一遍竟能把電影里的主題歌完整地記錄下來。后來他居然把一個唱片中的交響樂分樂器、分聲部地記下譜來。在從初中升入高中這一段時間他又迷上了作曲,經常在上課時也作曲,結果耽誤了聽課,受到一些同學的非議,而我與另外一些同學常常在考試前幫他復習、補課,可喜的是他的考試成績還相當不錯。1954年我擔任了學校的鋼琴組組長后,還主動把他吸收到鋼琴組,讓他練習鋼琴。這樣我們倆之間的關系就更加親密了。高一時,我們班的班主任得了重病,全班51個同學每人給老師送了一個雞蛋,他就寫了一首《五十一個雞蛋五十一顆心》的歌,在全校每學期都有的文藝會演中演出,我做鋼琴伴奏,結果還得了第一名。這樣,他的作曲才能在班上逐步得到認可,終于被接受為共青團員。后來他和馬勇(當時班上的文娛委員)及我還改編過《皇帝的新裝》、《金魚與漁夫的故事》等小短劇。由于他作曲已經小有名氣,學校便委派他編輯《圓明園歌聲》,我也幫助他編,1957年又協助他編了一本《中外民歌選》,里面選的歌曲全部都是他自己寫的,但大多用了假名字。油印時有幾本用的是當時比較高級的道林紙,他專門送了我一本,上面寫著:“見此如見人,久久莫相忘!贈給紹祖。光南1957年7月1日。”
就在這年的7月,我陪他一起去海淀區的一個派出所辦理了他離校的手續。他說他不準備考一般的大學了,而準備去考音樂方面的學校。中學畢業后,他先上了音樂中專,后又上了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后分到了天津歌舞團,寫了一些好歌曲,在社會上也有相當影響。我考上了清華大學,后又當了全國學聯主席,調到團中央機關工作,兩人作為朋友也經常來往。我覺得他仍然保持了在101中學時的一些好傳統,對他在音樂學校同學中的一些不良習慣和作風很看不慣。在“文革”中他也受到了批判。我還記得在“文革”后期有人批評他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有修正主義的問題。那時我已經調到王震同志處當秘書,有一次我們去天津出差,我還專門去看望過光南,并向天津市的有關領導同志講他的情況,希望保護他一下。后來我又幫助他聯系調到北京來。
他對社會上的一些弊端表示憤慨
“文革”以后,我和施光南的來往就更多了,他的處境也相當好,中央領導同志很看重他,推薦他當了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副主席、中華全國青聯副主席,還當選黨的十三大的代表,甚至還想推薦他當文化部的副部長,但被他回絕了。這個時期,他也對社會上的一些弊病表示憤慨,如《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元),我就是聽他講的。我還記得有一件事情,當時在團中央工作的陳昊蘇講他父親陳毅如何對待老同志的事,其中說到光南的父親曾背叛過革命,光南非常生氣,要我幫他轉一封信給當時黨的負責人胡耀邦同志,耀邦把信批給了昊蘇,吳蘇立即去向光南道歉,后來他們兩人竟成了好朋友。1982年光南又送了我一本《施光南歌曲選(獨唱)》,上面寫著“紹祖同學指正。光南。82年新年”。現在這一本和1957年送給我的歌曲集,都珍藏在我的手中。
他沒有聽到他作的會歌在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式上演奏
1988年底我調到國家體委工作,正好趕上我國要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在1989年春末夏初,我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當時為準備舉行亞運會需要我國編一個會歌,但是負責這項工作的同志竟找不到一個作曲家來創作這首歌。我知道這個情況后,立即找到光南,他很快就寫出了會歌。后來亞運會組委會有人想把這首歌換掉,我以這是亞運會組委會開執委會時定的,要換也得經過這個程序為由而沒有換。就在北京亞運會要正式開幕前不久,他溘然而去了,竟沒有聽到他自己作的會歌在開幕式上演奏。
光南去世后,也是他北京101中學的同學、當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曾慶紅把此事報告給了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可能用了“人民音樂家施光南”這個詞,因此這個詞就傳開了。我認為,用“人民音樂家”來形容光南,也不算是過分的。他短暫的一生,創作了大量的歌曲和其他音樂作品,不僅數量頗多,質量也頗高。我作為一個不甚懂音樂、但又相當喜歡音樂的人,感覺光南的音樂作品,第一是有時代性。他的歌可以說是反映了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的時代的心聲。我們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領袖,我們追求和向往美好的未來,我們對粉碎“四人幫”十分興奮,等等,他就寫出了這樣的歌。第二是有人民性。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的力量是無比巨大的,他寫的歌都是歌頌人民中各種各樣人物的,我們唱了他的歌就感到自己與人民融合在一起了。第三是有群眾性。他的很多歌都是從群眾生活中的具體小事出發,無論是“打手鼓”,還是“吃葡萄”,無論是思念參軍的親人,還是放眼希望的原野,都感到非常親切。第四是有優雅性。他的歌朗朗上口,柔柔繞胸,曲調動聽,節奏明快,體現了中國文化中庸、和諧的特點。第五是民族性。他不僅寫漢族的歌,也寫了很多我國兄弟民族的歌,惟妙惟肖,很有民族情趣,這對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是十分有利的。第六是國際性。他創作了不少涉外歌曲、區域歌曲和完全不同文化的外國歌曲。這既是學習外國文化,又是與外國文化交流,對構建和諧世界是大有好處的。
可惜光南只活了不到50歲,否則他還會創造出更大的業績。但話又說回來,人生的價值并不完全在于壽命的長短,只要是對人民做出了貢獻,那就是有意義的。施光南的一生應當說是對人民做了很大的貢獻,他的生命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想起了一句我們中國的古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如果我們反過來用,一個人即使壽命很長,活了100歲,但他虛度年華,碌碌無為,或者甚至他還危害過人民,那還有什么意義呢?真還不如只活了50歲、但對人民做出了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