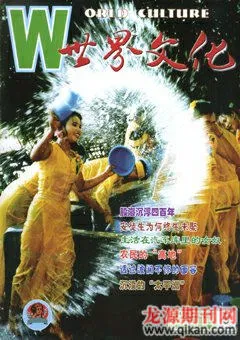對(duì)理性與文明的詰問
眾所周知,在18世紀(jì)的歐洲爆發(fā)了一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啟蒙運(yùn)動(dòng)。由于它將理性奉為最高權(quán)威,因而這一時(shí)期又被稱為“理性時(shí)代”。崇拜理性成為時(shí)代精神的主旋律,進(jìn)步、發(fā)展、理性、文明成為人們堅(jiān)定不移的新信仰。在改造自然和征服世界的狂熱中,人們虔誠(chéng)地企盼著“理性王國(guó)”的到來(lái)。被譽(yù)為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始人的丹尼爾·笛福在其《魯濱遜漂流記》中通過對(duì)魯濱遜一系列傳奇經(jīng)歷的逼真描繪,講述了一個(gè)關(guān)于啟蒙理性的神話,其中明顯透露著他對(duì)人類文明與理性發(fā)自內(nèi)心的樂觀與自信。但理性真的能使人遠(yuǎn)離野蠻,變得文明而進(jìn)步嗎?甚而言之,人自身真的是那么富于理性嗎?同期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格列佛游記》卻發(fā)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并以其諷刺的鋒芒無(wú)情地戳穿了這一美妙神話。
像《魯濱遜漂流記》一樣,這部小說也是在作者59歲時(shí)出版的,因而凝結(jié)了斯威夫特大半生對(duì)人生和社會(huì)的體驗(yàn)與思考。但不同于笛福的是,作為一代諷刺大師,斯威夫特卻以其尖刻而犀利的筆鋒刺向了啟蒙主義日漸膨脹的理性,通過剖析政治、科學(xué)、倫理、法律、思想等領(lǐng)域的非理性現(xiàn)象,對(duì)人類的理性本質(zhì)提出了深刻的質(zhì)疑。首先,特定的政治閱歷和敏銳的洞察力使他對(duì)英國(guó)統(tǒng)治階層的罪惡洞燭幽微。通過格列佛在小人國(guó)的經(jīng)歷他生動(dòng)地揭露了英國(guó)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腐化墮落、爭(zhēng)權(quán)奪利、窮兵黷武、嫉妒賢能等罪惡行徑。朝廷官員因?yàn)樗┢ぱズ蟾母叩筒煌譃閮牲h,長(zhǎng)年勢(shì)不兩立,明爭(zhēng)暗斗;兩個(gè)國(guó)家之間因?yàn)槌噪u蛋時(shí)應(yīng)該先打破大端還是小端的意見分歧而連年血戰(zhàn),勢(shì)如仇敵;國(guó)王選拔官員不是靠其才德,而是根據(jù)他們?cè)诶K上跳舞時(shí)間的長(zhǎng)短。作者就這樣以漫畫般的方式揭露和嘲諷了英國(guó)政府內(nèi)政外交中黑暗而荒唐的內(nèi)幕。既揭穿了這個(gè)自詡為“道德、虔誠(chéng)、榮譽(yù)、真理的中心,世界的驕子,全世界敬仰的國(guó)家”所具有的虛偽本質(zhì),也令讀者窺視到理性力量的虛妄與脆弱。
啟蒙理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科學(xué)理性。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甚囂塵上的科學(xué)崇拜,斯威夫特也潑了一盆冷水。格列佛在參觀拉格多科學(xué)院時(shí),發(fā)現(xiàn)那些“了不起的科學(xué)家”們?cè)谘芯咳绾螐狞S瓜里提取陽(yáng)光,如何將糞便還原為食物,如何用豬來(lái)耕地以及如何用蜘蛛來(lái)紡織,甚至有的在試圖發(fā)明一種能夠改變?nèi)祟愃急嬷R(shí)的機(jī)器。通過對(duì)這些奇思怪行的描述,斯威夫特不僅批評(píng)了科學(xué)研究中脫離實(shí)際的弊病,而且對(duì)人們崇信科學(xué)造福人類的思想也表示了懷疑。在小說中,他通過格列佛兩次“炫耀”了人類理性的“偉大發(fā)明”:“用這種方法射出去的最大的彈丸,不但可以一下子消滅一支軍隊(duì),而且能夠把最堅(jiān)固的城墻轟成平地,把載著一千名兵士的船只擊沉海底”。以這種反諷的手法,斯威夫特極大地消解了科學(xué)至上的正當(dāng)性。正因如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斯威夫特是“最早表達(dá)對(duì)現(xiàn)代科技以及所謂‘進(jìn)步’的憂慮的人之一”。
對(duì)當(dāng)時(shí)帝國(guó)主義方興未艾的殖民活動(dòng),斯威夫特也給予了迎頭痛擊。他大膽揭露了這一“文明壯舉”背后那野蠻、殘忍的罪惡行徑和虛偽、反動(dòng)的本質(zhì)。小說中的那個(gè)“飛島”其實(shí)就是一個(gè)高高在上的宗主國(guó)的化身。它鎮(zhèn)壓叛亂所使用的諸如“斷絕他們的陽(yáng)光和雨水”以及“投擲巨石”等辦法正是當(dāng)今帝國(guó)主義實(shí)施霸權(quán)統(tǒng)治所采取的諸如經(jīng)濟(jì)封鎖和軍事打擊等行為的生動(dòng)寫照。而那些所謂的魯濱遜式的 “現(xiàn)代英雄”們,在斯威夫特看來(lái),不過“都是一些亡命之徒,為貧窮所迫或者犯了什么罪,才不得不遠(yuǎn)走他鄉(xiāng)”。他們?yōu)榱恕八压吸S金”,而“進(jìn)行一切不人道的、放蕩的行為,于是遍地染滿居民的鮮血。這一幫專作這種虔誠(chéng)的冒險(xiǎn)事業(yè)的可惡屠夫,也就是派去開導(dǎo)感化那些崇拜偶像的野蠻人的現(xiàn)代殖民者”。他們帶給當(dāng)?shù)厝说牟⒉皇鞘裁次拿髋c進(jìn)步,而是殺戮與掠奪,是欺騙與奴役,是鮮血與淚水。相比于當(dāng)時(shí)像《魯濱遜漂流記》一樣的那些殖民主義敘事文本,《格列佛游記》再次顯出示了它的特異與深刻。
對(duì)斯威夫特來(lái)說,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批判與對(duì)人的省察是密不可分的。現(xiàn)實(shí)的荒唐、怪誕折射出的是人性的墮落和丑陋。《格列佛游記》既是一幅社會(huì)罪惡的諷刺畫,也是一幅人性丑態(tài)的寫真圖。這在小說第四卷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文雅、禮貌、充滿“友誼和仁慈”的“慧馬”面前,格列佛逐漸喪失了作為“唯一有理性的動(dòng)物”的自豪感,以致最終“無(wú)法保持人類的尊嚴(yán)”。因?yàn)槿祟悺爸挥美硇詠?lái)增長(zhǎng)他們的罪惡”:金錢成為滋生貪欲的酵母,政治成為腐敗墮落的淵藪,法律成為混淆是非的藝術(shù),歷史成為顛倒黑白的幌子,科學(xué)也淪為威力空前的殺人工具。理性非但沒有使人類變得文明和進(jìn)步,反而“助長(zhǎng)我們的墮落腐化的天性,同時(shí)連造物主沒有賦予我們的壞習(xí)性,我們也感染上了”。人類甚至連他們身邊的動(dòng)物都不如。因?yàn)樗鼈儭爸痪哂刑焐囊恍┳飷骸保^不會(huì)有那些發(fā)明與創(chuàng)造。斯威夫特像笛福一樣也在小說中設(shè)置了“野蠻人”的角色。但他不是為了以其為參照來(lái)反襯自身的進(jìn)步與強(qiáng)大,反而是通過與“耶胡”的比照來(lái)消解自身,以展示人類及其本性的真實(shí)面目。有人因此認(rèn)為斯威夫特“憎惡人類”,是個(gè)徹底的悲觀主義者。這恐怕有些失之偏頗。愛之深才痛之切。他這樣寫并非出于對(duì)人類的厭惡,只不過是以偏激、徹底的方式揭示出人性中的病苦,以顯微鏡和擴(kuò)音器刺痛人們的視聽,以期“引起療救者的注意”。正如英國(guó)學(xué)者安德魯·桑德斯所說的,“他對(duì)于人類的描繪不僅暗示人類因原罪而固有的墮落,而且暗示人類持續(xù)不斷地沉溺于罪孽中,沒有受到理性自律、利他道德或神授美德的約束”。 的確,警醒“沉溺于罪孽中”的人類并重塑完整而和諧的人性,這也許才是斯威夫特最終極的目的。
斯威夫特還將諷刺的矛頭指向了理性主義的一整套話語(yǔ)系統(tǒng),通過對(duì)其體裁、題材、風(fēng)格的戲仿戳破了其“理性”的外包裝,從而將其貌似合法的思想內(nèi)核淹沒在人們輕蔑的笑聲里。與《魯濱遜漂流記》一樣,《格列佛游記》也采用了游記體的形式,也講述了一個(gè)以獲取財(cái)富為目的而出海遠(yuǎn)游的故事。乍一看,格列佛的身份、欲望、心態(tài)、出行目的以及言語(yǔ)風(fēng)格無(wú)不與魯濱遜如出一轍。但綜觀全文,他們的冒險(xiǎn)實(shí)際上表現(xiàn)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歷程。蘇珊·桑塔格曾說過:“前現(xiàn)代的旅行文學(xué)……以旅行者的口吻講述的故事一定會(huì)為文明社會(huì)辯護(hù)”。但《格列佛游記》卻是個(gè)例外。格列佛也曾試圖像魯濱遜那樣在異域他鄉(xiāng)顯示“文明社會(huì)”的高貴和優(yōu)越,但結(jié)果卻暴露出它的野蠻和落后。他為大英帝國(guó)(甚至人類)的炫耀和辯護(hù)非但沒有為其贏得榮耀與尊重,反而更顯示出它們的委瑣和丑陋。對(duì)于格列佛自身來(lái)說,他屢次的海外冒險(xiǎn)不是像魯濱遜那樣成為自我認(rèn)同的旅行,反而變?yōu)樽晕曳駰壍倪^程。因而,他沒有像魯濱遜那樣成為“文明”的使者和偉大的“救世主”,并最終成長(zhǎng)為合格的社會(huì)中堅(jiān),反而變成“文明世界”的異己者和批判者,并最終淪落為與獸為伍的“耶胡”。就像當(dāng)年塞萬(wàn)提斯以《堂·吉訶德》橫掃西班牙文壇的騎士小說一樣,斯威夫特通過《格列佛游記》有力地批批評(píng)了當(dāng)時(shí)旅行文學(xué)的泛濫,同時(shí)對(duì)其所承載的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以及人類中心主義等意識(shí)形態(tài)也給予了徹底的顛覆。所以有的評(píng)論者指出:《格列佛游記》是對(duì)旅行文學(xué)以及“造就了旅行文學(xué)并使之風(fēng)行一時(shí)的時(shí)代情感的一個(gè)抨擊”,是對(duì)張揚(yáng)魯濱遜式主人公的正在興起的小說的一種全面的反駁。
不惟如此,小說還將理性主義的語(yǔ)言風(fēng)格作為戲仿的對(duì)象。和笛福一樣,斯威夫特也“酷愛”列舉數(shù)字和細(xì)目表,表現(xiàn)出鮮明的“算賬”思維。比如,格列佛離開小人國(guó)時(shí)對(duì)物品的數(shù)目、航行的時(shí)間以及地點(diǎn)的方位等數(shù)據(jù)的敘述可謂精確之極,他對(duì)第二次出海時(shí)家庭情況的介紹則如“流水賬”般客觀而冷峻,透露著一股濃濃的“科學(xué)”氣息。而第三卷第三章對(duì)勒皮他島的介紹則充斥著大量的數(shù)字、圖表、符號(hào)和公式等,儼然一篇嚴(yán)謹(jǐn)、審慎的科學(xué)論文。聯(lián)系到這一節(jié)作者的諷刺意圖,這種對(duì)科學(xué)語(yǔ)言的模擬無(wú)疑收到了極大的反諷效果。另外,像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另一位文學(xué)大師拉伯雷在其《巨人傳》中一樣,斯威夫特也在這部小說中多次描寫“糞便”等污穢之物,以狂歡化的方式“肆無(wú)忌憚”地將這些被文明社會(huì)視為“骯臟”的東西置于文字的前臺(tái),直刺現(xiàn)代人的審美目光。這不啻是對(duì)人類文明與理性的又一種“挑釁”。
正如我國(guó)學(xué)者黃梅在其《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jì)的英國(guó)》中指出的,斯威夫特是作為“啟蒙的抵制者和‘現(xiàn)代精神’的敵人”而馳騁于文壇的,他的作品是對(duì)以啟蒙思想為代表的所謂“現(xiàn)代性”——包括理性主義,實(shí)驗(yàn)的和理論的科學(xué)以及由此派生出的“進(jìn)步”史觀,認(rèn)為人性本善的新看法,新富階級(jí)的行為方式等等——全面的口誅筆伐。他“敏銳地洞察了正在生成的‘現(xiàn)代文化’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愚蠢乖謬”。可見,斯威夫特是不屬于他那個(gè)時(shí)代的。在進(jìn)行啟蒙反思的今天,我們才似乎有些理解這位偉大的作家。在《格列佛游記》那輕松熱鬧的故事背后,我們仿佛感到了他的那份冷靜與沉重,在他這個(gè)小說“獨(dú)生子”帶給人們的笑聲里,我們似乎也聽到了那位“父親”孤獨(dú)地哀嘆與悲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