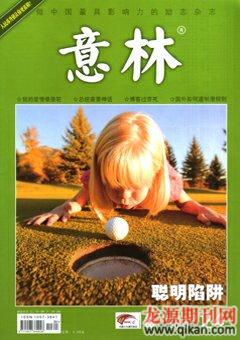產科病房
路人十六
這天,注定是不尋常的。凌晨,兒子出生了。雖然母子平安,但因為難產,需要住院治療和觀察,于是妻子住進了婦產科病房。這是一間三人病房,里面已經住了一位本地中年產婦,我們住進去以后,就還剩下一張空床。
第三天中午,護士來到病房,通知說馬上又有一名產婦要住進來,叫我們把東西整理整理。下午兩三點,醫院的護工阿姨把產婦送來了。這是一對外地農村夫婦,都是三十多歲的樣子,衣著樸素而整潔,隨身生活用品也不多。問他們哪里人,那男人說是湖北。又問生的男孩還是女孩,回答說是女孩。妻子低聲說,估計這對夫婦是“超生游擊隊”成員,現在生了個女孩,恐怕心里不痛快呢。看他們的表情,男人是茫然中有點無奈,女人是失望中顯出淡漠。絲毫沒有生兒育女的喜悅,似乎印證著妻子的猜測。
按照醫生囑咐,順產的婦女要先臥床休息1個小時,然后盡快小便一次,這是為了恢復對膀胱的控制機能。但這位農婦的舉動出人意料,她躺了不過十來分鐘,就起床上廁所,而且不需要丈夫的攙扶。妻子表示很慚愧,她因為難產,生完小孩躺了3天還坐不起來,更別說獨自行走了。
趁著農婦丈夫不在的機會,我們問那農婦這是第幾胎。農婦猶豫著,說是第二胎。又問,是不是想生個男孩啊?農婦說,是啊,家里男人就想要個男孩。農婦的話像是一種推脫,又像有些沮喪,卻絲毫沒有埋怨。打掃衛生的護工阿姨接過話頭說,看你產后這么快就能下床,只怕不止第二胎吧?農婦沒有否認,也不再多說什么。
事實上也看得出來,這對農村夫婦對剛出生的女嬰,并不疼愛。特別是當他們知道這個病房的另外兩個新生兒都是男孩時,我幾乎都能感覺到他們的自怨自艾了。晚飯時分,農婦從床上坐起來吃飯的時候,孩子正好放在身邊,農婦順手拉了下被子,把孩子從頭到腳都蓋住了。這舉動讓我和妻子面面相覷。我盡管沒有育兒經驗,但孩子睡覺時不該把臉蒙住,這是基本常識,而這農婦的舉動,看似無意,卻似有意,像在掩蓋某種令人羞恥的事物。我心里不禁生出一種悲涼。
接下來,似乎又有新的情況在醞釀。晚飯后,護工阿姨進進出出了幾次,后來還曾帶進一位陌生的本地中年婦女,她們跟那對農村夫婦低聲商量著什么。雙方的語氣冷靜且平和。妻子悄聲跟我說,估計這對夫婦不想要這女孩,想把孩子送人。我吃了一驚,但隱約聽到那位護工和那位陌生的本地婦女,都曾低聲提到“營養費”“沒有孩子”“這家人條件很好”等等。想來不是空穴來風。
第二天上午,病房里來了老老小小四五個本地婦女。妻子向我示意了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看來這對農村夫婦真的同意把孩子送人了。前來接孩子的女人們,帶了些營養品給農婦,又用帶來的被褥衣物給小孩換上。其中一個中年婦女還對那農婦說,放心好了,這家人對孩子很“寶貝”的。你看剛才給孩子買衣服奶粉就花了1000多元。農婦和她男人都沒有多說什么,沉默地坐在床邊。只是,那農村男人的目光卻始終被那孩子牽引著,而那目光,顯然只有親生父親才有。
不到半個小時,孩子被接走了。這對農村夫婦仍然沉默著,表面淡漠的神情里,似乎又多了一絲無奈。過了半晌,隔著布簾聽到點數鈔票的聲音。也許,這就是對方給的“營養費”吧。又過了一會兒,到午飯時分,他們已經在收拾衣物,看樣子是準備出院了。果然,等我吃完午飯再進病房,他們已經離開了。
人的命運真是無常,就像這孩子,注定得不到父母的歡迎。出生才一天,一個孩子和她的親生父母,從此就各分西東。
(周東平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