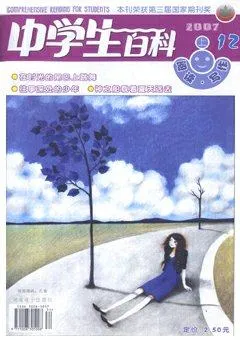指間的溫暖
對(duì)父親,我一直是心存畏懼的。父親工作忙,在家極少,偶爾回來(lái),除了問(wèn)我的學(xué)習(xí)成績(jī),就是給我上“思想教育課”。我一直以為天下的父親都是這樣不茍言笑的。直到去同學(xué)家,見(jiàn)她追趕著父親搶奪煙盒,而那身材高大的父親一邊佯作生氣地笑罵,一邊跳著腳跨過(guò)桌椅追趕。我大大地驚訝了——原來(lái)父女間的關(guān)系也可以這般融洽。
我的父親也是煙癮極大的,可我從來(lái)沒(méi)有這樣的膽量“犯上”,只要他的黑眉毛一擰,我便能從心底打個(gè)哆嗦。其實(shí)父親對(duì)我,不僅沒(méi)有打罵,呵斥也是極少的。可是我何以怕他呢?當(dāng)母親慫恿我?jiàn)Z父親的煙時(shí),我斜眼瞅瞅父親臉色,氣比膽還虛,索性找個(gè)借口,鞋底抹油算了。
13歲那年,跟隨父親到他所在的學(xué)校念書。穿得鮮艷一點(diǎn),會(huì)是花枝招展;跟男同學(xué)交往一多,有被說(shuō)成早戀的危險(xiǎn)。身為校長(zhǎng)的女兒,我仿佛受拘役的案犯,渾身拘束,不得隨意伸展,像一只無(wú)法破繭的蟲蛹。怕,有疏離的意味。內(nèi)心里巴不得父親出差或者開(kāi)會(huì)——只要看不見(jiàn)我就好。等到我上高中,父親已呈老態(tài),耳朵也開(kāi)始背了,可仍是一家之主。獅子再老也是森林之王。
對(duì)父親的牽掛,是他被查出胃病后。香煙成了全家的敵人,父親也從“雕像”的位置跌回了本真的童心。我試探著藏起香煙,但不管藏在哪里,父親總能找到,一旦找到便如獲珍寶,竊笑不已。我拿出早備好的“一滴尼古丁能毒死一匹馬”之類的健康知識(shí)作思想滲透,父親只聽(tīng)不記,眼頭眉角都是笑。這時(shí)的父親親切到可愛(ài),讓我忍不住想再遞給他一支。
為那么一些家庭啊兒女啊的大事小事,父親常常一坐就一下午,一摸身邊煙、火俱無(wú),便心生煩躁。后來(lái),終于“舊情難忘”,一支煙燃盡,父親的眉頭便平整了。于是戒了抽,抽了戒。雖然父親終究沒(méi)能把煙戒掉,但父女倆的關(guān)系,再不像以前那樣嚴(yán)肅、枯燥甚至是可怕。我想,如果沒(méi)有香煙這條惡棍,生分了十幾年的父女該如何走近呢?
大學(xué)畢業(yè)參加工作后,有一段時(shí)間,我的生活問(wèn)題叢生,身體也不堪其擾,經(jīng)常整夜地咳嗽、失眠。一天半夜醒來(lái),看見(jiàn)父親坐在客廳里,眉頭緊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他坐在那里,如一座塌陷的小山堆,那樣的疲倦、無(wú)力。女兒大了,除了擔(dān)憂,他已分擔(dān)不了什么。這是父親受不了的。
編輯/梁宇清
- 中學(xué)生百科·小文藝的其它文章
- 成長(zhǎng)的煩惱
- 直面青春的彎道
- 射手座的星語(yǔ)
- 心動(dòng)de色彩
- 果子,果子
- 盒子里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