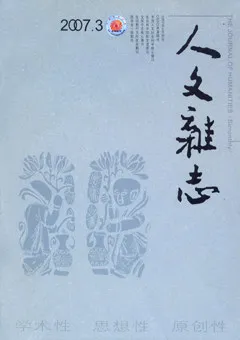文學言語的私有性
內容提要 文學言語的私有性特征是架構文學與個體生命之關聯的橋梁。論文通過在文藝學領域內對維特根斯坦關于私人語言不可能性論證的推演分析指出,個體生命在突破語言規則、習俗、慣例等束縛之后才能實現私人感覺的有效表達,即私人感覺的個人化表達。文學言語是私人感覺個人化表達的范例。這也正是文學言語私有性的實質所在。
關鍵詞 文學言語 私人語言 語言游戲 語言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I045;H0-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07)03-0105-07
文學言語的私有性是一個極易引起爭議的界定。語言是公共的,正如我國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所言,“語言好比通貨,通貨不能個人發個人的,必須是大家公認的通貨才有價值。”(注:魯樞元:《超越語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64頁。)論文論述語言的私有性并不是為了論證在公共語言之外還并行存在一個供個人使用的私人語言,這種假設本身是毫無意義的。伽達默爾認為,語言是“對話性”的。語言只要用于對話,它就必須是人所共有而非個人私有。“講話并不屬于‘我’的領域,而屬于‘我們’的領域”,“語言的精神現實就是把我和你統一起來的精神”。(注:伽達默爾:《哲學與解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第65頁。)這是語言的基本特征之一——語言的“無我性”。探討文學言語的私有性只是為了尋找一條觀照文學語言與個體生命的內在關聯的途徑,在這條路上,我們可以從生命本體論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本真存在:文學與個體生命的內在關聯,具體體現在文學言語的私有性特征之上。
一、文學言語私有性探討之原由
文學與個體生命的內在關聯,或文學中的“主體性”問題由來已久。我們從“文學是人學”這個著名的命題就可窺見一斑。早在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就在他著名的格言中提及:詩人的個人經驗是詩歌的源泉。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對想象力、情感表現以及獨創性等問題的討論也表明傳統文論對“主體性”的關注。但西方傳統文學理論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語言的修辭學研究。從這條語言途徑踏入文學的世界,我們將發現,對“真實性”的追求取代了文學的“主體性”,無論是創作主體、接收主體,還是人物的生命個體都處于一種身心分裂的狀態。僅從工具論的語言觀對文學語言進行修辭學的研究不但不能解決文學所面臨的內容與形式的割裂,也不能有效地解除文學創作主體的“語言之痛”,更沒有真正關注文學與個體生命的整體性存在的關聯。(注:詳見拙著《主體的殘缺——淺析西方傳統文論中的主體性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受現代語言學的影響,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文學的實驗(從形式主義到結構主義)似乎也沒有為文學帶來太多前進的動力,相反,科學化的研究方法與目的將文學簡化為一堆可拆卸組裝的結構與零件。現代語言學將語言從思維的載體這一工具性地位提升到意義的生產者的本體性地位,語言似乎取代了理性,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語言具有神圣的力量,成為解決哲學終極目標的有效途徑,但人的意識概念和自我中心都被從他原先的中心位置上趕了下來。文學本體論中的文學主體的消解,也遮蔽了文學與個體生命之關聯的文學“主體性”因素。在文學研究領域,文學的主體性仍被文學的真實性和文學的外在結構模式所掩蓋,個體生命存在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狀態似乎一直由于語言的局限而未能進入“澄明的存在”。
盡管如此,從語言通向文學的這扇大門似乎不應就此關閉。因為,語言并非僅是現代語言學對象化語言,是一套由習慣形成的規則與結構。語言具有生命。當我們從文學語言的修辭學研究和形式主義研究的十字路口原路返回后,我們將發現,在索緒爾為我們指引的“語言”入口對面還有一條“言語”的道路。正如杜夫海納所言,由規則和結構組成的語言只是語言構成的中間地帶,在它的下面與上面分別存在一個語言的漩渦。他命其為“次語言”和“超語言”(注:杜夫海納:《美學與哲學》,孫非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79頁。)。語言的這兩個構成部分與個體的生命活動,特別是個體生命的心靈世界與精神領域密切相關。也正是這一點啟發我們從文學語言的私有性角度揭秘文學與人、文學與個體生命之間隱秘的關聯之奧妙。如在《超越語言》一書中,魯樞元教授將文學創作動機之萌動、文學文本的產生與接受的整個文學過程理解為一種言語活動,并將文學言語的重要特性概括為“個體性、心靈性、創化性”,并從文藝心理學、語言發生學以及闡釋學等角度探討文學言語與個體生命的關聯,探討文學言語的內在性與私有性的問題。
語言的私有性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維特根斯坦在后期的語言哲學中曾花費了大量的精力來論證“私人語言”的不可能性,因為“私人語言”表達的是個體生命的私人感覺部分,屬于公共語言不可言及的黑暗王國。依照維特根斯坦的理論,我們只能對此保持沉默,以維護公共語言的可流通性。維特根斯坦反對“私人語言”的理論依據之一就是私人語言的不可交流性。但維特根斯坦在“私人語言”不可能性論證中提及的“私人感覺”的表達問題卻隱含了語言與生命的內在關聯,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使我寧愿頂著忤逆不恭的大忌,從語言的私有性角度來探索文學與個體生命的內在關聯,因為作為個體生命的組成部分,私人感覺是否應該獲得完整的表達、以及如何獲得完整的表達,關系到個體生命在世界中存在的完整性。
二、私人感覺能否表達?
維特根斯坦關于“私人語言”的論證開始于《哲學研究》243節,原文如下:
但是否也可以設想這樣一種語言:一個人能夠用這種語言寫下或說出他的內心經驗——他的感情、情緒,等等,以供他自己使用?——用我們平常的語言我們不就能這樣做嗎?——但我的意思不是這個,而是:這種語言的語詞指涉只有講話人能夠知道的東西;指涉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覺。因此另一個人無法理解這種語言。(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3頁,第243節。)
從維特根斯坦的原文中,我們至少可以概括出“私人語言”的兩個基本特征:一,私人語言指稱或表達個人的內在經驗,即私人感覺的語言;其次,由于私人感覺只有自己知道,他人無法知道,用于表達私人感覺的語言只能是私人的,無法為他人理解,不能參與交流。別人無法知道我疼或頭暈或其他什么感覺。囿于以上特征,維特根斯坦明確指出,那些可以被翻譯成公共語言的密碼語言和個人的內心獨白等語言表達方式都不屬于私人語言。按照他的語言觀,這些語言應是語言共同體中語言游戲的一種范例。
從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目的來講,反對“私人語言”,諸如“我知道我疼”等命題,是為了澄清傳統哲學面臨的、卻無法解決的形而上學問題,為了整治因對語言的誤用而導致的哲學疾病;從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念的角度上講,對“私人語言”的反對,是為了重新審視語言與心理現象之間的關系,或重新確定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可以說,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不可能性論證的哲學原因與意圖是明確的,論證邏輯是合理的,論證結果也是可信的;但如果我們跳出語言分析哲學的框架,從文學言語,或個體生命哲學的角度來看這個論證,是否能發現這個論證的不同含義呢?既然表達私人感覺的私人語言不存在,作為生命構成的一部分,私人感覺又如何實現其意義呢?維特根斯坦另辟蹊徑,他運用“生活形式”、“語言游戲”這種分析的哲學行為主義的方式,一方面調和身心二元分立,重新建立語言與心靈世界的關系,另一方面試圖在公共語言的游戲規則中實現私人感覺的有效表達,但結果卻并不令人樂觀。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私人感覺的表達并不依賴指代觀念的私人語言,而是在“人類共同的行為方式”下對外在行為達成某種一致的認同感,從而達到主體間的相互理解與交流。維特根斯坦承認心理現象的存在,即承認私人感覺的存在,并用公式的形式說明了心理現象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內在之物”,“內在之物的確就是感覺+思想+想象+心情+意圖等等”(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5頁,第959節。),它是隱蔽的,但它并不是獨立于身體的實體。“這里有一種內在之物,只能以一種不確定的方式從外在之物中推斷出來。”(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3頁,第957節。)維特根斯坦認為內在的過程一定會借助某種外在的行為標志顯現出來。通過這些外在的行為標志,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心中的內在之物。這個外在之物就是人的外在行為,包括人的面部表情、行為舉止以及話語等。“我們按照他的行為、他的話語、他的思維能力構造一幅關于他心中想些什么的圖畫。”(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6、437頁,第650節。)當這種外在行為與一定的標準、慣例相吻合時,他人便能通過對這些外在行為的觀察了解一個人的私人感覺。而對這種外在的行為標志的理解與運用就是一種語言游戲,是在語言共同體中對規則與社會習俗的遵守,而不是某個人的私人活動。如醫生向護士詢問病人的情況,護士根據病人的外在表現得出結論:“他很疼。他在呻吟。”維特根斯坦通過“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完成了私人感覺在公共語言表達中的外化,但外化后的私人感覺在多大程度上還保留著個體生命的獨特性和私密性?這取決于“生活形式”與“語言游戲”的實質所在。
生活形式的實質是什么?第一,可以肯定地說,生活形式強調的是生命存在的社會性而不是個體性。在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中,“生活形式”和“世界”、“世界圖式”、“世界觀”、“環境”具有相同的含義。“生活形式”并不是個體存在的生命活動。在《1914—1916年筆記》中,他明確指出:“生理學的生命當然不是生活,心理學的生活也不是。生活乃是世界。”(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9頁,第1節。),而“世界是所有發生的事情”,是“事實的總和,而非事物的總和”(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89頁,第31節。)。第二,心理活動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但卻需要借助語言為媒介。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中,語言對心理活動的描述的有效性在于對外在行為的認同的一致性上。在《哲學研究》中,他把期望、意向、意謂、理解、感覺等心理活動都看作生活形式,但它們是由于人們共同生活和使用語言而成為生活形式的。在心理活動與語言表達的關系上,維特根斯坦認為是因為有了語言使用的一致性,心理活動才能成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即對“理解”、“感覺”等心理現象達到對這些詞使用方法的一致性。他強調說,心智活動,如命令、期望、懷疑等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活形式的重要部分。但這些心智活動是以人使用語言的能力為條件,即心智活動必須是通過語言表達出來。而語言使用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中是以遵守語言規則為前提條件的,這就決定了生活形式的第三個特征:生活形式中缺乏個體生命的律動,即心理活動被簡化為外在行為,并受到語言規則的制約,只有這樣,無論是關于“理解”、“懷疑”等心理活動的語言游戲,還是陳述、命令的語言游戲才能進行下去。這一點在維特根斯對規則的強調中尤為明顯。
維特根斯坦在語言使用中尋找語言的意義,指出語言游戲、生活形式的多樣性會導致語言意義的多義性,將語境引入語義分析中,這是維特根斯坦后期語言哲學的成功之處。但以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以遵守規則為前提的語言游戲并不能成為私人感覺的有效表達。
原因之一:心理活動在何種程度上會外化為行動的一致性?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生活形式包括人們在特定的環境中,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各種風俗、習慣、制度等等。遵守規則對每個生命存在來說就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那種必須被接受的東西,被給予的東西,就是生活形式”。(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18頁。)從一定意以上講,強調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遵守一定的習慣、一種制度、一種社會文化并沒有錯。韓少功通過小說的形式,如《馬橋詞典》對語言現象進行思考時,更多的也是考慮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但他很快意識到在語言之外存在某種東西。他說,“在寫完《馬橋詞典》以后,我感覺到有些生活現象從語言分析的這個框架里遺漏了,或者說沒法放入這樣的框架。”(注:韓少功:《大題小作》,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74頁。)因為人的內在意識受理性與非理性兩種力量的控制。當受理性控制時,人的動機與行為之間賦有一種線性因果性或必然性;當理智控制弱化而非理性意識蔓延時,人的動機與行為之間就只有隨機性或偶然性,即行為不僅不受既定方針的暗示,人的心理也與其行動無關。(注:夏中義:《藝術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44頁。)維特根斯坦將私人感覺外化為外在行為標志的做法,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做法。謊言是一種語言游戲,因為它也是理性的。而夢是非理性的,但夢才是真正的詩人。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將人的情感、情緒等與個體生命活動有關的私人感覺置于習俗、慣例的篩子上過濾,符合公共語言游戲規則的私人感覺得到了表達并被理解,不符合的便被篩出,那我們能否懷疑,每個人的“內在之物”都是共性與個性、理性與非理性的組合,但由于語言的公共性,我們僅選擇了私人感覺中符合人類共性或理性的部分,而舍棄了個性和非理性部分呢?我們能否質疑,維特根斯坦在論證私人語言的不可能性的同時,也順帶廢除了私人感覺的個性或非理性部分以及私人感覺個人化表達的權利呢?如果是這樣,個性或非理性部分是否就應用公共語言的個人化表達來保存呢?
維特根斯坦曾用“拿一朵紅色的花來”為例子來論證對語言的理解與語言在心中引起的心理意象與內心體驗無關,因為有無內心體驗和心理意象并不影響聽者按照語言的指令完成行動,以表明對語言的理解與運用。但我們同樣可以假設有兩個聽者同時同地(我不說同一語境,因為語境往往包括聽者的內心狀況)接受“拿一朵紅色的花來”這個指令。他們都按照指令完成了任務,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理解的標準,我們可以說他們都準確地理解了這句話。那事態就這樣結束了?語言所引起的后效就這么簡單利落?設想其中一個聽者由于在幼年期親臨過車禍,“紅”對他說意味著死亡、混亂、恐怖、警車的嘯叫、人的哭泣等等一系列內在情緒或外在行為表現,他懷著所有這些內心感受完成了指令,“紅”的意義還僅僅限于他選擇了一朵紅花兒沒有拿紫色花朵嗎?在現代闡釋學的詞典中,“理解”已經不再是對于身外之物的認同,理解成了人類自身存在的一面鏡子,成了人的存在展示的過程,成了人的歷史存在的方式。在文學藝術領域中,“體驗”一詞更是突出了藝術創作中主體的存在。維特根斯坦語言理論中的這種簡化行為對他個人的理論體系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但對個體生命的存在來說卻是不公允的。海德格爾說,“現實的語言的生命在于多樣性。把生動活躍的語詞轉換成單義的機械地確定的符號條例的呆板性,這是語言的死亡和生活的凝固和萎縮。”(注:馬丁?海德格爾:《尼采》(上),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68—169頁。)尚杰在《歸隱之路》一書中也說,作者“已說的”和“要說的”不是一回事。“德里達從對福柯著作的閱讀中發現了福柯未說的,或誤說的。我把他理解為從‘顯’(作者的話語和文本)中讀出‘隱’。這樣的閱讀就不僅僅是對作者的還原和接受,而是一種創造,故稱其為‘危險的增補性’”。(注:尚杰:《歸隱之路——20世紀法國哲學的蹤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0頁。)
維特根斯坦強調對行為的描述,忽視感受;強調對語詞的使用,忽視體驗的做法并非偶然的,它源自一種分析的理性主義精神,正如意大利思想家維柯所說,理性主義的知識論是有局限性的,忽視了人的活動和創造。《西方哲學概論》,仁厚奎等編著,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40頁。維特根斯坦沒有忽略人的活動,他將語言看作人的生命活動,一種生活形式,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但他忽略了人的創造,特別是處于大腦黑箱中不為人知的創造階段。“因為我們對隱藏起來的東西毫無興趣”(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頁,第123節。),“語言的界限就意味著我們這個世界的界限”,(注: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涂紀亮主編、涂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5頁,第5.6節。)維特根斯坦在反對私人語言的同時,將個體生命納入了語言共同體中的語言游戲的網絡,被諸多的規則牽制、約束,不免使人擔心語詞的使用主體的命運將何去何從。正如張志揚在《語言空間》一書中提及,“維特根斯坦否認了‘私人語言’,……。但它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覺,或者是人的誤解,似乎語言或語言的公共性與個人無緣。”(注:張志揚:《語言空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6頁。)言下之意,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似乎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表達私人感覺,因此個體存在并不能在語言游戲的規則中獲得其意義。
三、私人感覺如何表達?
那么,私人感覺如何才能有效完整地得到表達呢?或者說作為個體存在的經驗自我如何跳出類的共性限制,獲得自身的生存權利與意義呢?
在藝術,或文學領域里,或者說在感性而非理性或科學精神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里,私人感覺似乎找到恰當的存在方式和表達形式,它就是富有創造性地文學言語活動,因為,寫作,或文學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個體生命遁入異域以逃避習慣,重新獲得生命意義的方式。這種對習慣(表現為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世界圖式”,索緒爾的語法規則與結構,福柯的“知識型構”等)的突圍體現在具體的文學語言上便是對語言規則背叛。就像杜夫海納說的,“藝術掌握在一些常常唯恐失去自主性的個人手里。個人的決定往往是在離經叛道中完成的。”(注:杜夫海納:《美學與哲學》,孫非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82頁。)
尼采認為,對于每一個人而言,除了通過寫他自己的語言和描述他自己的目標來賦予他自己的生活意義外,沒有別的選擇。這一點羅蒂表示同意。羅蒂說,“我們通過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來創造我們自己。”(注:〔美〕撒穆爾?斯通普夫等:《西方哲學史》,中華書局,2005年,第718頁)在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中,馬橋人就是通過自己的語言勾勒了自己的生活與歷史。“發歌”之王萬玉的命運正是一種個人化的書寫。“發歌”是一種民謠,更是一種語言藝術,不僅是馬橋地區婚喪嫁娶的風俗習慣,也是當地人表達愛情、宣泄情感的手段和娛樂方式,更是當地民眾的一種生存態度。它的存在是與馬橋人的生命密切相關的。當政府要求用“發歌”的形式來歌頌釘耙、鋤頭與拖拉機,宣傳毛澤東思想時,“發歌”被另一種語言規則替代,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活力,“發歌”之王萬玉也因拒絕遵守新的語言規則而被生活拒之門外,抑郁而終。《馬橋詞典》用非常規語言——文學言語的方式闡釋了作者個人對語言命題的理解。他以馬橋方言為例,說明“共同的語言”只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共同的語言”在某種意義上暗合了“權威”和“文化傳統”的意思,是集體對個人的抹殺,是常規對個性的禁錮。“我們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著某種頑強的表達。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注:韓少功:《馬橋詞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352頁。)詞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來自于它的使用者一生的悲歡離合、榮辱沉浮、生老病死,來自他們的性格與情感,來自他們對生命的體驗與對生活的態度。《馬橋詞典》是一部用語言寫語言的小說,馬橋人的語言成為小說的主題。讀者,甚至小說作者,都是通過解讀馬橋人的語言才真正認識馬橋人的。這種語言不是傳統的傳達思想的工具,也不是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共同體中的一種語言游戲,因為這種語言的意義不僅限于馬橋人用以交流、行動的規則,它還與馬橋人的歷史、生命、情感密切聯系。《馬橋詞典》是一部馬橋人的生命詞典。讀懂他們的語言,就是體會了他們的生命歷程:他們對生、死,對權威,對瘋癲,對革命的理解與接納的態度。在這個意義上,馬橋方言是馬橋人的私人感覺的個人化表達,是他們獨特的生命存在。公共語言,作為馬橋詞典的詞條注釋,不過是進入馬橋人的生命軌跡的一種嘗試。如,馬橋人用“醒”字表示愚蠢,用“夢婆”表示瘋癲的做法都違背了公共語言的使用規則,一度給外來者帶來不小的困惑。但一旦將這些詞語與馬橋人的生命歷史相聯系時,我們會為馬橋人看待這些問題的獨特眼光而驚訝,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會發現馬橋人對瘋癲的看法與福柯對瘋癲的態度有著多么驚人的相似。
個體的命運在語言共同體中總是渺小薄弱的,超出常規的言語活動卻是個體顯現自身活力的途徑。個人按照公共語言規則的表達只是常人熟知的,在海德格爾看來只是一種“沉淪式的閑談”。只有在突破語言規則的束縛之后,個人才能超越語言的界限,將原本沉默隱蔽的世界顯現出來。要想完成個體生命的自我呈現,實現個體生命完整的生存意義,個體生命的私人經驗,即私人感覺是不可或缺的存在部分。
維特根斯坦在廢除了私人語言之后,提出的“語言游戲”無法有效地表達私人感覺,個體生命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共同體”中是一種不完整的存在,個體生命間呈現一種歸閉式的隔膜。將海德格爾語言觀與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相比較,我們將發現兩者間有趣的異同點。兩者同樣都把語言作為哲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都付予語言本體論的地位,認為語言是人類的生命活動,但海德格爾強調的是此在通過語言作為個體生命的呈現和相互交融;而維特根斯坦強調的是個體帶著語言共同體的規則之鐐銬的群舞。海德格爾追根溯源,指出原語言的本質是交流、談話,事物自我呈現的方式。認為文學語言是詩的語言,是原語言的替身。文學語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語言的最初形態,能以語言的方式呈現事物的本真面目。維特根斯坦強調的“用途說”則表明對語言理解只能在使用和接受語言中遵循其規則。相比之下,個體生命在海德格爾的語言之家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共同體中卻有太多地顧忌,偶爾的任性之舉都有可能被斥為不符合規則而被逐出游戲之列,語言可能演化成一種權利,判定個體是否具有存在的意義。
生命哲學從生命本體論的角度將語言與個體的經驗、意向、直覺相聯系,認為文學語言是傳達直覺感受的最佳途徑。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中心術語。綿延是持續運動、變化的過程,是實在本身。生命沖動是綿延和運動的本質,是一切事物持續運動的創造力。理性不能把握生命沖動,而直覺可以。藝術家的創作是通過直覺來再現生命的運動。由于柏格森持傳統工具論語言觀,認為語言是概念化的,屬于理性范疇,所以語言不能表達描述深層自我,即綿延。他說,“語言是一組抽象符號的集,不能表達‘精神會診’時感受到的生命的靈魂搏動”(注:〔波蘭〕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牟斌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48頁。)。但他對文學語言卻非常重視。他說,一位詩人使用語言的方式實際上違反了語言的標準用法,其目的是把自己的直覺感受傳送給讀者。直覺感受根本不能交流,但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的作品近似地表達這種感受。當我們試圖向另外的人傳達語言自身不能表達的某種感受時,我們也擺脫不了語言的限制,但我們仍能用語言去引起各種暗示、隱喻或強烈的審美意象,以喚醒其他人的直覺能力。這種用語言表達自我或生命綿延的意圖也是生命沖動的本質,是人類獲取自由的的努力。法爾克在《維特根斯坦與詩歌》一文中也指出,在想象文學領域,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不可能性的論證局限性明顯地體現出來了:詩歌里有一種很明顯的共識,即詞并不是按照約定的規則使用。詞的意思并不取決于它的實際用途,而是取決于它的可能用途。因為除了自己親身體驗或發現,還有什么能向我們展示現實中潛在并且需要實現的可能性呢?(注:法爾克:《維特根斯坦與詩歌》,見《多維視界中的維特根斯坦》,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現象學美學家杜夫海納也認為在審美體驗和藝術創作時,個人感覺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對語言進行創造性的個人化使用是個人感覺的表達方式。在論述“審美經驗”時,杜夫海納極力謳歌感性,強調美是感性的完善。“美的對象所表現的意義,既不受邏輯的檢驗,也不受實踐的檢驗;它所需要的只是被情感感覺到存在和迫切而已。”(注:杜夫海納:《美學與哲學》,孫非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20頁。)他認為,藝術并不像語言(這里的“語言”是索緒爾關于語言/言語分類意義上的語言,即有著特定規則的符號體系。杜夫海納反對“藝術是語言”這一思想,認為藝術更像言語,是對語言規則的個性化使用。詳見杜夫海納著《美學與哲學》?《藝術與語言》。),可以有一個統一的規則,它更像話語,是對規則的一種個人化的創新。
在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論證中,私人語言存在的確困難重重:一、哲學論證認為私人語言把字詞的意思與感覺經驗聯系起來,而感覺經驗卻因人而異,由于對感覺的記憶與判斷的不確定,表達感覺的字詞的意思就缺乏統一的標準。因而無法理解。但這種語義的不確定性很可能正是文學語言所必需的空白,意義的不在場使得個體生命之內涵的自由填充成為可能。二、由于私人語言是對心理現象的描述,而心理世界并不是如外在物質世界一樣,是獨立存在的實體,故用于描述心理現象的語言只會混淆哲學概念。但在文學作品中,從傳統的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與分析,到現代小說中人物的內心獨白以及意識之流的再現不是呈現人物生命活動的有效手段嗎?三、私人語言包含這樣的觀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經驗,每個人對事物的感覺有特殊性,字詞的意思是由說話人賦予的,這會造成對語言理解的不可能性。但在文學創作中不是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嗎?字詞的使用者必要時肯定賦予了字詞特殊的內涵,從而形成語言的隱喻性、象征性和歧異性。四、哲學論證認為私人語言是指稱內在的感覺經驗,但每個人的特殊的感覺經驗是不可知的,即我心如何知他心的困難。但從生命本體論的角度來看,文學不正是通過對自我生命的呈現,使此在達到“在世界中存在”的完美境界嗎?由此看來,文學,作為一種生命活動,是個體存在的經驗自我跳出類的共性限制,獲得自身的生存權利與意義的方式。我們只能期待文學言語為我們打開通向個體生命之流的大門,這也正是我們談到文學言語私有性的目的所在。
四、結論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心靈世界是語言之外的世界,對此,我們只能保持沉默;用于描述心靈世界內的私人感覺的語言是私人語言,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的。但在文藝學領域內觀照維特根斯坦的這一論證卻有可能揭示出文學言語私有性的實質所在:個體生命得以沖破類的局限,獲得本真存在的一種方式,即個體生命的私人感覺之外化,具體表現為個體生命私人感覺的個人化表達。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