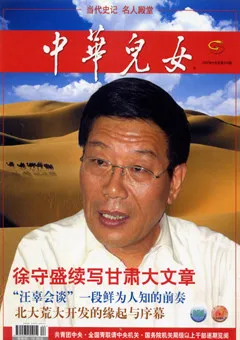博士后劉永明與敦煌學約會

24年前,他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13年前,他進入蘭州大學攻讀歷史系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從此與敦煌學結緣……
雖然已過不惑之年,但41歲的劉永明在敦煌學研究者的群體里還很年輕。然而,就是年輕、富有活力的劉永明,已經與敦煌這個神秘之地、和敦煌學這門相對冷僻的學科,結下了長達10余年的不解之緣。
2007年1月3日,劉永明的博士后論文《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世俗化研究》順利通過了由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的評議委員會的評議,他也成為我國首位出站的敦煌學博士后。
熱愛歷史,結緣敦煌學
劉永明出身于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的一個農民家庭,這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劉姓卻是當地難得的書香門第,所以,家族中有一種久遠的文化傳承。劉永明從小在爺爺的歷史故事熏陶下長大,高考時,他毫不猶豫地填報了蘭州大學歷史系,從此得以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并與敦煌學結緣。
劉永明大學畢業時,敦煌學被重新重視起來還時間不久。地處大西北,蘭州大學在敦煌學研究方面可謂近水樓臺,所以在全國率先成立了敦煌學研究機構,形成了正規的敦煌學研究氛圍,也匯集了一些卓有成績的敦煌學研究學者。留校從事圖書資料工作的劉永明終日與古籍相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文獻功底,并在與師長的溝通影響下,對敦煌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94年,劉永明在齊陳駿先生和樓勁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攻讀歷史系歷史文獻學(敦煌學)碩士學位。“是碩士研究生階段使我進入了研究之門。”時至今日,劉永明仍舊感激這段歲月,感激自己的導師。
2003年,從南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劉永明難舍鄉土之情,回到母校工作,恰逢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敦煌學)博士后流動站成立,劉永明正式歸隊,成為第一位獲準進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員。
人一輩子,總要選擇一項畢生的事業。因為熱愛,劉永明選擇了敦煌學,而現在又成為率先進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員,從而促使自己在學業上的長足發展,劉永明深深地感到:“結緣敦煌學是我的幸運。”
甘坐冷板凳,愿啃硬骨頭
敦煌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古代希臘和波斯(現阿拉伯地區)文化的交匯地。“敦煌”一詞,通常解釋為“大而盛”,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中進一步解釋道:“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

上個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藏經洞中發現的敦煌遺書包容了儒、佛、道、摩尼、祆教等多種宗教文獻,也保留了多種文字,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寶藏,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但是,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絕大部分被列強劫奪而去,散落世界各地。現在資料雖然大多公布,但由于散亂、殘缺、損壞、真偽混雜,以及年代久遠等原因,資料的整理辨析十分不易。敦煌學研究之艱辛,可想而知。
在敦煌文獻中,道教文獻的數量僅次于佛教文獻,所以敦煌道教的研究是敦煌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博士后階段,劉永明以敦煌道教這一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為主攻方向,一方面考察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曲折發展,一方面深入探討道教向民間宗教、社會生活、民俗文化以及佛教等方面的滲透,將道教的世俗化問題落到實處。在研究中,劉永明在學界關于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出了一批敦煌道教文獻以及與道教密切相關的文獻,為敦煌道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同時將道教放到了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研究。
敦煌道教文獻由于出自佛教藏經洞等局限性,反映本地區道教歷史的資料缺乏而且矛盾重重。但劉永明心甘情愿地去啃這塊硬骨頭,因為他認定,作研究就應該去選擇有難度又有意義的課題。
正是這樣,劉永明從敦煌的故紙堆中一點一點尋找道教存在的蛛絲馬跡,再根據自己的考察、分析,判斷出最終的結論。有一件事情劉永明記憶猶新,神泉觀是敦煌史料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處道觀名,但是文獻記載的神泉觀詳細位置居然有三處:分別位于沙洲敦煌縣城的不同方向,而且描述都十分詳細。“神泉觀到底在哪里?”對此,學界未作深究。但劉永明一定要找出一個答案來。通過一段時間埋頭研究《道藏》,劉永明終于從行文格式中觀察出道觀地理位置描述有誤差的原因:根據教義規定,道士描述自己身份的時候,姓名前的地名為該道士的籍貫,而道觀名被夾在籍貫與姓名中間,意為強調,與道觀實際地址無關。由此他不但解決了敦煌道觀地址方面的一些問題,而且進一步認識到了道教的發展變化和道教教義方面的一些矛盾,對道教的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實際上,每一次選擇,劉永明都會給自己一個挑戰,以挑戰促動新的進步。他認為,人原本是有惰性的,應該想辦法克服它。
2000年,劉永明到南京大學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出人意料的是,他沒有繼續自己原來的研究方向,而是選擇了道教醫學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道教醫學需要將“道教”和“中醫學”跨學科交匯到一起,研究難度很大。劉永明這樣解釋他的選擇,“如果我繼續敦煌道教研究,成績得來更加容易,卻失去了當初選擇到南京大學讀博士的初衷。我的意圖就是要在新的環境中需求新的收獲。所以,我強迫自己在博士期間進行全新的研究,我沒有太多的功利心,只希望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2003年,劉永明最終以《道教煉養學的醫學理論創造——腦學說和身神系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事后,劉永明回想起來認為,如果沒有當時的機會和勇氣,這篇論文就不可能產生。
《道教煉養學的醫學理論創造——腦學說與身神系統》的出籠,不僅讓劉永明順利獲得博士學位,而且拓展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道教醫學的研究還讓劉永明體會到:“中國人應該懂些中醫知識。”醫學書看多了,劉永明已粗通醫理。現在他能從大夫開出來的方子里判斷出治療思路,家人有個頭疼腦熱,他也能自己開出方子,他笑稱父親吃他的方子最靈了。
劉永明現在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副教授,他常教導學生,做學問必須不怕艱深,學術研究課題應該選擇難度大的做;只有深入其中,才能發現被忽視的內容,做出新意來,“只要下功夫做事,時間長了一定會有收獲。”
“學問需板凳甘坐十年冷,敦煌學研究面對如此繁復的歷史資料,更要格外吃苦。”劉永明說敦煌學研究其實比人們想象中的還要枯燥、艱苦。記不清多少個夜晚孤燈相伴;記不得多少個假日于敦煌遺書、敦煌道藏對面而坐;記不清多少次苦心拼湊殘片,使研究得以繼續;在敦煌的實地考察,也遠非旅游觀光那般悠閑自得,“但是,作為敦煌學研究者,就是窮盡畢生精力,也要還敦煌文化以真實面貌,這是敦煌研究者的責任和義務。”十幾年的研究生涯,劉永明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在敦煌道教這個較為冷僻的領域里艱難跋涉,又樂在其中。他說,做學問最痛苦是在鉆進去的階段,過了那個階段會眼前一亮。好比陶淵明《桃花源記》里所說:“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為敦煌的明天而堅守
“敦煌學者,今日國際學術之新潮流也。”學者陳寅恪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敦煌學的評價,時至今日也不為過。“敦煌所藏的資料多是唐五代以前的書卷,內容豐富,而且作者多為普通人。閱讀這些書卷,就像直接傾聽古人的聲音。這是經過文人雅士加工過的傳世文獻中所沒有的。這也是敦煌文獻的獨特價值所在。”
從道士王圓箓打開敦煌以來,到現在已是百年之久,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內憂外患不絕,竟然連自己的珍貴文化遺產無力保護。所以,才有當時陳寅恪先生的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時至20世紀80年代,還出現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雖然這段話的真實性已遭質疑,但劉永明坦言這還是給中國研究者很大壓力,“很多外國人已經把敦煌的珍貴作品原件掠走P8bhrsdrM59l3ufi7se69GctGMLzr3G/1V19k/U6cNw=,今天我們自己要研究只能屈辱地買微縮膠卷,那么,現在掌握在我們手中的真跡,就不能再從我們這一代手中滑落。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必須保衛它。”令人欣慰的是,改革開放以后,敦煌學越來越受到國家和學者的重視,經過20年的研究,中國的敦煌學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落后,并日益走向領先地位。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之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要研究基地,唯一的敦煌學博士點、博士后流動站,便是這一學術發展的標志。
作為“新生代”敦煌學研究者,劉永明和他的同事們站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致力于進一步將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推向前進。“敦煌學研究一方面是對敦煌學的研究,一方面也是對中國整個傳統文化的研究,它超越了單純的學科范疇。新時期的敦煌學研究,應該納入到中國文化的大體系中去。”
劉永明認為,在敦煌學界,他還是一名新兵。在這一領域,有很多大師和名家曾經開拓過,現在還有不少優秀的專家學者在潛心研究。雖然目前我國敦煌學研究還存在著科研經費緊張等問題,對敦煌的研究和保護也亟待更多的幫助和支持,但是,劉永明同其他的研究者一樣,克服各種困難,將一個個舉世矚目的成果擺在世人面前。劉永明說,這是他們在與敦煌對話,也是對祖國的文明膜拜。和敦煌學的先輩、同行一樣,劉永明也早已將敦煌學深深融進了自己的血液,他為敦煌的輝煌而高興,也為敦煌的未來發展而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