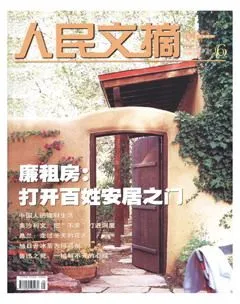一名醫生的九年坎坷打假路
說了實話,卻丟掉了飯碗
陳曉蘭15歲下鄉做過“赤腳醫生”,1976年回上海。從工人、廠醫一直做到地段醫院的醫生,本著“尊重生命”的原則,她始終兢兢業業,也頗有人緣。然而1997年發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她平靜的生活。
1997年7月24日,陳曉蘭的一個病人說醫院新進了一種“激光針”,很多病人打過都有發抖的現象,問她這種治療好不好。陳曉蘭去了注射室才知道,這種“光量子透射治療儀”是病人在輸液前,瓶中的液體先充氧后流經治療儀,經光照后再輸入病人體內。院方稱之為激光照射。照一次40元,醫生可以拿7元的提成,總營業額占到了醫院的60%以上。
無意中,陳曉蘭見機身上印著3個醒目的字母:“ZWG”,“這不是紫外線的縮寫嗎?紫外線跟激光怎么會是一碼事呢?”陳曉蘭納悶了。
她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其他醫生。結果,在不久后的醫院全體職工大會上,院長宣布:禁止任何人說“光量子治療儀”使用的不是激光,并且說“你是什么人,人家研究者上海醫科大學的陸應石教授還不如你嗎?”
陳曉蘭一下子在醫院“出名”了,但紫外線是紫外線,激光是激光,稍微有些物理常識的人都知道啊?醫生不能騙人啊?較真的陳曉蘭為了弄清真相,兩次前往上醫大人事處找那位“陸應石教授”,得到的答復讓她震驚:查無此人!
陳曉蘭決定向上舉報。
然而不久后,陳曉蘭就被院方通知“全脫產自學”。朋友勸她算了,現在醫療器械的混亂現狀就是如此,個人的力量能改變什么呢?同時,陳曉蘭連續遭到相關醫療單位的非難,各種各樣讓她覺得不可理喻的事情一次次地發生:辦公室莫名其妙被砸,家庭書信、書籍等物品被竊……但一個醫生的良知使陳曉蘭全然不管,仍然堅持舉報。
經過她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98年6月,上海市藥監局責令醫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療。同年11月,醫院報復性地讓她自動離職。同事們也不復往日的和善,有的抱怨她影響了醫院和大家的收入,有的說她“吃里扒外”,甚至有人預謀要打殘她,再把她送到精神病醫院去……
那些惡狠狠的話,陳曉蘭不是不在意,但她認為自己是對的,至少對得起良心。
一個人的戰爭有多孤單
陳曉蘭以為,“光量子”停用了,一切也就結束了。她本身并不是一個喜歡管閑事的人,只是基于一個醫生的職責才管上了“光量子”的事。然而,讓她沒有想到的是,一切只是剛剛開始。
不久,她聽說停止使用“光量子”的只有她所在的這家醫院,其他醫院依然我行我素。這個對別人來說也許毫無意義的消息,對陳曉蘭來說,卻像敲響的戰鼓,催促著她又一次奔走查證,到藥監局反映。結果工作人員告訴她,其他醫院沒有接到舉報,沒辦法管。陳曉蘭回去想了三天,決定親自扮患者,讓自己成為“受害者”。
在這個特殊患者的努力下,1999年4月15日,在上海橫行三年的“光量子”終于被取締了。
2001年2月,經上海市信訪辦協調,將陳曉蘭調往另一家醫院任理療科醫生,并對她的行為給予了肯定。
然而好景不長,2001年10月,陳曉蘭發現自己新到的這家醫院在為患者提供一種“新奇療法”——“鼻激光”。“怎么和原單位使用的‘激光照射’如出一轍?”陳曉蘭的良心又開始按捺不住了……
經她反映,藥品監管部門這次很快取締了“鼻激光”。然而,2002年12月31日,50歲的陳曉蘭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編制”退休,更讓她寒心的是,她的醫保竟也被“強制封存”,成為醫療界惟一沒有醫保的醫生。
這條打假之路太難走了,一路上的坎坷和險阻顯而易見,但陳曉蘭越是走在醫療器械打假的道路上,越是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醫療器械的現狀是多么的混亂和無奈。“患者的利益根本無法保障,患者不懂,但醫生該懂哇。如果懂的醫生都不出頭,那患者要依靠誰?中國醫生的信譽還有誰來保障?”
漫漫打假路,一次次化裝取證,一次次奔波在各個部門,一次次以身試器械,鍛煉得陳曉蘭成了一個全能戰士,那就是要想揭發這些事情,舉報這些事情,必須要有運動員的身體,偵察員的機智,博士的知識,還要有一個持之以恒的決心。
9年的時間,陳曉蘭獨自一人扳倒了8種假醫療器械。
夢想一個良好的醫療環境
陳曉蘭現住在閘北的某小區里。
隨時進門都會看到書房里、客廳的地上,到處雜亂堆放著大包小包的各類藥品和一疊疊各種材料。藥都是她自費購買的“證據”,材料也是多年整理的結果。書房里則放著各種專業書籍,電腦、掃描儀、傳真機一應俱全。
陳曉蘭4年前搬到現在住的地方,2室1廳的房子,現在只住著她一個人。客廳墻角的涂料已經有些斑駁了,她說沒精力顧這些事。自從女兒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已漸漸習慣這樣一個人的簡單生活。每天不是整理準備材料,就是聯系知情人了解情況,跟朋友討論,心事重重的她晚上經常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就在前不久的一天,她想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忽然感到全身無力,心跳加速,人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我的心臟病已經30多年沒犯了,也許是最近實在太累了!經歷了這次心臟病,我已經在家里備好了‘強心針。’”說到這,陳曉蘭又無奈地笑了。
犯心臟病時,陳曉蘭惟一想的就是女兒,因為除了女兒,她已經沒有別的親人了。
陳曉蘭1981年正式和丈夫離婚,那時女兒才3歲。對女兒,她有著說不盡的愧疚。女兒小的時候她一直忙著自學和工作,等女兒長大了,她又瞞著女兒踏上漫漫打假之路。直到去年女兒從報紙上讀到媽媽為了取證“以身試針”的事,才知道母親多年來的艱辛,當時在公共汽車上就不顧一切地放聲大哭。女兒回家摟著她說:“媽媽,你是我最親的人,我不能失去你啊!”
人總有脆弱的時候。因為一直忙于醫療器械打假,她沒有時間照顧好父母親。母親和父親的相繼去世給了陳曉蘭沉重的打擊。從此生死兩茫茫,她感覺自己忽然像變成了孤兒一樣。那一刻,她真的對自己的打假之路生出一絲悔意來。
母親是研究化學的,生前對陳曉蘭的醫療器械打假有著巨大的幫助。陳曉蘭常說,在失意時,就到母親的墓前,或哭泣或默立,母親臨終前的叮囑總是給她無窮的力量:“病人不懂,你作為醫生,你懂,任何時候都要保護病人的利益。媽媽會一直支持你!”
“我希望在死后下葬時能穿上一身白大褂。因為女兒說,媽媽穿上它時最像醫生!”對陳曉蘭來說,醫生始終是她最崇敬和熱愛的職業,“我沒有多少財產能留給后代,作為醫生,我只希望下一代能有一個好的醫療環境。”
(秦 淑摘自《東南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