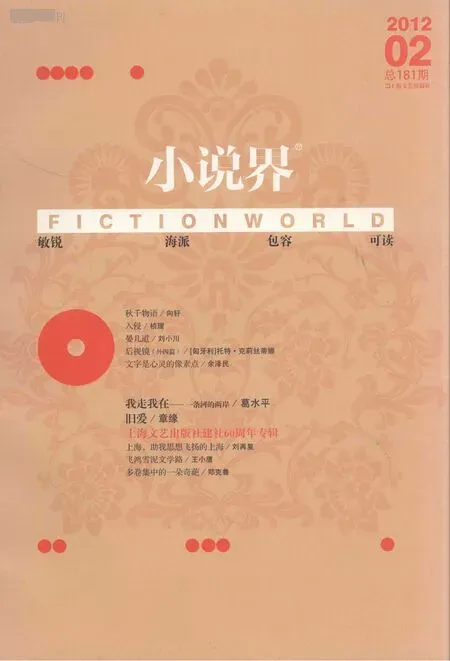列車時刻表
[丹麥]海勒·海勒 余澤民 譯
他是一個已婚男人。整個晚上,只有他還沒有跟我搭過話。夜里十一點左右,喜慶的氣氛到達了頂峰,他邀我出去散一散步。他告訴我說,他已經(jīng)觀察了我?guī)讉€小時,完全被我吸引住了,并說我笑的時候總聳鼻子。
我們一起到海濱散步,彼此之間保持幾米的距離。我用手抓著自己的衣領:天氣很冷,我的大衣下面只穿了一件混紡襯衣。
他跟妻子出國生活了四年,不久前才從加拿大回來。作為生物學家,他參加了一個調查雞禽疫感染的研究小組,與此同時,他的妻子撰寫畢業(yè)論文,現(xiàn)在忙著應聘工作。他們從學生時代就彼此認識,婚后生活十分和諧。
他說,他不常跟陌生女人在夜里散步,他建議我們走到沙灘。我牽他手時他沒有拒絕,我覺得很冷,頭發(fā)粘在潮濕的礁石上。隨后,我們坐著望著大海發(fā)呆。我掏出香煙遞給他,但他不抽。他撣了撣衣角上的沙子,并且磕了磕鞋幫。
“這本來根本不可能發(fā)生,”他自言自語道,“我不知道回頭該怎么對她說。”
我將煙卷放在礁石上。我望著他,但是只能看到他面孔的輪廓。
“也許她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我們兩個不見了,”他繼續(xù)說,“也許已經(jīng)出來找我們。”
他站了起來,環(huán)顧四周:海灘上除了我倆,再見不到一個生靈。
“我想,我該送你去火車站,”他說,“我知道這顯得冷酷無情,但我沒有其它選擇。”
“最后一班列車肯定已經(jīng)走了,”我回答說,“另外,我根本沒有回家的情緒。”
“這關系到我們的婚姻,”他繼續(xù)說,“回頭我可以跟她解釋,你要我送你去趕火車,對這樣的請求我不好回絕。”
他扶我從礁石上站起來,我則彎腰去拾香煙。我們回到別墅。他的車停在稍遠的路邊,他拉開車門催我上車。
“我要進屋取我的皮包。”我說。
他問我是不是必須要取。
“鑰匙和錢包都在里面,”我回答說,“否則我回不了家。”
他催我快點,并且說:要是他妻子看見了我,就說我感到身體不適。
“你就說,整個晚上都在嘔吐,暈得一步也挪不動。”他叮囑我說。
“但我剛還跳舞了呢。”
“那無所謂,你就這么說。”
從客廳里傳來喧囂的音樂,一些人鼓著掌,一些人大聲歌唱。他的妻子端著一盤炸薯片從廚房里出來。我伸手抓了一把,隨后到門后找我的皮包。我還找到半瓶被誰放在地板上的白葡萄酒。我拎著酒瓶回到車邊,馬達已經(jīng)啟動了。
“拿著,”我說,“喝一口吧!”
但是現(xiàn)在他沒心思喝酒。他開動汽車,直到上了主路,才打開車燈。
“遇到我妻子了嗎?”他問。
“見到了,而且還從她手里抓了幾個炸薯片。”
“她有沒有說什么?”
“沒有。”
“你能肯定是她?”
“當然了,她穿的是綠衣服,對不對?”
“對。她是長發(fā),有些卷,但是自然的卷發(fā),不是燙的。”
“哦。”
“她跟你什么都沒說?”
“沒有。”
“她看上去怎么樣?”
“情緒不錯。”
“怎么不錯?”
“看上去微笑。”
“她到底笑還是沒笑?”
“我說了,她面帶微笑。”
“可能她什么也沒有察覺。”
“肯定沒有。”
“那就好。”
他提高車速,下了主路。我記得,橫穿樹林有一條直達火車站的近路,只有幾公里,來回也用不了十分鐘,有足夠的時間趕上末班列車。他打開收音機。我將酒瓶舉到嘴邊,呷了一口溫熱的葡萄酒。
“別喝了好不好?”他問。
“為什么?”
“至少用個一次性杯子,在你前面的車匣里就有。”
我取出一只塑料杯,照相機從里面掉了出來。
“把它放回去。”他吩咐說。
在林間公路上我們撞死了一只動物。汽車咯噔一下停了下來,我們從車里出來,看到一只狐貍躺在路上,嘴里流血。他彎下腰,伸手去摸狐貍的皮毛。狐貍扭頭沖他低吼了一聲,他嚇得迅速將手縮回。
“該死的。”他咬牙罵道。
“咬到你了?”我問。我正好站在他的身后。
“沒有,但真倒霉!”
狐貍的嘴里咕嚕了一聲。
“它一定很痛苦,”我判斷說,“我們應該把它砸死。”
“你說的對,”他應道,之后鉆進了樹林里。過了一會兒,他拎著一塊石頭回來了,然后瞄準狐貍的喉嚨。
“快砸啊!”我催促說。
“我覺得這塊石頭還不夠大,”他回道說,“我覺得肯定砸不死它。”
“那你再去找塊大的。”
“我覺得我可能下不了手。”
“你不是生物學家嗎?”
“是啊,”他回答說,“但跟這是兩回事。”
我提議說,我們坐回到汽車內,然后開車軋死它。他不同意,并且將石頭扔到地上。
“我覺得,五分鐘之內它自己會死。”他說。
他鉆進汽車。我也跟著他鉆進去,喝了口白葡萄酒。
火車一個小時前就開走了。但他仍不死心地盯著貼在站臺墻上的列車時刻表。他朝候車室門口走去,但是大門鎖著。我坐在火車站的臺階上,點燃一支煙。
“最后一班火車已經(jīng)走了。”他告訴我。
“是的。”
“既然這樣,我們也沒有其它辦法。”
“沒有。”
我們重新坐進汽車里,他要把煙捻掉。我將煙卷扔出窗外,隨后系好了安全帶。
“我猜想,如果讓你留在這兒等早班車,不太可能對不對?”
“對,”我回答說,“那不可能。”
“當然了,”他聳了聳肩,“這能理解。”
他啟動汽車,退出車站。開到出城的公路上,他下意識地看了下表,時間又過了二十分鐘,現(xiàn)在回去顯然更遲。
“該死的火車,”他嘟囔說,“怎么會弄得這么麻煩。”
他重重地捶了一下方向盤。
“還有那只該死的狐貍。”
我建議說:“還是抄林中的近道吧。”
狐貍蜷縮在公路中央,路面上的血跡已經(jīng)變黑。
“我估計,它早就死了。”我說。
“這么長時間它也該死了。”
“至少我們把它扔到林子里。”我建議說。
他小心翼翼地踢了一腳。狐貍居然咕嚕了一聲,我們驚得倒退了一步。
“你也可以試一試。”他說。
“它又不是我撞的。”
“是它跑到我車前的,該死的,是它自己闖的禍。”他回答說。
“那就把它扔在這兒吧。”我建議說。
我們一聲不語地鉆進車里坐了會兒。他搖下車窗,朝地上的狐貍望了一眼。
“我還是狠不下心來,不能做與我的職業(yè)相反的事,不能將它這樣痛苦地丟在這兒。”
“我也跟你想的一樣。”
他轉過臉望著我。
“要不這樣吧,”他想了想說,“我把你送回別墅去,然后去找一支獵槍、一把鎬頭或鐵鍬,回頭再來收拾它。”
“這個主意不錯。”我表示贊同。
“真的嗎?”
“是啊。”
“這樣最好。”他一邊說著一邊啟動了汽車。
他將汽車停在坡下的路邊,他讓我先下車,自己鉆進了車庫,尋找什么能用的家伙。他將手搭在我的肩上。
“或許,你該馬上躺下休息一會兒。”
“好吧。”我答應道。他則用力撞上了車門。
前院里,客人們正圍成圓圈一起跳舞。我走進房間,在廚房里吃了幾片炸薯片,并朝一只酒杯里斟滿了酒。我將酒在嘴里含了好一會兒,咽下之前,漱了左腮又漱右腮。走到前廳,我從皮包下找到電話,叫了輛出租車送我回家。
我在路邊等車的時候,點了支煙。其他人還在花園里跳舞,灌木叢后,可以看到胳膊和酒杯。有人注意到我,跟我打招呼。
“來啊!”他們沖我大喊,繼續(xù)跳舞。
“我馬上就來。”我敷衍回答,并捻滅了煙頭。這時,出租車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路口。
出租車司機選擇了近路,橫穿樹林。借著出租車的燈光,我從很遠就看到了他。坐在一個樹墩上,手里拎著一把鎬頭,狐貍躺在他的腳旁。他的車停在兩棵樹之間,他并沒有注意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