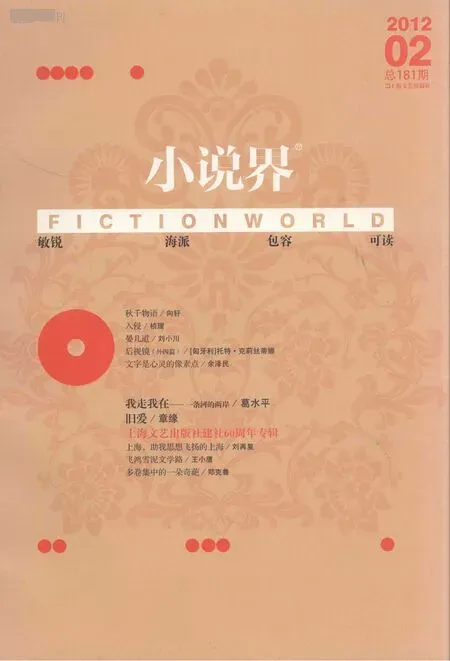伴你同行
達 理
1
剛從高架橋駛進入口,托尼就看到101高速公路上那塞得密不透風,仿佛凝固了的龐大車陣。其蠕動之慢, 常令托尼想到地球上大陸板塊的漂移。其實,何需去想。每逢早晚交通尖峰時段,這條通往硅谷的交通要道,永遠是無可救藥的擁堵。于是舊金山灣區KPIS交通臺的播音員,描繪此情此景,多年一成不變的用語總是:“保險杠頂著保險杠,像個巨大的停車場。”
然而百密一疏,同向四條車道的左邊的一線卻暢通無阻。那是Car pool——美國交通管理部門為了鼓勵共乘,在尖峰時段開出的一條專用線,只限兩人以上的共乘車輛行駛,違規者重罰237美元。托尼在電視上看過一則報道,一個老美自作聰明地從成人商店買來一具可供發泄用的橡皮妞兒,放在副駕駛座上,駛入了Car pool。被交警發現后,不僅吃了罰單,還以欺詐罪被送上了法庭。
托尼瞥了一眼空空蕩蕩,車速如飛的Car pool ,心中百感交集。僅僅一個月前,在長達一年的日子里,他也是這種特權的享有者。每日上班下班,都有一名共乘者與他結伴同行。這個伴兒可不是什么橡皮人,而是一個會說、會笑、活色生香的女孩兒。由于她的相伴,托尼得以在緩慢爬行的車陣旁享受馳騁的快感。看著旁邊蝸行車中投來的嫉妒的目光,托尼認定自己就是那威風八面一飛沖天的王子,身邊的女孩,就是給他帶來好運的公主。
如今,他的伴兒已經遠走高飛,消失得無影無蹤,他也從天上跌到了地下,跌到了這令人窒息的車陣中,忍受著無休無止的困擾與煎熬。
僅僅十幾英里的路程,正常情況下,只需十分鐘,他卻整整開了半個多小時,還好沒有遲到。當他跨入公司大樓時,前臺小姐剛剛就坐,畢恭畢敬地向他道早安。他無言地點點頭,繞過大堂,邁入一條長長的通道,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
通道左側,是行政與開發部門,右側是他主管的銷售部門。半人多高的灰藍色屏風,分割出幾十間辦公室。推銷員們各據一間,俯首案頭,電話鈴聲此伏彼起。討價還價,厲聲軟語不絕于耳。每次經過這里,托尼都覺得這里是一座巨大的整日轟鳴的蜂巢。每只工蜂蜷縮在自己的孔洞里,榨干精血,耗盡生命,醞出甘美的蜂蜜,奉養著至高無上的蜂王。
托尼的辦公室可不是孔洞。雖然不大,卻有寫字臺,會客用的小沙發,以及排滿一面墻的檔案柜和書架。另一面墻上掛著一幅大尺寸的世界地圖。金幣似的小圓塑膠片星羅棋布,代表著公司觸角所及之處。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擁有一扇窗戶,旋開乳白色的鋁片百葉窗,他可以飽享北加州常年燦爛的陽光,眺望環繞著停車場的成排的橡樹和大片的草坪。這兒是硅谷的中心,圣塔克拉拉市,圣托馬斯與勞倫斯快速路之間的黃金地帶,一片花團錦簇,草木如茵的科技園區。
他在窗邊坐下,目光留戀地向外眺望。
正是這扇窗,從上班的第一天起就令他驚喜,令他著迷;也令那些蜷縮在不見天日的蜂巢里的下屬欽羨不已。然而,也正是這扇窗,為他洞開了另一種生活,使他決心結束眼前的一切。
他抓起電話,接通總裁秘書小姐莫尼卡,請她查一查,今天總裁的日程里,是否安排了同他的談話。
“沒有,先生。”莫尼卡幾乎不假思索,直截了當地否認道,“還有別的事嗎?”
為了阻止對方放下話筒,托尼突然加重了語氣:“莫尼卡,請立即轉告總裁,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他報告。準備發往天津的兩集裝箱‘奔騰電腦散件,對方提出將近期信用證改為遠期,否則取消合同。合同編號9742。成交額四百六十萬美元。記下了嗎,莫尼卡?”“是的,先生。我立即轉告總裁。”
放下話筒,托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作為公司的銷售主管,要約見總裁,過去是多么輕而易舉。只要先打一個電話過去,或是徑直走到門口. 若莫尼卡說里面沒有客人,他便可以長驅直入。 要知道,這位總裁喬治,是他妻子的叔叔,他的叔丈人。憑著這一層關系,秘書小姐自然十分知趣,從不擋他的駕。但是,一個月前,當他與妻子琳娜鬧離婚,并向喬治遞上辭職報告以后,情況立即急轉直下。莫尼卡轉達了喬治的指示: 以后托尼要見總裁, 必須先陳明會見內容,并由秘書做出安排。盡管莫尼卡對他的態度仍然十分得體、有禮,但十有八九擋了他的駕,讓他嘗盡了熱面孔、冷板凳的滋味兒。
不到五分鐘,莫尼卡來電話,請他立即去見喬治。并賣乖地說,總裁為了擠出這次會見的時間,特地推遲了今天早晨的工作例會。
“謝謝你,莫尼卡。”
托尼料到會是這樣的。事關四百多萬的大生意,別說推遲什么工作例會,就是推遲他老爸的葬禮,也在所不惜。
喬治那間富麗堂皇、酒店大廳一樣寬敞的辦公室里,散發著咖啡的誘人香味,圍成一圈的意大利皮沙發上,散放著手工精制的絨繡靠墊。咖啡桌厚厚的玻璃臺面上,擺著一籃新出爐的法式羊角面包和丹麥甜點。刻花水晶盤里是碧綠的白蘭瓜,金黃的哈密瓜和鮮紅透亮的草莓。
托尼知道,這是每周一早晨工作例會的餐點。以往,每逢例會之前,喬治都會先把托尼找來,叔丈人和侄女婿并排坐在一張長沙發上,問問周末過得如何,有些什么消遣?是去蒙特瑞打高爾夫,還是去太浩湖滑雪了?琳娜又去誰家打了麻將,手氣如何……莫尼卡這時一定笑盈盈地端上兩杯香噴噴的咖啡。她那甜甜的笑臉,映在亮閃閃的金屬咖啡壺上,變得細長而又滑稽。
今天卻不同了。托尼進門后,喬治始終沒有離開他那寬大的櫻桃木辦公桌后的高背轉椅,眼睛盯著莫尼卡剛剛替他找來的那份合同,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地回避著托尼的目光:“談談情況吧。”
托尼在辦公桌前的臨時會客椅上坐下,重復了一遍客戶提出的新要求。
“你是怎么答復的?”喬治透過金絲邊眼鏡,關切地注視著托尼。
“我知會他們,如果將信用證從短期改為長期,必須把訂金從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結算銀行由中資改為外資。”
“哦,”喬治點了點頭,“對方同意了嗎?”“起初不同意。后來我答應給有關承辦人百分之二的回扣,對方立即拍板了。”
喬治陰沉的臉上終于綻出了一絲微笑:“很好,干得不錯。其實這無須向我匯報了嘛,你自己完全可以做主的。”
托尼當然料到他會滿意的。現金進賬增加了一倍,幾乎與出貨成本相抵,何樂而不為?
“如果沒有別的事了,我讓莫尼卡通知各部門主管來開會。”喬治抓起了內線電話。
“等一等!”托尼縱身躍起,按下了電話機的叉簧,“喬治,我的辭職報告交給你,到今天已經整整一個月了,你應該給我一個答復。”
“哦?有這么快嗎?容我去查一查。”喬治一臉狐疑的模樣。
“你不用查了,我記得很清楚。”
這一個月,他是一天一天捱過來的。為了今天的見面,他特意把這件早已圓滿解決的爭執,說成事關重大的懸案,讓莫尼卡通報總裁,得以敲開喬治的大門。
“托尼,再等一等好嗎?”喬治似乎滿懷歉意,“你看到了,我現在正忙。”
“我知道。”托尼極力抑制著自己的沖動,“我絕不多占用你的時間,根據公司的規定,主管一級的雇員,辭職報告提出一個月,公司必須做出答復。同意不同意是公司的事情。我只想告訴你,今天下班以前,我已有權利離開公司。”說完,托尼轉身朝門外走去。
“托尼!”喬治終于從高背椅上站了起來,照難道你非走不可嗎?琳娜昨天晚上還跑到我那兒哭哭啼啼,求我一定想法子留住你; 她爸爸今天早上也從臺灣打來電話,表示一切都好商量。托尼,你就不能重新考慮一下嗎?”
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托尼苦笑著搖著頭。
看來,他們并沒有忘記這個“大限”的日子,喬治剛剛裝模做樣表示查一查,不過是借故推托而已。托尼實在難以理解,像他這樣一個辱沒家族門風的叛逆,他們何以能夠容忍他繼續坐在公司銷售主管的位置上呢?也許,真是器重他的才華,也許是擔心他所掌管的客戶流失,也許是一時還沒有找到替代他的人選。但托尼相信,這一個月來,他們一定絞盡腦汁,費盡思量,卻一直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
“托尼, 你知道,作為公司,一定要公私分明。”喬治繞過辦公桌,走到他面前。“你和琳娜之間的問題,是家事。再說已經過去了嘛。那個女孩兒也走了嘛!琳娜昨天對我說,她很后悔當初同你大吵大鬧,使著性子逞口舌之快。你何必賭氣計較呢?作為一個大公司,我們一向選賢任能,你完全可以放心地做下去嘛!”
對于喬治的表白,托尼半信半疑。無論怎樣標榜任人唯賢,這畢竟是個家族企業。就拿眼前的喬治來說,能長年穩坐總裁寶座,不就因為他的史姓嗎?這個史姓,猶如《紅樓夢》里的四大家族一樣,是臺灣電腦界四大骨干企業之一。每年僅從美國接到的訂單,就高達十幾億美元,更有幾倍于此的OEM(委托加工)產品返銷美國以至全世界。史氏家族的發展史,正是幾十年來臺灣出口加工產業的縮影。先是玩具,繼而皮鞋,最后是電玩、電腦。從來料加工到自創品牌。隨著產業一波波轉型,產品不斷升級換代,市場占有率逐年擴大,迅速積累起巨大的財富。有了大筆的錢,就可以網羅一流的人才,建大公司,做大生意。兩年前托尼剛來的時候,不過是一名才疏學淺的本科畢業生。之所以被授予銷售主管的頭銜,還不是因為他貴為史家的新科駙馬?最初的那些日子,他不僅受夠了公司上下對他的那種彬彬有禮的輕蔑,連他自己也感到一種尸位素餐的恥辱。幸而公司從那時開始大舉進軍大陸市場,他挾著史氏家族的雄厚財力,又調動了家鄉的各種人脈關系,逐漸建立了自己的客戶網,大幅度提高了公司的銷售額。有時,他所主管的銷售部門一天業績可達百萬,超過硅谷千百個夫妻檔小公司全年的營業水平。他深信,這也是在他雖然干出了令家族蒙羞的出軌行為,又同史家三小姐打得天翻地覆,喬治以及他的老丈人仍然竭力挽留他的原因。但他絕不戀棧。除非他肯就范,重新回到琳娜身邊。否則,遲早有一天,他們會把他一腳踢開。
“謝謝你的好意,喬治。”托尼去意已決,“我想,我還是走的好。請放心,我會履行與公司簽訂的合約,離開之后,不會做與公司利益相沖突的事情。再見!”說完,大步跨出門去。
離開總裁的那間寬大氣派,但卻令他窒息的房間,托尼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他不禁又來到窗前坐下。這是最后一天了,是留戀這個令人羨慕的座位,還是留戀這個窗口曾經給他帶來的美好時光?
2
現在,他已無法確切記得,究竟是從什么時候起,開始注意窗外那個姑娘的. 是他的目光透過窗口捕捉了她,還是她的身影穿過窗口射入了他的眼簾?他的視線,又情不自禁地投向停車場正中那座磚紅色的水磨石花壇。兩株年代久遠異常粗壯的老橡樹,伸展開密實寬大的樹冠,遮住了陽光,給花壇周圍投下大片陰涼。每逢中午十二點,對面電子廠的大門里,就會涌出一群身穿制服的女工,徑直奔到花壇的石階前坐下, 打開各自的便當,享受一頓戶外的午餐。對于終日埋首于重重公文數字的托尼,這有聲有色的畫面,猶如每天早上第一杯香濃的咖啡,或是身心交瘁地奔馳于高速公路上時, CD唱盤中忽然傳出惠特尼·休斯頓輕柔的歌聲。
漸漸的,他那漫不經心的目光竟不時停滯在一個永遠穿白襯衣的身影上,她把工作制服系在腰間,水磨石臺階上的坐姿是訓練有素的,兩條細長勻稱的小腿交叉疊在一起,腳背繃直,腳尖輕輕觸地。在嘻笑吵鬧,話語嘈雜的女工中,她只是一個忠實聽眾,不時開心地笑著,齊肩的黑發隨意扎成一束馬尾辮兒,在挺拔的頸后甩來甩去。活像個稚氣未脫的中學生。
幾乎每天中午,他都會去凝望這幅賞心悅目的畫面。漸漸的又覺得那可望不可及的遠景是一種難耐的缺憾,他渴望看到一個特寫,看到他已經凝視了無數次,但仍然無法看真切的那張面孔。
終天有一天,他走出了辦公室,推開了通向花園的大門。明知這一步跨出去有些荒唐愚蠢,但他竟無法自制。正是午餐時間,在辦公室里憋了一上午的男人女人都到戶外來享受一下溫暖的陽光。
幾位公司的小姐太太,柔聲細氣地交流著烘烤果仁蛋糕的訣竅;一群不修邊幅的工程師們坐在藤蘿架下吞云吐霧。托尼假裝去車里取東西,信步走過花壇. 女工們對他的出現并未介意,那姑娘也是毫無異樣。她一邊在聽身旁一位女伴兒說話,一邊用叉子去撥弄飯盒里的一朵綠椰菜。當他在花壇邊踟躕時,她正笑著向女伴兒仰起臉,旋即又伏在女伴兒肩頭笑個不停。
也許是那正午的陽光,也許那是迷人的笑容。一瞬間,他只覺得抬不起眼,有一群驚飛的鳥兒,撲啦啦地在他的心頭沖撞。
回到辦公室,坐在此時已變得空曠的窗前,他仍無法平息自己的慌亂。他鬼使神差般地撲到電腦跟前,抑制著抖動的手,移動鼠標,從硬盤中調出朋友送給他的最新軟件“影像世界”.這里儲存著取自世間一切俊男美女,珍禽怪獸,奇花異草,衣帽服飾的各種“零件”,可任憑主人的喜好,描繪拼湊出夢中情人或心愛之物。他想搜尋出一個如同小女工那樣的笑臉,然而終究徒勞無功。他無論如何也無法在冷冰冰、硬邦邦的熒屏上,勾畫出那清純真切,讓他怦然心動的笑臉。他不得不嘲笑自己的愚癡。屏上不過是一群無生命的電子點陣,怎么能呈現出有血有肉,鮮活生動的萬物之靈呢?
他困惑了。這是怎么了?他結了婚,有了妻子啊!他已經洞悉了女人的一切秘密,為什么現在又會為另一個姑娘魂不守舍呢?也許,這就叫一見鐘情?是的,這是他有生以來從不曾有過的感覺。在他的妻子身上也沒有感覺到。因為他與妻子并非一見鐘情,而是莫名其妙地被人撮合在一起的……
3
托尼覺得他這一生總是被人擺布。
他出生在東北長春市。父母都是籃球運動員,給他生就了一副高大挺拔的身材。長春出美男子。中央芭蕾舞團的第一個“王子”就是從長春選去的。有人說,他比那個“王子”還帥,只是沒有被星探發現,倒被遼寧體育學院選去學滑冰。按他的本意,他是想學機械的,將來去長春一汽做一名汽車工程師。從小生長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冰上功夫似乎與生俱來, 還沒有畢業就在全國冬運會上奪得亞軍。 沒當上芭蕾王子,卻成了冰上王子。九十年代中,大連市政府組團赴美國加州奧克蘭市參加締結友好城市周年慶典,特邀他隨團出訪。奧克蘭體育館的一場冰上獨舞,以及與那位日裔冰上皇后的雙人舞,令舉座震驚,歡聲雷動。黑色閃亮的緊身長褲,配上一件寬松如鳥翼的黑色上衣,他便像黑色的海燕凌空翱翔。 騰翻跳躍,俯仰旋轉,無不徐疾有致,從容不迫。尤其是結尾那段抱胸自旋,轉速之快,定點之準,令人目眩神迷。恍惚之際,以為他已化作一縷青煙,裊裊婷婷,直上云天。當他戛然而止, 以王子的跪姿躬身謝幕時,無數群花和姑娘的飛吻向他拋來,使他久久無法退場。
第二天,一個講國語的經紀人到旅館找他,向他出示一份合同書,有家機構愿出四年全額獎學金,供他上舊金山州立大學,專業任選。條件是每年他必須做兩輪專業性巡回演出。當然,平時的必要訓練,也可以完全保證。他似乎沒有理由拒絕,盡管這是又一次別人為他做的安排。
畢業前夕,他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表示愿意跟他談談工作去向問題。對方報出的公司大名,他并不陌生. 硅谷大名鼎鼎的電腦公司,臺灣炙手可熱的史氏家族在美國的分支機構。
約談晚餐訂在舊金山西海岸著名的“峭壁餐廳”。高大的玻璃幕墻之外,就是晚潮洶涌的太平洋. 遠方錨地上等候入港的遠洋巨輪,點亮了璀璨的燈火,猶如一座座水晶鑲嵌的海上城堡。
“你好,我是喬治。”對方遞上一張名片。托尼從喬治的姓氏和職務上看得出來,他是史氏家族的重要成員。
喬治為他點了酒和菜。在舊金山灣區,不點太平洋的鱈魚而點佛蒙特的龍蝦;在加州,不點納帕的葡萄酒而點法國的波爾多。這究竟是表示自己的身份,還是對客人的盛情?被清醇的波爾多浸得有些目光迷蒙的托尼真是有些說不清。
喬治一向開門見山,言簡意賅:我們決定聘用你,做一個部門主管——比如銷售,起薪八萬,外加紅利和公司的股票。另外,還為你提供一輛汽車,甚至一棟房子。當然,還有辦綠卡。
“條件呢?”托尼下意識地感到,這不會是無緣無故的。
喬治優雅地叉起一塊龍蝦肉,緩緩送進嘴里,紅潤光亮,保養極好的臉上浮起一絲神秘的微笑:“小伙子,別緊張嘛。哪里有什么條件。相反的,我們給你的會更多,更好。”
“為什么?”托尼更疑惑了,憑他一個本科畢業生,何以獲得如此厚愛?聽起來真像“芝麻開門”一類的天方夜譚。在美國,從來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是三歲孩子都懂的格言。
“也沒什么,只想順便介紹你和史家的三小姐琳娜認識認識,交個朋友罷了。”
喬治說得很得體。沒有什么。順便,罷了。
輕描淡寫,恰到好處。既不失身份,又讓對方掂得出話中的斤兩。
托尼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小伙子。不僅完全聽懂了這“順便”之中的條件,而且吃驚得幾乎扔掉了手里的高腳酒杯。哦,老天!這可不是什么每年的兩輪演出,而是將以自己的一生一世為代價。
喬治又殷勤地為他斟酒。然后,托尼邊啜酒邊聽喬治介紹那位仿佛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史家三小姐。
原來,琳娜也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就讀。從小在臺灣長大的三小姐,只在出游北歐和日本時見過兩次冰雪。在加州讀書的最后一年,偶爾隨一群“姐妹會”同學去看了一場托尼的花樣滑冰,便一發不可收。雖然在她的公寓里貼滿了李察·基爾、湯姆·克魯斯、凱文·寇斯納這樣的好萊塢帥哥的照片,并常會想入非非; 但任性的三小姐并非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傻妞兒。即使老爸能為女兒鑄一道黃金的梯子,她也無法企及那滿天星斗中的任何一顆。可望而不可及的好萊塢星空太遙遠,而冰場上這位來自大陸長春的美少年,倒是一次次微笑著走進了她的夢鄉。于是,琳娜捧著她的夢,追隨著托尼的冰刀,跑遍了大半個美國。她沉醉在托尼的每一場演出里。她每次都親眼目睹一群群如花似玉的姑娘鳥兒歸巢般地奔向托尼,向他扔鮮花,拋飛吻,求他簽名,追著偶像提些傻里傻氣沒頭沒腦的問題。琳娜不愧是巨商富賈的后人. 她才不干這種毫無意義,頂多討個羅曼諦克感覺的蠢事; 也絕不加入這種傻丫頭的競爭行列。她是史氏王國的三公主,富可敵國的豪門千金。她向父母表示,非托尼不嫁。否則,寧肯出家當尼姑。父母軟硬兼施,百般勸說無效。只得委托琳娜的叔叔,美國分公司總裁喬治進行一番周密調查。結論是此人背景簡單,才貌出眾,行為檢點,學業優良,可堪造就。于是就有了這一次“峭壁餐廳”的晚餐約談。
喬治留下了幾張琳娜的照片,并給他一周的時間考慮。
這些照片是那種竭盡布光取景之能事的攝影佳作。假如六十幾歲的“玉婆”伊麗莎白·泰勒的玉照讓你覺得像個千嬌百媚的少女;麥可·杰克森的KTV讓你覺得是個風度翩翩的白人美男子; 那么,誰還能對這種天衣無縫的光學伎倆給予多少信任呢?
但托尼還是認真考慮了一周。工作、高薪、綠卡、汽車、洋房……這是多少來美新移民的夢想。有人即使奮斗終身也未必全能得到。他呢?只要輕輕一點頭,一切唾手可得。他懷疑自己或許永遠都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每逢人生的關鍵時刻,總有一只巨掌向他伸來
4
婚禮在舊金山灣區最豪華的“香滿樓”舉行。
席開百桌,賓客如云。第二天,幾大中文報紙都在地方新聞版以大幅標題報道:“臺灣史氏千金,大陸冰上王子,喜結連理……”
琳娜的父母,專程從臺灣飛來共襄盛舉。托尼的雙親則無緣露面。事后,他將婚禮的全程錄影帶,一厚疊照片以及剪報統統塞進一個紙箱寄了回去。封箱時,一英寸寬的透明膠帶貼滿了一層又一層,好像有心不想讓父母順順當當地打開紙箱,又好像這箱里深藏著連他自己都不曾剖折,不愿面對的一塊心病和被涂著棕紅色寇丹的女人指甲掐過的自尊。不過,當他一坐進那張為他安排好的座椅,享受著加州的明媚陽光,陶醉于男人在名利場上縱橫馳騁的快感時,一切隱隱的刺痛、不安,又都被撲進窗來的和煦的風,吹得無影無蹤。
眾多的照片中,有一張是琳娜身穿結婚禮服的單身像,也是琳娜最得意的一張。她加印了許多份。不僅掛在家里的客廳和臥室。還在托尼的辦公室墻上掛了一張。
“我要讓你天天看著我!” 琳娜的嬌嗔中還有任性的要挾,“要讓那些不死心的女孩子知道,你不只有太太,而且,你的太太姓史!”
結婚以后,被琳娜拖去參加那些沒完沒了的派對、舞會、慶典、宴請, 才使他感到,在此地的華人圈子里,史姓是何等八面威風。無論什么場合,也無論是被人介紹還是介紹給人,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姓徐,人們總是說:“這是史家的乘龍快婿。”或是:“這是史小姐的先生。”臺灣習俗頗有日本遺風,男尊女卑至今大行其道。出了嫁的女人,一律被冠以夫姓。唯有托尼是個例外,婚后幾乎丟了自己的姓。有一次,托尼不滿地向琳娜說起這種陰差陽錯,琳娜得意地笑起來。她捧起托尼的臉,像欣賞剛買來的一塊寶石,“那有什么關系?你本來就是我們史家的上門女婿!”
琳娜的喜怒無常,不可琢磨倒頗似舊金山的天氣,早上還是晴空萬里,午后就會濃霧彌漫。 不過在人前,琳娜還是很給托尼面子的。豪華的晚禮服,價值連城的鉆戒、胸針,都對她渴望在貴客中惹人矚目的欲念無補。唯有挽在臂上的托尼,他的英氣,他的俊朗,才使她成了星空中的明月。她迫不及待地向認識或不認識的賓客們介紹她的托尼!什么州大高材生、電腦界的后起之秀,當然還有那冰上王子的光輝歷史。她恨不得有一根魔杖,立即把水晶吊燈照耀下的客廳,點化成一片冰場,讓她的托尼在貴婦淑女們仰慕羨艷的目光中,重現冰上王子的風采。
有一次, 在洛斯·阿圖斯山上一個地產商朋友的花園里參加燒烤聚會。占地兩英畝的豪宅帶有國際標準的網球場。一群孩子特意帶來了四輪旱冰鞋,在網球場上橫沖直撞,旋轉跨躍,引來了不少圍觀的客人。大家嚼著烤肉串,喝著冰啤酒,稱贊李家龍龍越長越帥,是不是已經有了一個班的女朋友?金家的小蕊身材多美,舉手投足都有芭蕾明星的派頭……
小蕊的哥哥大鵬玩累了,叉開了兩條長腿坐在草地上,脫下的旱冰鞋一前一后地甩到琳娜身旁。
“喂,大鵬!我要用用你的鞋。”一直被某種欲望折磨著的琳娜忽發奇想,還沒等大鵬答應,她早已抓起旱冰鞋,跑到托尼面前,手腳麻利地解開了他的鞋帶。
“你,你要干什么?”托尼一臉的疑惑。
“上,托尼!”她不由分說,扒下他的網球鞋,把旱冰鞋扔在他的腳下,“來,穿上,給大家表演表演。”琳娜施過粉的鼻尖兒上泌出細密的汗珠兒,心急火燎地催促著。
“別開玩笑了,我從來不玩旱冰的。”托尼本能地往后縮著腿,躲閃著琳娜硬要套到他腳上的旱冰鞋。他再三向她解釋,這是兩碼事。器械與場地的材質、硬度、彈性都截然不同。
眾目睽睽之中,兩人僵持不下。琳娜剎時翻了臉。她低聲卻咬牙切齒地對托尼命令道:“你是要掃大家的面子,存心要我下不來臺嗎?今天就是死,你也要給我上!”
托尼不愿再同她對峙下去。他強吞下憤怨,套上了不合腳的旱冰鞋,心里懷著一絲僥幸,也許不會太壞吧。
然而剛一上場,他就感覺不對,腳下根本無法控制。好在他居然勉強地繞了一個大圈,并試著抬了抬腿。可輪軸連接處的間隙過大,使他完全掌握不了平衡,不知該如何急停、旋轉以及大跳。他覺得腿在抖,肩在晃。雖然他盡量想使自己動作顯得協調和優美,但他知道,為了避免摔倒,他的兩臂在胡亂抓撓,腰胯在不規則扭動,全然一副奮力掙扎的丑態。
圍觀的客人中不時爆出笑聲。但也能聽到一兩句禮貌性的恭維。唯有那批精于此道,天真無邪的少男少女發出一陣陣喝倒彩的怪叫。
剛一下場,琳娜就把他拖走了。
即使她真有些后悔剛才的輕舉妄動,嘴里仍能找出一百條理由來編派托尼的不是:“真是小家子氣,怎么一點兒上不了臺面!”
托尼一再辯解這是完全不同的技巧,他沒摔個大馬趴就不錯了。
“還跟我頂嘴!”史小姐愈發怒氣難消,“明明差不多的事情,稍稍變一點不就行啦?你們大陸人就是笨,怪不得都是窮光蛋!”
“對,你闊!可你的虛榮任性、淺薄無知比你的錢多得多!”托尼忍無可忍,脫口罵道,“以后你去那些狗屁聚會,少他媽的拖我陪綁!警告你,這就給我閉嘴,我討厭你那滿口鳥語!”
史小姐怔住了。結婚以來,她頭一回看到托尼發作。此前,她已經習慣了托尼對她的百依百順,心滿意足之中不免有些乏味. 現在,當他像獅子似的吼起來時,她又在意外中感到某種刺激。
晚上睡覺時,她硬把賭氣搬去書房的托尼拖回了主臥室。在四壁鑲滿鏡子的大理石浴室里,她無限柔媚地解下了他的睡袍,自己的粉紅真絲繡花睡裙也倏地滑落下去。
“哦,托尼,你好棒、好帥、好迷人!你今天一定好累好累。來,我給你按摩。仿佛白天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她是天下最溫柔賢淑的女人。母親怎么說的?對男人要恩威并重,有張有弛。
指甲涂滿棕紅寇丹的手,在托尼全身隆起的肌肉上如饑似渴地摸索,然后又小鳥依人般地將整個身體貼了上去。忽然,一只手神經質地捉住了那無意間勃起的下體,另一只手擰開了淋浴花灑的開關; 清涼的水流噴灑在她滾燙的身上。她尖銳地呼叫著,將托尼推倒在水花四濺的地面上。托尼擺動著頭顱,躲避著迎面撲來的水花,琳娜趁勢騎到他身上,仿佛他是她胯下一匹馴服的馬。
這是琳娜最喜歡的姿勢。新婚第一夜,史小姐胯下的新郎就是這樣第一次仰視他的一絲不掛的新娘。在水霧中倍顯朦朧的燈光下,琳娜瘋狂地忘情地在他身上躍動著,扭擺著。被水浸濕的長發在他胸前抽打著,被水沖花了口紅的雙唇在他臉頰上吸吮著,最后,他又幾乎被猛地覆壓下來的乳房窒息了。
5
托尼揚起臉,視線正與辦公室墻上照片里身著婚紗的琳娜的目光相遇。憑心而論,刻意包裝、精心打扮的史小姐確有幾分姿色。倘若他們真誠相愛,倘若琳娜真是賢良,做招贅的女婿也沒什么不好。可婚后的一切,卻讓他越來越透不過氣。好在這一切很快就要結束了。剛才,他給律師打了電話,律師說,離婚協議書三天前就準備好了,他隨時都可以去取。
電話鈴忽然響了,誰呢?他剛通知過總機的接線小姐,他已經辭職了。從現在起,不接任何電話。他又通過電腦網絡,向所有的客戶發出自己的工作有變,聯絡方法另行奉告的通知。
他遲疑地抓起話筒,是喬治。他約托尼出去吃午飯。
“只告別敘舊而已,不談其他。”喬治說。
他婉言謝絕了喬治的美意。他還有許多東西要收拾,再者,他也不情愿陪著這位當年的月老去吃這頓最后的午餐。
他早已打定主意,今天這頓午餐,要去公司大樓旁的那家“SUNCOFFEE”。這家小店位于園區的正中,既對內又對外,由一對韓國夫婦經營。除了菜單上平日供應的漢堡包、熱狗、三明治以外,每日還推出一兩樣各國風味的“LUNCH SPECIAL”(特別午餐)。經常更換的中國、日本、韓國、越南、意大利、墨西哥等各種菜式,為小店招徠了大批英語中帶著濃重口音的外鄉客。托尼手下一位老美推銷員說,這里賣的“凱薩迪亞”墨西哥牛肉奶酪煎餅,比他的墨西哥丈母娘做得還地道。每天中午,這里人流不斷,坐無虛席,總要到兩點左右才略顯清閑。
封好最后一只箱子,托尼離開大樓,向“SUN COFFEE”走去。這條熟悉的小路,兩年多來走過無數遍,然而,只有一次終身難忘。
那天中午,他照例憑窗遠眺,竟久久不見他渴望的身影。女工們用畢午餐,漸漸走散了,那張笑臉終未出現。起初,他竭力把那笑容嚴嚴實實地埋在心底。可她竟像一縷擋不住的陽光,一陣關不住的春風,晃得他睜不開眼,吹得他心旌搖蕩。可是今天,她沒有來。是生病了?要不,就是辭工了?不,不!他連她的名字都還不知道,她怎么能就這樣走了?
一點半了,該是他吃午餐的時間了。他又擔心他剛離開,她恰巧此刻現身,豈不失之交臂?
他決定打電話請“SUNCOFFEE”送一份外賣。
就在他剛剛點好菜時,她出現了!但她手里沒有便當盒,也沒有走向花壇,而是徑直朝“SUN COFFEE”走去。
托尼急忙朝話筒喊著取消外賣,便奪門而去,沖出大樓,迅速跟上了她的腳步.他第一次這樣近地審視她的背影。今天,她的馬尾編成了發辮,在腦后盤出一個圓圓的發髻。潔白耀眼的襯衣領口上,露出挺拔、纖細的脖頸。藏青色的牛仔短裙下,兩條被陽光曬成橄欖色的腿光潔而修長。白色的網球鞋,白短襪上,鑲著一道與裙子同色的藏青。她腳步輕盈而迅速,使托尼想起去太浩湖度假,有時會看到別墅后花園的野鹿,旁若無人地在花園中徜徉,還沒等你看仔細,它已輕松敏捷地躍上了房后山坡的紅松樹林。
他們一前一后來到“SUNCOFFEE”的柜臺前。
此時餐廳里已空無一人。這正是托尼所期望的。姑娘仰臉看著密密麻麻的菜單,猶豫不決。
“可以嘗嘗這兒的拉薩尼亞,很地道的。”托尼試著用國語向她建議道。
她吃了一驚,扭過頭來,瞪大了眼睛,嘴唇輕輕動了動,大概想重復這個繞口的菜名,又吃不準似的。
“是呀,拉薩尼亞!”五短身材的韓國小老板吉米高聲吆喝著,“今天是意大利餐,拉薩尼亞配蒜蓉面包,水果沙拉. ”
托尼越過姑娘,同吉米打了招呼,要了兩客,付過賬,回身向姑娘笑道:“就剩最后兩份了。我吃一份不夠,兩份又太多。估計咱們倆合作, 一定各得其所。”
托尼畢竟是久經沙場的冰上王子。盡管端托盤的手在微微顫抖,但說話時的神情,仍坦然從容得好像他和她是一條生產線上的工友,或是一個家里出來的兄妹。
“你這是……”她果然講國語,還是標準的普通話。
“照顧照顧人家生意。”托尼朝吉米眨眨眼,“要是這兩份剩下了,他老婆非逼著他都吃下去不可!”
她卟哧一聲笑了。又是那種異樣的,令他怦然心動的笑聲。像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堡敞開了門,吹出了一縷清風。
托尼把她帶到一張餐桌旁,放下托盤,又去買來兩瓶阿爾卑斯山礦泉水。
“來,就為這拉薩尼亞干杯!”托尼舉起手中的水瓶。
“等一等,我先付你錢。”姑娘說著掏出一個小錢包。
托尼把托盤推到她面前:“先嘗嘗再說。愛吃,算你的;不愛吃,算我白請。”
“是這樣,那就應該說不愛吃了,對吧?”姑娘俏皮地歪一歪頭,接過托尼遞來的帕米桑奶酪粉聞了聞,“喲,什么味兒呀?跟臭腳丫子似的!”
托尼忍不住大笑。久違了,這一口清脆道地,字正腔圓的北方鄉音。在琳娜的口中,永遠是那一嘴荒腔走板的臺灣國語,把“媽媽”說成“馬麻”,“爸爸”說成“把拔”,還有什么“葛格”(哥哥),“底迪”(弟弟)……托尼每逢聽到,都會起一層雞皮疙瘩。
姑娘頓時緋紅了臉:“對不起,吃飯時說這個……”
“沒事兒。”托尼揮揮手,“聽到鄉音,你瞧,我胃口大開!”說著,叉起一大塊沾滿臭腳丫子味奶酪粉的意大利烤面,塞進嘴里。
她也吃得津津有味。不做作,不矯情,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大大方方。以至托尼生出錯覺,好像他們真的已經認識了很久。他的緊張,窘迫也在不知不覺中煙消云散了。
“你叫什么名字?”托尼問。
“辛迪亞。你呢?”
“托尼。”
提問到此為止。
這是托尼剛來美國就學會的第一條社交守則。美國男女初次約會,吃飯,可能都不問對方的職業,家庭; 更有甚者,可能彼此同眠共枕之后尚不知對方的姓名,只兩情相悅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