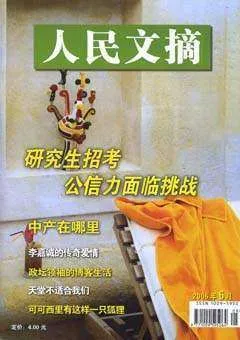嫁了個英雄過日子
丁曉兵的事跡我是在戰地醫院聽到的。1984年,在邊境一次重大軍事行動中,作為“第一捕俘手”,他在生擒一名俘虜往回撤的時候,一枚炸彈突然炸響,他倒在了血泊中。醒來時,他的右手被炸得只連著一點皮肉,他以驚人的毅力用匕首割下殘臂別在腰間,和戰友一道扛起俘虜在叢林跋涉了4個小時,身后留下了4公里長的血路。當遇到接應小分隊時,他一頭栽倒在地,暈死過去。戰地搶救人員當時以為他已經犧牲,開始為他整容,準備送往烈士陵園。恰好那個時候,后方醫院巡診醫生路過,便將他緊急送往戰地醫院,切開他的腿部動脈,強行注入2600CC血漿,經過三天兩夜的搶救,他才活了過來。但是,他的右手永遠地留在了戰場。
說實話,聽到這個兵這么堅強,我當時對他也是特別關注。而且,他一被抬進醫院就表現出了跟其他傷病員不同之處。上手術臺做手術時,麻醉藥失效,他忍痛一聲沒吭,卻把手術臺上的床單抓破了……
他這個人真是不簡單。現在想來,我和他愛情的種子,也許正是那個時候開始種下。
后來,他的事跡轟動了全國,他被保送上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快過年的時候,他催我去他的老家合肥結婚。其實那時什么也沒有準備,連新房都沒有布置,但是我們都覺得這個并不重要。我從昆明開始往合肥趕。也許好事多磨,由于交通原因,大年三十我竟然是在武昌火車站度過的。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他在家鄉是個大名人,幾乎家喻戶曉。婚禮被安排在他父母所在單位——合肥鋼鐵公司大禮堂舉行。合肥鋼鐵公司工會主席主持婚禮。合肥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做證婚人。迷人的《婚禮進行曲》在城市的上空飄蕩。
突然,婚禮中,傳出一聲稚嫩童音:“新郎叔叔抱抱阿姨。”整個現場像剛打響的一場戰斗又在瞬息結束一樣一片啞然!所有人的目光從聲音響起的地方移到了他身上,盯著他的那只右臂,那一只空空的袖管!
他突然一怔,然后“啪”地用左手第一次給我和父老鄉親們敬了不同尋常的軍禮。他說:“鄉親們,父老們,我的右手永遠留在了前線,今生今世,我無法完成所有新郎應該給予新娘的擁抱,但我可以向我的新娘致以更為崇高的軍禮!”話音未落,我的淚水和現場許多客人的淚水不停地往下流。合肥電視臺將我們特殊的婚禮制作了新聞專題,向全市人民播報這對戰火硝煙新人的新婚實況。
這么多年,一路走下來,酸甜苦辣,什么感覺都讓我嘗到了。
我臨產那天,他從幾十公里以外的軍事訓練場沖向醫院。分娩讓女人感覺到自己原來會如此脆弱。
見丈夫來到身邊,我心里的緊張感有一些放松,和他探討起給即將到來的小生命“命名”的事。手術車來了。護士們等著他把我抱上手術車。裝著假肢、而且把假肢揣在褲兜里的他愣住了。從認識到現在,他從來沒有在嚴格意義上擁抱過我,這個動作不是靠苦練就能練出來的。
尷尬如同婚禮的場面再次出現。他看著我。周圍人看著他。
“你是產婦的丈夫嗎?趕緊抱啊,把你妻子抱到手術床上。”
“你是男人嗎?還愣著干什么,難道還需要別人幫你抱嗎?”
護士的話刺耳穿心。我見他面紅耳赤,額頭上青筋凸起。這一刻,我覺得他是可憐的,我到現在還記得他當時的表情。到現在為止,這一輩子惟一讓我感覺他可憐的就是那一次。我知道,那一次,已經傷到了他最看重的男人的尊嚴。
見到這場面,我趕緊說:“對不起,大夫,他不方便,我自己來。”
我咬緊牙關,挪動著笨重的身體,艱難地爬上手術車。
就在那一刻,羊水破了,血流滿地……
我進了產房。那個時候還沒流行丈夫陪同妻子分娩,他候在了產房門外。門外有兩張長條椅子,他沒有坐,一直站著往門縫里瞧個不停。
他焦急的聲音透過兩道玻璃門被我聽到了:“我妻子陶婉珠怎么樣?我妻子陶婉珠怎么樣?”
門關上了。
我還是隱約能聽見他的跺腳聲。多年來,他遇到著急的事時,最習慣性的動作就是跺腳,這種響聲就始終縈繞在我的耳邊無法消失,我覺得這種響聲好動聽啊,比“我愛你”那三個字動聽得多啊。
手術車推出來了,我身邊到處是瓶子、吊針。
我感覺丈夫看著我的眼神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感覺非常特別,讓我一下子什么也說不出來,一下子覺得受罪的不是我而是他。我剛說完“沒事沒事”幾個字,喉嚨似乎就被一塊硬物生生卡住了。
車往病房推時,他一把幫我抹掉了眼角的淚水,他原本就是戰場上槍林彈雨要第一個沖上去堵槍眼兒的人,看不得女人的眼淚。然后,他用手掌輕輕按在我的額頭上,手術室到病房的距離很長,天氣又熱,我感覺他滿手的汗順著我的額頭流了下來……
十多年后,我依然對那一幕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