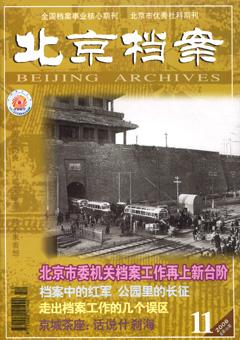芻議社會檔案兼管
郭東升
一
黨政文件出現在收藏品市場上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檔案報刊時不時有關于北京報國寺潘家園買賣檔案的文章。不止于北京,這在全國怕都不少見,比如上海文廟市場。筆者在本市舊書攤上發現過一本打印的《臨清文革大字報選編》,要價150元,一份《中共臨清縣委關于清查“516”的計劃》,要價100元,一份縣委、縣革委表彰先進的紅頭文件,要價10元等等。初見到這些東西上市筆者心里有些復雜。大概是有些職業病吧,首先是想到檔案執法收購。既而則是嘆息,這些文件市檔案館里都還有重份的文件存著。當年搞檔案館管理升級時,對館藏重新進行鑒定,剔除了數萬份的重份的文件,討論它們的銷毀時,筆者力主繼續保存。當被詰問它們還有什么用處時,筆者竟異想天開地說:“如果檔案館實在不好再保存它們,把它們一份一份的拿到市場賣給別人,讓別人收藏。”我的同事瞪大眼盯著我,卻不再說什么。
作為一個比較頑固的反檔案商品論者,筆者當然知道買賣檔案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行為,上述想法只不過是在某些檔案面臨銷毀危機時所作出的本能的反應。現如今,筆者的異想天開已變成別人的行動。現在,要對人家進行檔案執法,我們自己心里是很嘀咕的。嘀咕什么呢?首先,對人家進行檔案執法,人家要問,這買賣的是檔案嗎?我們應怎樣回答?國家檔案局印發的《機關文件材料歸檔和不歸檔的范圍》規定,不歸檔的文件材料的范圍包括了重份文件。國家檔案局頒布的《檔案館工作通則》規定的檔案館接受檔案的范圍,縣級檔案館只接受具有永久和長期保存價值的檔案。如今人家買賣的是檔案館里都保存的文件,甚至于在館里還保管著其重份文件,也就是說那本市舊書攤上賣的文件,按《機關文件材料歸檔和不歸檔的范圍》規定,在檔案形成單位它是不應歸檔的重份文件,它不是檔案。自然,站在檔案館角度,它就更不是需要接受的具有永久和長期保存價值的檔案了。如此,我們再搬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檔案法實施辦法》關于出賣檔案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批準、禁止出賣屬于國家所有的檔案的規定,依法追究人家的法律責任,便很有些理短,人家可以說,按檔案法規的規定,出賣的不是檔案。當然,檔案館也不會對上述所出賣的文件進行收購。你總不能把它們收購進來,再當作不歸檔的重份文件銷毀處理掉吧?!
二
筆者對檔案商品化觀點持反對態度,對倒賣檔案牟利持反對態度。而對檔案買賣現象的客觀存在,筆者有以下建議,第一,修正我國檔案業務建設規范中利于檔案自由買賣方面的文字條款,修補檔案法規體系中的漏洞,避免檔案倒賣者鉆其中的空子。比如,《機關文件材料歸檔和不歸檔的范圍》中,被列入“不歸檔的文件材料范圍”的“本機關的文件材料”的重份文件。事實上,這一規定早已過時。1998年的《山東省機關檔案工作規范》便規定了“本機關重要發文實行兩套制”,這自然是為了緩解日益增長的檔案利用需求與檔案保護之間的矛盾。現實中,許多檔案保管機構的某些印發文件,為適應利用需求正在被多套的送上檔案柜架。第二,建立社會檔案(非國家檔案保管部門所有的檔案)動態監管機制,對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實施具體有效的全方位監控。其監控內容應包括以下幾點:
建立社會檔案監管公告制度。要實行對社會檔案的監管,首先應讓公眾特別是讓集體和個人所有者知道被監管社會檔案的具體范圍,這就需要向社會發布社會檔案監管公告。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檔案并不都是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其中那些對國家和社會不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應當保密的檔案除外)是不需要國家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監管的。但這其中的具有與不具有之界限的劃定卻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誠然,有些集體和個人所有檔案在形成之初便可顯出國家和社會價值,但也有許多檔案的價值隱秘性很強,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才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漸漸顯露出來。因此,被監管社會檔案應有現行與歷史之分。所謂現行檔案即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新近形成的檔案,如與國家現行檔案概念相區別,也可稱其為新近社會檔案。這里新近的概念似以15年以內所形成的檔案為時限比較合適。15年是國家機關文書檔案短期保管時限,在這一時限內,集體與個人可以從容地考察其新近檔案的價值,國家檔案行政管理者亦能較為從容地對本轄區內新近檔案的國家和社會價值給出鑒定結論。新近檔案的監管公告應每年定期發布一次,特殊情況下,還應隨時發布。同樣理由,我們可以把被監管的15年以上的社會檔案稱之為非新近檔案或者往常檔案,往常檔案監管公告應不定期的發布,或者搭車與新近檔案監管公告合并發布。
協調《文物保護法》與《檔案法》關于文物檔案買賣條款的不協調之處,嚴謹檔案監管法規的可操作性。要嚴密地、全方位地構建集體和個人所有對社會有價值檔案監管體系,必然要解決文物與檔案在法規文件上的不協調問題。文物與檔案兩概念之外延多有交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列舉文物概念之第四部分,“歷史上各時代重要的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和圖書資料等”,便是檔案概念外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此,一事物被檔案界界定為檔案,而在文物界則被界定為文物者不止成千上萬,甚至數以億萬計。而《文物保護法》與《檔案法》關于文物與檔案買賣的規定有很大不同。《文物保護法》在“民間收藏文物”一章中規定,“文物收藏單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從文物商店購買”“從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購買”文物,“公民個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換”也是合法的。《檔案法》規定,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或應當保密的檔案,檔案所有者“向國家檔案館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出賣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嚴禁倒賣牟利,嚴禁賣給或者送給外國人”。
從以上兩種表述可以看出,國家對國有文物與國有檔案之外文物與檔案流動的法律規定是有很大不同的。其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國家禁止將檔案作為商品買賣,更不允許檔案買賣市場化。對文物,則網開一面,有條件地允許其買賣。這當是檔案對于國家利益、國家安全較之文物利害關系更緊要的緣故。亦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某些檔案以文物的面目流入市場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帶來嚴重損失的問題。依筆者看,這問題已相當嚴重了。
2002年《中國檔案》第11期載郭紅解文章《從檔案進入拍賣市場說起》云:“在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前些日子舉辦的一場拍賣會上,一批檔案史料走上了拍臺”,“《國內和平協定》(馬敘倫本)1500元成交;成交價格最高的是一卷《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信札》,有宋慶齡簽發的《上海文藝界致司徒雷登大使》信”。作者扼腕直陳:“盡管是一種‘尷尬,但檔案史料進入文物拍賣市場畢竟已成為現實。”
2005年3月18日《中國檔案報》之《檔案大觀》一篇《抗日史料火爆書刊拍賣市場》有如下文字:“2002年3月,北京報國寺、潘家園收藏品市場同時驚現1941年至1945年山東解放區抗日軍事檔案數十冊,其中40件日軍戰俘檔案和八路軍115師手繪作戰地圖為極其珍貴的抗日史料。‘四大天王合為一股,匯同羅榮桓元帥家鄉藏界書友當日集資3.8萬元,搶在海外買家之前將珍品拿在中國人自己手上!”讀這段文字讓檔案人好不觸目驚心。我黨我軍形成的珍貴革命歷史檔案以文物的名分被拍賣,且是搶在海外買家之前將珍品拿在中國人自己手上的,如此之局面,真叫在此時無力回天的檔案人欲哭無淚,而只能時時抱憾在胸了。
當然,檔案人不能只有抱憾,要有解決問題的辦法。筆者提出必須解決文物與檔案在法規文件上關于兩家買賣內容的不協調之處。如何修改?如何解決檔案文物兩個概念交叉給檔案買賣執法帶來的難題?筆者以為,應該依重來源原則,將來源原則的檔案館室整理、保管作用引入擴大到社會檔案兼管領域。
具體做法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之第五章,民間收藏文物之第五十一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不得買賣下列文物”一條內增加一款,可以如此表述:民間收藏文物同時是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官辦社會組織及個人執行公務形成的檔案與革命政權及個人從事革命活動形成的檔案的。這類文物的保管、轉讓、出賣方式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同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之第十六條,第二段后增加這樣的文字“前款所列檔案中同時是民間收藏文物的,其來源特征同屬于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官辦社會組織及個人執行公務形成的檔案與革命政權及個人從事革命活動形成的檔案的,其保管和流動,按本條和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而不適用《文物法》關于民間收藏文物經營買賣的規定。上述檔案的認定工作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組織實施。這樣,按來源原則,按檔案形成單位(個人)國有性質來避免其所形成檔案作為民間收藏文物被買賣比較適當。檔案與文物在概念外延上雖有大量重復,但所重復之檔案并非都對國家社會有價值或涉密,對國家社會有價值或涉秘者大多屬于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官辦社會組織及個人執行公務形成的檔案與革命政權及個人從事革命活動形成的檔案。因此,如此規定既能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所在,又便于檔案行政部門對檔案文物雙重身份之事物為檔案法所不容之買賣者實施檔案執法。
作者單位:山東省臨清市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