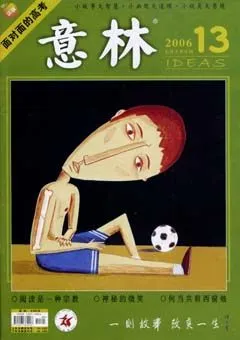回報父愛那滋味
巖 石
每個人都是父輩與下輩間基因鏈的一環,因此,人間的親情與香火才得以溫暖地延續下去。
27年前,在父親臥床不起、病情最為嚴重的時候,我恰好在家等待畢業分配,有幸和父親度過了難忘難舍的最后日子。
父親退休前是一名維修工,平時不愛說話。小時候,我就記得他總是蹬著一輛三輪車,風里來雨里去的,刷油哇,鑲玻璃呀,干得又快又好。那兩道三輪車的車轍,好像是兩道時間的軌跡,慢慢地,我們就長大了。父親對自己的晚年很滿意,說自己三代同堂,兒女也孝順。遺憾的是,父親不到70歲就得了癌癥。
父親得的是食道癌,到了晚期,吃東西很困難,只能吃豆漿泡油條。上世紀70年代末,連豆漿、油條這樣的小吃也很缺少,買時要起早排隊,還限量供應。那時,每天天不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頂著凜冽的寒風,去三馬路火燒鋪給父親買早點。看到父親吃力地將油條掐成一小段一小段,再在豆漿里長時間地浸泡,我的心就如刀剜一樣難受。
有時候我去晚了,排了一早的隊,輪到我時卻已籃空桶凈。為了父親的早餐,我只好去鴨綠江飯店對過的冷食宮二樓買鮮奶、油條。因為牛奶價錢貴一點兒,許多人不買,所以反倒容易買到。可每當這時,父親會不高興,說:“沒有就不吃,怎么買這么貴的奶回來呢?”我知道父親是怕多花錢,是惦記著家里。
隨著父親病情的加重,他連豆漿、油條也咽不下去了,而且經常是吃一半吐一半。同時,父親體質急劇下降,終于臥床不起了。后來,父親連排便的力氣都沒有了,即便是咬著牙、鼓著肚子也無濟于事。不忍看到父親的痛苦,我就用手幫他摳。從此,我又承擔了給父親清洗糞便的任務。父親很不安,我安慰他說:“小時候,我們不也是父親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大的嗎?盡孝的機會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我對父親說:“爸爸,我很榮幸。”爸爸聽了,眼淚就流出來了。
那天,報到的通知來了。我高高興興地拿著人事局簽發的派遣證,第一個要告訴的就是父親。他聽了,臉上露出少有的笑容。得病以來,父親幾乎再也沒笑過。當晚,父親還在我的攙扶下坐了起來,將我工作的消息告訴了來我家玩的同學。盡管父親說話很吃力,但臉上的笑容仍是少有地燦爛。他的笑,一直印在我的心底,成為一道永遠的記憶。
那天,父親說了不少話。我很驚奇,以為是父親吃的中藥見效了。那時,我還在內心里為他祈禱,我相信世界上沒有比那更純真、更虔誠的祈禱了。
第二天早上,父親病情突然惡化,母親說要給他穿衣服時,他點了點頭,同意了。他好像還想說什么,但只是嘴張了幾下,沒說出來。很快,父親就去世了。
那年是1979年臘月十八,上午9點,父親走了。是在得知我——他最小的兒子有了工作的消息后走的。那一年,他剛剛70歲。
(肖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