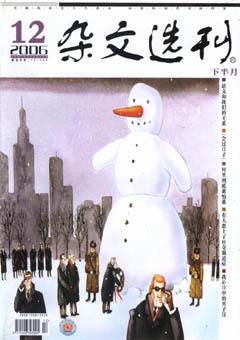我怎么就名不起來等
阮 直等
我怎么就名不起來
阮直
三十年前,我“名”了,為了保護生產隊的鴨子,我跳進了齊腰深的洪水中,用根竹竿系一個大網兜,套回七十只生產隊的鴨子,就是換成當今澳洲的泳壇名將索普他也未必能有我這本事。因為我有一顆紅心,做好了兩手準備,獻出生命和青春也不能讓洪水把生產隊的鴨子沖走。遺憾的是沖跑的鴨子比我套回來的多。不過我的事跡還是上了廣播,登了報,全縣十六個人民公社,我巡回演講了八個。當年給我的掌聲不比如今的“粉絲”鼓給潘長江的少。
可我這么大的“名聲”第二天在縣委招待所的小賣部買一塊肥皂卻不靈了。我們的英雄事跡報告團領隊說:“他是保護生產隊鴨子的某某啊!”耶店員說:“就是保護生產隊羊群的龍梅、玉榮買肥皂也得憑票。”可我一轉身,一個穿四個兜干部服的人也沒什么票,就買走了兩塊肥皂。
封給我那么大的“稱號”,給了我那么多的榮譽,卻頂不上一個肥皂票,我名了一回,也悲哀了一回。
十年后,我又“名”了起來,大學畢業,成了當地的詩人,每月都有好幾元錢的稿費,最多時一首詩得了二十元,哇!相當于我工資的三分之一了。創作會、筆會每年都有,住過賓館,吃過館子,四處參觀、采訪,后來還得了獲獎證書。單位領導對我也刮目相看,空缺了八個月的辦公室主任,讓我當了。我感到我就是那個“斯人也”——天已降大任于我。
有一天,家里買了五百個蜂窩煤,送煤的工人是由鄰居何大伯領進院的,我正準備上班,何大伯說:“你是某某嗎?”我說:“是呀!”何大伯樂了:“可算找到你了,這一中午了,我帶著送蜂窩煤的人問了六家人了,誰都說我們小區沒有這個人,多虧了你大娘腦袋轉了彎,宇慧她爸是不是某某。根據這條線索這才摸對。”啥也別說,眼淚嘩嘩地下了,我在這兒住了五年,連個大號人家都不知道,左鄰右舍封給我的“符號”是借了女兒“宇慧”的光,原來我這詩人僅僅是個“宇慧她爸”。
看來“名”這玩藝都是有圈子的,比如在我居住的圈子,何大伯是名人,他每天為左鄰右舍張羅張羅,管些閑事,小區里沒他,就沒了“領域”;我的女兒是這個小區的名人,她四家流竄,常在李家吃餃子,趙家吃拉面,時常還領回一個“豆豆”、一個“倩倩”,我也知道哪個是他們爸、他們媽,可叫他們的大名來我也不知道。這個小區的名人,老的老,小的小,如日中天的大人,一概無名。
聽說近年韓國女明星在中國很有名,可我就不知道都有誰,有個姓“金”的女明星在電視的廣告上見過,那也是一不注意時讓廣告給輻射了。女兒說:“她是韓國第一美女。”我認真地瞄了一眼,覺得是美,可這樣的美女我們哪個城市沒有?我估計,這個名人也是名在她的那個圈子里,就像在我的眼中,阮直也是個“名人”,可是我在大街上對一百個人進行現場提問:“你知道名人阮直其人嗎?”他們的回答百分之五十是“你有神經病吧!”從此之后,我就再不做名人的夢了。可惜的是我的覺悟晚了五十年,因為今年我五十一歲。
[選自《文新傳媒》]
兒子,兒子
劉吾福
我曾經為有一個聰明的兒子感到驕傲和自豪。我常常在朋友面前拍著我兒子的后腦勺說,這是我兒子!朋友對我說,多像你,簡直是一個模子里脫出來的!
兒子在幼兒園時就能背誦“鋤禾日當午”。就能解答“樹上騎七個猴”之類的腦筋急轉彎,就能唱“南泥灣好地方”。
兒子十五歲時參加中考,僅差一點五分沒有考上市里的重點高中。兒子說,爸,我沒考上重點高中其實是你沒面子,因為我是你兒子。瞧我兒子這話!為此,我和愛人東挪西借湊足了一萬元“超招”費,兒子終于進了市里的重點高中。
我的面子沒有維持多久,讀完高一,兒子的成績已是每況愈下。兒子總是垂著頭,滿臉疲憊,像霜打的茄子。直到有一天,我一個親戚的兒子到家里來,親戚的兒子大學畢業一直沒找到工作,親戚的兒子說,早知如此,那大學還不如不讀呢。兒子聽了這話很興奮,就像注射了一針強心劑。
兒子讀高二的時候,有一天我接到兒子班主任的電話,問兒子為什么沒去上課。我有點奇怪了,兒子明明吃過早飯上學去了,怎么會沒有上課呢?
我突然想起了從家里到學校的街道邊那幾家網吧,心中一怔。
果然不出所料,我把兒子從一個網吧里揪了出來,兒子那時正傾心于一個叫“星際爭霸”的游戲,兒子熟練地操縱著鍵盤,游戲里那個叫做“神族”的魔鬼被我兒子“打”得拼命地慘叫,“救命啊——救命啊——”。我揪著兒子的耳朵說,我得先救救你的命才是!
兒子被我揪回家,我怒火中燒,把兒子摔在沙發里,像摔一只塞了舊棉絮的枕頭。
兒子充血的目光看著我。我像審犯人一樣審問兒子,你說,你不讀書,怎么會有出息?
兒子嘟噥一句,有一個游戲玩家才十三歲……
我說游戲玩家玩出什么啦?
兒子說,你別孤陋寡聞,人家在網吧里呆了整整兩個月,足不出戶……后來成了網絡游戲高手,好多網站老板搶著高薪聘用,月薪八千元!
我被兒子噎了一下。
有一次,我拿過兒子的數學作業本來查:看,兒子把幾道三角函數題都弄得顛三倒四,一塌糊涂,滿頁作業紙上都是鮮紅的叉叉,真叫人慘不忍睹!
我說,兒子,你爸好歹也是個高級教師,相當于大學里的教授級別,題做不出可以問你爸,有什么能難得住你爸的題目嗎?解幾道函數題,不就是幾分鐘的事情么?
兒子不吭聲。
過了幾天,兒子把幾道題目摔到我的眼皮底下,兒子斜了我一眼,說,老爸,這幾道題麻煩您給解一下,只耽誤您那么幾分鐘得了!
我拿過那幾道題,先瀏覽了一遍,發現竟然是奧賽題,我使出了渾身解數去解那幾道題,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
兒子架起二郎腿坐在沙發上,兒子說,已經一個鐘頭了。我聽著墻上的時鐘嘀嗒嘀嗒地嘲笑我,兒子又冒出一句,哎呀,又一個鐘頭了。我知道,兒子給我下了一個套,這一次我要栽在兒子面前了。我對兒子說,過幾天我把答案告訴你吧。兒子昂起了頭,一副打了勝仗凱旋的樣子。隨即,兒子進了他的臥室,兒子的臥室里便激蕩出發瘋般的《東風破》來。
兒子很有一段時間沒有去上課,但也沒有去網吧。兒子現在又迷上了打臺球。兒子進門出門都扛著一根古銅色的臺球桿,就像士兵扛著一桿槍。
兒子跟他媽說,你知道啵?有個小子叫丁什么暉的,從沒讀過大學,但他的臺球打得神,打出了國界,打過了太平洋,捧回許多獎牌,獎金都上萬呢!兒子跟他媽講這話時,眼睛分明斜看著我。
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對兒子實在是沒半點指望了。高考時,兒子合乎情理地沒有考上大學。但兒子很快樂,兒子的臥室里永不疲倦地響起他的《東風破》。
我成天陰著臉,愛人則一副淚眼婆娑的樣子。兒子卻拍著胸脯對他媽說,媽您別著急,說不準兒子比老爸更有出息呢。兒子說完這話,一摔門蹦出去了,留下砰的一聲沉重的門響,讓我的心顫抖了一下。我終于忍耐不住,推開窗子向外面吼了一嗓子,你走吧,走了你就別回來!
兒子真的走了,還在他枕邊留下一張字條:老爸老媽,兒子闖世界去了,兒子定要闖出一片風光來……
我愛人哭了,愛人邊哭邊抱怨我,說兒子是被我逼走的。
當我們苦苦地煎熬了二十天后,終于接到遙遠的都市救助站的一個電話,那里收容了我的兒子,兒子在遙遠的都市“闖”了二十天后無奈地被收進了救助站。接到電話的那一刻,愛人笑了,我卻哭了……
【原載2006年11月5日《今晚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