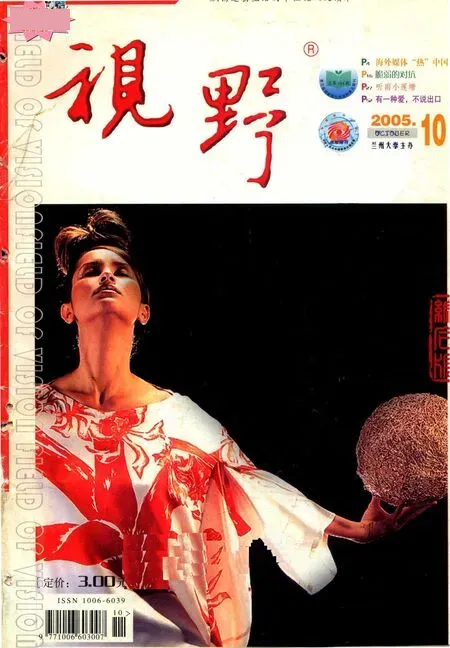脆弱的對抗
北大帶給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我出生在農(nóng)村,畢業(yè)于一所普通的中學(xué)。1992年高考時,因為考得好了一點(據(jù)說還是什么狀元),我進了北大歷史系。
上北大的第一年是軍訓(xùn),我受到很大震動,因為突然間我覺得自己的優(yōu)勢不僅全沒了,而且在某些方面還很無知,很無能。我不會唱歌,不會跳舞,也不會踢足球!同寢室的北京同學(xué)聽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搖滾我聞所未聞;他們還看米蘭·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說,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當(dāng)時我甚至還看不懂,這時我才發(fā)現(xiàn),他們的見識遠在我之上。
軍訓(xùn)時這種差距感還不是特別明顯,回到北大后我才真正地傻眼了:這里有國際馬拉松冠軍,有全國圍棋、田徑和乒乓球比賽的冠軍;有父母是大學(xué)教授從小家學(xué)淵源讀書很多的人;有能獨立舉行舞蹈和鋼琴專場演出的學(xué)生……一般意義上的組織社團活動、組織晚會也沒我的份兒,因為大城市和重點中學(xué)來的學(xué)生這方面能力很強。這個時候,我真的發(fā)現(xiàn)自己一無是處, 12年的讀書生涯幾乎沒有學(xué)到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我是家人和鄉(xiāng)親的驕傲,在北大我卻感到非常自卑。
在看清和承認自己被剝得精光、一無所有的現(xiàn)實之后,我開始拼命學(xué)習(x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大學(xué)四年我只做了兩件事情:看書和踢足球。
因為痛感差距太大,因為突然打開一個知識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強烈的緊迫感,我沒法以一種從容的心境把這些書讀透,而是以一種狼吞虎咽的方式,以一種可怕的速度進行惡補。
在短短四年時間之內(nèi),我瀏覽了諸子百家,通讀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還有《全唐詩》、《劍橋中國史》,以及李澤厚、馮友蘭的思想哲學(xué)史等等大量書籍。但這樣的速度能讀出一個什么樣的結(jié)果,是可想而知的。
未來的大師應(yīng)該由我培養(yǎng)出來
受到如此強烈的刺激之后,再回過頭來看我所受的基礎(chǔ)教育,我難以抑制自己的憤怒,我痛恨教育體制,痛恨課程設(shè)置,痛恨教材,聲稱對我的中學(xué)老師“一個也不寬恕”!
到大四時,我已經(jīng)覺得要成為學(xué)貫古今中西的學(xué)術(shù)大師的夢想恐怕不太可能實現(xiàn)了,于是,我產(chǎn)生了要到中學(xué)去,改變基礎(chǔ)教育現(xiàn)狀的強烈沖動。我為當(dāng)代中國沒有思想大師、文學(xué)大師、史學(xué)大師感到深深的遺憾!我想:未來的大師應(yīng)該由我培養(yǎng)出來。要是能培養(yǎng)出魯迅、王國維這樣的人,我該是多么幸福呀!
后來自貢蜀光中學(xué)接納了我。這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學(xué)。剛到學(xué)校報到的時候,同事聽說我是北大的都感到很驚奇,說:“我們沒有別的出路才教書,你北大畢業(yè)有的是好去處,到中學(xué)來干什么?”有的問:“你的女朋友在自貢嗎?”還有學(xué)生和老師私下里傳說:“他在大學(xué)一定犯過錯誤!”
三年痛苦而失敗的教書生涯
在蜀光中學(xué),我主要擔(dān)任高一年級的歷史教師。這個時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大量給學(xué)生介紹真正有價值的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藝術(shù)等方面的好書,介紹各種文學(xué)藝術(shù)流派和各種哲學(xué)思想,讓他們在上大學(xué)之前就積累大量有價值的知識;第二,對學(xué)生進行歷史知識和思想的啟蒙;第三,高度重視藝術(shù)和體育教育。
隨著知識視野的打開,思想的提升和見識的增長,北大四年已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讓我脫胎換骨!明白了那些陳舊和僵化的東西毫無意義之后,我已經(jīng)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時候的學(xué)習(xí)方法教給學(xué)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數(shù)老師那樣機械地講授課本上的死板的知識。以那種教法,即使我教的學(xué)生都考上了北大和清華,我也不會有任何成就感。因為那在相當(dāng)程度上是反教育的,不可能培養(yǎng)出有人文情懷和公民素養(yǎng),又具有真正創(chuàng)造力的人。在那樣的教育中我也不可能獲得任何創(chuàng)造的快樂和意義感,同時,我對教育和社會的責(zé)任感也不允許我這么做。
每接一屆學(xué)生,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給學(xué)生洗腦。我跟他們說你們過去在語文、歷史等課上學(xué)的東西相當(dāng)部分都是無用甚至有害的偽知識,真正的文科知識你們連夢都沒夢見過。然后在學(xué)生目瞪口呆之時就開始對學(xué)生進行知識轟炸:從《史記》、《左傳》、四書五經(jīng)到唐詩宋詞;從穆旦、海子到蘭波、艾略特;從弗洛伊德到超現(xiàn)實主義;從涅磐樂隊到行為藝術(shù)。
這個時候,學(xué)生的態(tài)度就開始分化:一部分只重考試的學(xué)生一看我講的跟考試沒關(guān)系,就開始做其他科的作業(yè);一部分雖然聽得云里霧里,到底還是覺得新奇,還是勉強在聽,不管聽不聽得懂。你想這樣密集的流派、理論、人名、書名的轟炸,學(xué)生怎么受得了!不坐飛機才怪!
學(xué)生對我的評價也開始出現(xiàn)分化:有的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有的喜歡聽我吹牛,因為我居然會跟他們講兵器知識講戰(zhàn)爭侃武俠聊足球!有的學(xué)生惱怒地說:“誰聽他的,聽都聽不懂,他在那里自我陶醉!”
在我教書一段時間之后,校長從學(xué)生家長和老師那兒得到了一些關(guān)于我的負面信息,于是,特意來聽我的課,聽完之后他找我談話:“你上課不能發(fā)表自己的看法,要少講課外的東西。本來我們準(zhǔn)備在你熟悉一年之后就對你委以重任,讓你教高三文科班!現(xiàn)在你老講課外的東西,講教材以外的學(xué)術(shù)觀點,一點都不管考試,又講得那么深,我們怎么敢讓你帶高三?”
我說:“我不想帶高三,因為我不想摧殘學(xué)生!”校長臉色大變,說:“難道高三老師都是在摧殘學(xué)生?”我默認。與我同一辦公室的高三老師則臉色尷尬。
也許我太書生氣了,由于在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時極度缺乏策略,我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而學(xué)校環(huán)境的極度僵化、封閉和壓抑,則讓我覺得自己如置身于瘋?cè)嗽阂话?在自貢蜀光中學(xué)教書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毅然“飛越瘋?cè)嗽骸保x開自貢到了廣州,開始尋覓新的出路。
鏈接:
我們的無知
紅蓼知秋
他一開口就告訴我們,中學(xué)歷史教材沒什么好教的,接著便開始把我們知道的熟悉的一點點東西貶得抬不起頭,又狂轟濫炸般把一大筐我們聞所未聞的東西捧得天花亂墜。于是第一堂課下來,我們就覺得自己無知得如同白癡。
第二堂歷史課就有人開始做其他科作業(yè)或是睡覺了,包括我在內(nèi)的另一部分人則仍然饒有興味地聽他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地神侃……這種情形一直持續(xù)到最后一堂課。
他的另類從頭到尾地貫穿在我們對他的記憶中,沒有過絲毫的磨損。
他大談魯迅、穆旦、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我們卡夫卡、艾略特、《人間詞話》。他曾經(jīng)傾情地為我們朗誦穆旦的《春》,還曾請來他的一位朋友為我們講那些陌生的音樂,講譚盾、葉小鋼。他覺得我們是那么的糟糕,卻又堅持不懈地灌輸給我們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僅僅是為了我們上大學(xué)后不會像他當(dāng)年一樣“像個白癡”。從這一點說,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師都看得遠、為我們考慮得遠,因為他沒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對輕松的高一,他讓我和很多同學(xué)瘋狂地迷戀上了文學(xué)——我和朋友從學(xué)校圖書館“挖”出了《人間詞話》和幾本詩集,興奮地讀著、談?wù)撝?/p>
除了課堂上的范美忠,我還看到過足球場上汗流浹背的范美忠,大橋上一手拎菜一手捧書的范美忠,小書店里蹲在地上看書的范美忠。他是我所見過的把“另類”二字闡釋得最準(zhǔn)確最自然的人。惟一一次在辦公室里見到他是一次期末考試后分發(fā)各班批改后的試卷。這種場合的混亂可想而知,每個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績。嘈雜混亂中,他憤憤地嚷了一句:“一個分數(shù)就讓你們成了這樣!”他的話淹沒在一片喧嘩中。我當(dāng)時正巧站在他旁邊,聽見了這句話,從那以后我再沒去打聽過自己的分數(shù),不管是什么考試。
他一定有過很多的故事和傳奇,但我們不敢向他打聽,只能從他講課時的言語中零星了解一些。他的孤傲、博學(xué)和強健,給了我北大的最初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最后在北大和清華間的選擇。但他已經(jīng)離開了,這個學(xué)校里關(guān)于他的記憶在年復(fù)一年地淡去。我們有幸成了他在這里教過的最后一屆學(xué)生,我們離開后,不知以后的學(xué)生們還會不會知道范美忠這個名字。即使知道了,又如何呢?不會再有人給他們講葉芝蘭波波德萊爾了。
無論如何,我對他只有感激和敬佩,這是一種最傳統(tǒng)最純粹的學(xué)生對老師的感激和敬佩,因為他根本不認識他教過的這些學(xué)生,也不屑于他們對他的任何態(tài)度。我曾想過,如果現(xiàn)在有機會再見到他,甚至和他互相認識,我也會躲避、放棄,因為我知道自己只會被他藐視。我曾把他講的一堂課錄了一部分到磁帶上,我只是常常懷念著那段有他這樣的老師的歲月,那段毫無功利之求的沉迷于文學(xué)的歲月。
(本文作者是2002年四川省高考理科狀元,現(xiàn)為北大光華管理學(xué)院學(xué)生,也是范美忠的學(xué)生,網(wǎng)名紅蓼知秋,文章首發(fā)在“榕樹下”散文隨筆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