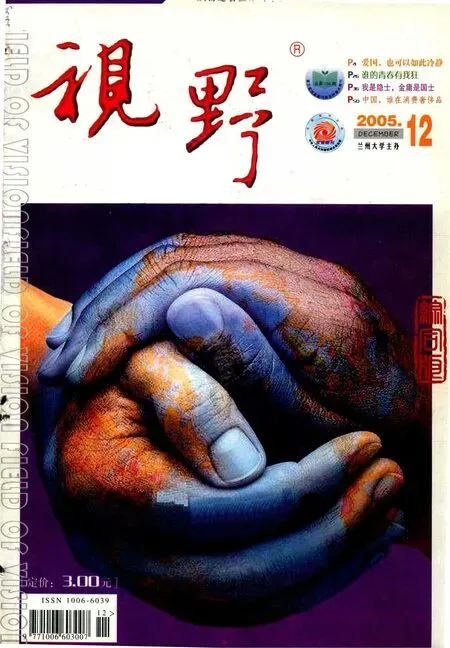我是隱士,金庸是國士
梁羽生 黃惟群
對話人物
梁羽生:香港著名武俠小說家,被譽為“新武俠鼻祖”。本名陳文統,1922年生于廣西蒙山,1949年定居香港,一直供職于香港《大公報》。此后在澳洲隱居,迄今已有18年。
黃惟群:澳洲著名華人作家,曾任當地華文報社記者及總編輯。
梁羽生—七劍
黃惟群(以下簡稱黃):梁先生此前一定看過徐克導演的其他電影,不知印象如何?
梁羽生(以下簡稱梁):我知道徐克導演,他也知道我,彼此都不陌生,但直到現在還沒見過面。這幾天通過一個長途電話,他邀我去香港。他的電影拍得非常美。比如《七劍》,看過的人說,拍得非常美。以前我的《白發魔女傳》是張國榮和林青霞演的,在巴黎科幻國際電影節中獲冠軍大獎。《七劍》要比它拍得更美,有天山雪景等等。我對他的藝術感有信心。他的電影給我的印象是很放得開,有人說他天馬行空。這也是一種藝術。
黃:《七劍下天山》被很多評論家認為是東方的《牛虻》,梁先生對此怎么看?你在創作《七劍下天山》時是否一定程度上受十九世紀歐洲文藝思潮的影響?
梁:我寫《七劍下天山》,是五十年代中期,那時風靡中國的小說有兩本,一本是《牛虻》,一本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鋼鐵》是受《牛虻》影響產生的,有人說它是《牛虻》的蘇聯版本。這兩本書對我都有影響。當時一個世界級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寫過《約翰·克利斯多夫》,我的《云海玉弓緣》里憤世嫉俗的金世遺,就是受《約翰》的影響,寧肯冒犯社會和社會鬧翻,也要堅持自己的精神自由。羅曼·羅蘭當時已七十多歲,看到《鋼鐵》后,親自寫信給奧斯特洛夫斯基,感謝這個年輕作家,寫出了這樣鼓勵提高人精神世界的小說。我當時想,我的武俠小說要用新的世界觀、價值觀、史學觀來寫。我想嘗試寫一部中國的《牛虻》,或說東方的《牛虻》。但怎樣中西融合?東方和西方很不同。比如在外國,宗教權力常常高過政治權力,中國的宗教權力怎么都不能跟皇帝比。總之,既要引進西方的,又要符合中國國情。這個話題詳細講的話太長,但有一點很重要:我的《七劍下天山》里,不單有西方文化的影響的東西,也有純粹中國的東西。
黃:有評論認為徐克這次拍的《七劍》過于暴力,打斗場面過于血腥,梁先生覺得是否與原著的名士風度有異?
梁:暴力場面那是他們的創作。我的小說沒有暴力。電影我沒看過。假定他需要的話,是可以的。徐克確實很有才氣。我感覺,一個作品,如果內涵比較豐富,那就看作者用哪部分作為切入點,強調重視哪部分。有一點一定要重視:小說要尊重作者,(電影的話)作者要尊重導演。
梁羽生—金庸
黃:梁先生曾化名“佟碩之”寫過《金庸梁羽生合論》,其中提到金庸后期武技越寫越怪,有神怪之嫌。而十多年來武俠電影動輒拍到武林高手飛來飛去,出手如電光雷嘯,脫離現實,是否正是受到這種武技描寫過于離奇的影響?梁先生心目中合適的武斗場面是怎樣的?
梁:我個人不想這樣寫。可能我也犯過這種“離奇”的毛病。但我的作品中“離奇”不是主流,不是我的風格。這問題要探討的話,那就牽涉到怎么看待魔幻小說,怎么看待《哈利·波特》。關于武斗場面,我倒覺得金庸有一段,胡斐與苗人鳳的武斗場面,寫得很好。我對我自己滿意的是《白發魔女傳》里寫武當五老的那些。要讓人發揮,百花齊放,有各種形式,不能我喜歡這,別人就不能喜歡那,這不行那不行的話,梁羽生就成罪人了。但講多元化,也不能全都飛來飛去。我只代表我自己。羅孚叫我寫《金庸梁羽生合論》時,我還是比較正統的觀念,我認為自己基本沒錯。我已是最溫和的了。當時的高層還認為我對金庸評價過高。盡管有些字是不是用得厲害了些過火了些,可以商榷,但我并沒貶低金庸。
黃:如果今日再寫《金庸梁羽生合論》,你對兩人之間的認識,會有什么補充,什么不同?
梁:再寫是不可能了。以前我們很近,如今環境不同了,大家也都不寫武俠小說。我們的友情是過去的,盡管不滅。他是國士,我是隱士。他奔走海峽兩岸,我為他祝賀,但我不是這塊材料。當年青島市市長請弘一法師(李叔同)赴宴,應邀的有社會各界名流。弘一法師沒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國士筵中甚不宜。很多事就是這樣,換個環境再做,就不適宜了。
黃:你怎么看待人性?
梁:人性當然是復雜的。我以前的論點是有善有惡,現在是可善可惡。但我還是覺得從一個人的善惡重點來說,是有區別的。我離開中國這么多年,現居澳洲。澳洲講多元文化。我的想法也可以轉變。就像我說過的,“凡說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為金庸是經常變動的,有五十年代的金庸,有六十年代的金庸,有八十年代的金庸,也有現在的金庸。
黃:梁先生一直覺得傳統文化中,人物的塑造是有大正大邪之分的,但如今正邪混合的人物在武俠世界大行其道,你對此如何看待?
梁:表現人性的復雜可以。各個作家可以不同。現在韓劇大行其道。韓劇是重視中國文化道德的,盡管人性復雜,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但正邪還是有分別。比如《大長今》里面的崔尚宮、今英,是反面人物,是邪的,盡管她們有好的一面,觀眾還是能清楚地“認定”哪個是正哪個是邪。崔尚宮老要害大長今,但大長今還是以德報怨,表現了中國的傳統,令我很感慨。看韓劇,感受最深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到了韓國;欣慰的是,這樣的傳統道德觀念在今天,實際是受歡迎的。以前有一股風潮,喜歡正邪不分。并不是說這沒藝術性沒現實性,但成為主流,是否也要考慮副作用?也許,那樣可以賣座,有商業價值。現在講理想講俠氣講精神文明,都好像是傻瓜,是怪物,被嗤之以鼻。這種現象,我個人是感覺到可怕的,甚至悲哀的。盡管我不反對。
梁羽生—江湖
黃:你說過“寧可無武,不可無俠”,這話很經典。你能不能具體解釋一下什么是“俠”?
梁:俠是一種精神,武是手段,武是用來達到俠的,是次要的。俠才是目的。什么叫做俠?俠有很多不同定義,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俠:青洪幫自稱俠門,講哥們義氣,也是俠……我個人的看法是:對大多數人有利的行為就是俠義行為。
黃:你寫了這么多江湖故事,能不能談談什么是江湖?
梁:有人說“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話說得俏皮,但還是沒說明什么是江湖,亦即是沒從本質上來分析江湖。江湖是“動態”,如果“一潭死水”,那就不能稱江湖。“浪蕩江湖”、“行走江湖”、“重出江湖”,從這些常見的武俠小說俗語來看,也可見其動態。所以簡單來說,江湖者即有風波的地方。若以哲理性的語言來講,江湖者,“眾生擾攘的俗世也”。
黃:作為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你對梁、金封筆,古龍逝世后的新派武俠小說現狀、格局、發展有何看法?
梁:武俠小說不會就此死亡,將來成什么樣子,很難估計。比如加上科幻,和科幻結合起來,是否可以?我想是可能的。科學發展很快,人們的了解認識也發展很快。
(童湘屏摘自“網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