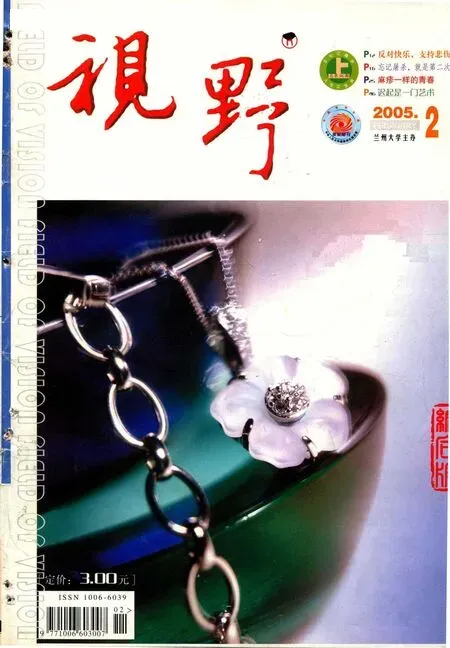窗口之光
邦達列夫
正月間,風雪交加,巷內的白楊樹凍得吱吱直叫,來自上游的勁風把房頂上的鐵皮吹得隆隆亂響;房檐上的雪粉不斷被風卷落下來,然后順著白皚皚的柵欄,圍繞一個個新的雪堆,飄來舞去。而它,在夜幕中間惟一發亮的這個窗口,透射出恬適的綠色光亮,用窗簾遮掩著,總是那么明亮、溫暖,總是那么引人注目,并且使人產生一種困倦和神秘莫測之感。
每天晚上,固定不變地在巷內迎接我的,就是小木房里的這個令人愉快的家庭小燈標,就是這個用窗簾遮掩著的臺燈的光亮——我這時想像得出,一座爐火正旺、散發著木柴氣味的小木房,里面靠墻擺滿了舊書架,一塊破舊地毯鋪在沙發前的地板上,有一張寫字臺,玻璃燈罩在昏暗中擴散著光環,那里有一個人,靜靜地,微駝著背,面帶老年人的慈祥皺紋,孤獨地生活在書籍的極樂天地里。他無求于世,也不向往世俗歡樂,時而用手指愛撫地翻動書頁,時而在室內寂靜之中蹣跚地踱來踱去,常常伏案思考和工作到深夜。可是,他究竟是誰呢——是學者?是作家?是誰?
有—次,在去年春天,我望著那個陌生的、神秘的、不眠的窗口,望著那個在室內燈光照耀下似乎永遠呈現溫暖綠色的窗簾,突然產生—種完全不可抑制的感情。我很想走過去,敲敲窗戶的玻璃,看看窗簾被掀開時的輕微擺動和他那慈祥的面孔(我想像那面孔是白白的,稍微瞇縫著的眼睛周圍刻有網狀皺紋),看看堆滿了紙張的桌子、塞滿了書籍的小房間和地板上的舊地毯……我想對他說,我大概是弄錯了門牌號碼,怎么也找不到我要找的住家——這樣簡單地撒個謊,為的是哪怕匆匆瞧一眼他那個十分整潔的生活和工作場所的迷人而寧靜的氣氛,他的周圍全是書,書籍好像就是他惟一的忠實朋友。
但是,我沒有下定決心,沒有去敲窗戶,后來我一直不能原諒自己這一點。
兩個月過去了,世界上什么都沒有改變。是的,一切依然如故。而在靜靜的小巷里已經充滿春色。這時,我看見一只小金蟲使勁兒地嗡嗡叫著,開始從暗處慢慢飛來。它撞到了路燈的玻璃罩上,堅硬的甲殼掉落在人行道上,動彈不得。后來又大為驚慌地活動起小爪爪,試圖翻過身來。我這時用鞋尖幫了它一下,不知為何對它說:“你怎么啦?”它順著人行道向一座房屋的墻壁、向一條排水管(離窗口三步遠)爬去。就在這時,我感到了一種沉重的不安,一種意外的空虛從五月黃昏的深藍色中出現在我的面前。
小房子的窗口沒有亮,它變得一片黑暗,像地陷了一樣……
發生了什么事?
我走到小巷盡頭,在拐角佇立了20分鐘,然后又轉身而回,因為還想看看那看慣了的窗口之光。但那窗口卻黑著,玻璃反射出晦暗的微光,窗簾一動也不動,不再像往常晚間那樣發出令人喜愛的綠光。頃刻之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令人毫無舒適之感,這表明:在那里,在那間看不見的小房里,發生了不幸。
我懷著愈益強烈的不安心情,再次來到拐角處,就地抽了兩支煙,接著又不由自主地急忙轉回,再次來到巷內。我暗自說,現在或者再過幾分鐘,那個窗簾上就會突然出現綠色的光亮,小巷內將一切如故,將平安無事……
窗口之光沒有亮。
第二天,黃昏剛臨,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幾乎是跑步來到這鄰近的小巷。這時,這里出現的意外新情況使我大吃一驚。窗戶敞開著,窗簾拉開了,房間的內部、書架和某種地圖都露了出來——所有這一切,我都是初次看到,盡管我曾不止一次想像過這位好在晚間工作的陌生的朋友。
一個相貌像男人、發式也像男人的漸近老境的女人,站在寫字臺旁,抽著煙,用疲倦的眼光瞧著房間里的空地方。
恰在這時,她忽然發現了我,馬上氣呼呼地拉上了窗簾——接著,臺燈亮了,又像往常那樣出現了一小片淡綠色光亮。而我卻不禁覺得毛骨悚然,有一種可怕的空虛感頓時襲入了心房。房子也好,小巷也好,窗口之光也好,對我來說,一下子都成了昏暗的、虛幻的、陌生的東西。
我這時明白了,是發生了不幸。我想像中的朋友,那位走路時腳下發出悅耳的沙沙聲的白發孤身老人,那位書籍愛好家和哲學家,每晚窗口發亮時都如此吸引我、如此令我心醉神往的那個人,不可能是剛才看見的站在寫字臺旁的那個生有一副陰郁的男人相貌的女人。在悟出這一真相的最初時刻,我覺得自己如墮五里云霧中,感到一種失去親人的悲傷,仿佛剛剛收殮了一位故交,收殮了一位如此有自知之明、有創造力、與我最親近和心神相通的朋友,我雖然與他素不相識,從未見過面,但我終生都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