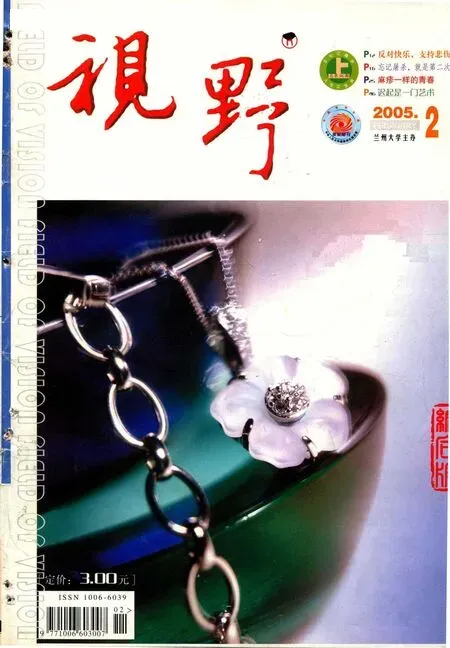那天,我真想放下教鞭
派垂克
今天件件事都晦氣,教室里的30個一年級學生在椅子上坐不定,整天不肯安靜。閱讀課令我失望,沒有一點兒進步,實際上,是退步了。上午時分,校長把我叫去:原來我忘記交上一份重要的報告。想起來,仿佛是把它丟了。兩節游藝課,運動場上灼熱了,刮著風,吹起許多沙子塵埃。下課前,我僅有的一雙尼龍襪被鉤破了。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然而,晦氣接踵而來。最后一堂的下課鈴響時,只見瓊斯太太哭哭啼啼地闖進課室,她的瑪麗因生病已缺了40天課,所以成績不好。我盡量耐住性子,婉言安慰她。
下午4點,我巴不得回家泡在浴缸里舒坦一下。但今天是區里一年級教師今年最后的一次集會。主講人是從外地請來的一位著名教育家。她說,教育的新時代即將來臨,我們必須本著專業精神做準備。過了5點,她的話還未講完。她越說下去,我的專業精神越消沉。她似乎說穿了我這位老師所有的缺點。
散會后,跑進雜貨店,高價買了面包、牛乳和熟肉,奔回家。我有兩個10歲的兒子,一個8歲的女兒,家里亂七八糟。把買來的東西放在桌上讓孩子吃,自己拿了個蘋果,鉆進汽車,和丈夫急駛到50里外的安馬里魯去。
今晚我們又當學生了。我們每星期到安馬里魯聽一堂課,教育局現在指定我們要進修碩士學位。
我疲憊不堪,不想說話,倒在汽車里閉上眼睛,想著今天的經過。越想越氣,不禁心生一念:干脆不教書了!
在安馬里魯的班上,懶洋洋地倒在座位上,講師說什么都沒有去聽。何必聽?我不教書了。
講師滔滔不絕地講下去。15分鐘的小息時間終于到來。鄰座一個熟識的婦人欠身對我說:“前幾天我遇到一個欽佩你的人。”
我筆直地坐起來,不再困倦了。心中思忖:是不是什么早已淡忘了的男朋友還在想我?我客氣地輕輕說了一聲“哦”,希望沒露出好奇神色。
我聚精會神地聽她繼續說下去:“上星期我在公共汽車站等我兒子,看見一個墨西哥女人和她的小女孩。做母親的不會說英語,我和那女孩聊起來。她說她們要到柯羅拉多去,她父親已經在那里。又說她在念二年級,還把她老師的名字告訴了我。”
“接著,從袋里掏出一個舊皮夾子,抽出一張照片說‘我真愛這位老師。我認出那是你的照片,十分詫異。照片已經褪色,破破爛爛的。”
“我說我認識你,她便轉告她媽,母女兩人都很興奮,仿佛要吻我的樣子。”
我聽了,想起去年教過的拉丁美洲學生。我問:“她是不是名叫裘利亞?不是?可能是阿達林娜?”
婦人說:“對,她叫阿達林娜。”
是阿達林娜,我真高興。她父母剛從墨西哥到美國來,兩人都不會說英語,但笑口常開,把他們的獨女視同掌上明珠。
去年11月下旬,他們帶阿達林娜到我的教室來。阿達林娜垂下頭,神色慌慌張張,穿著整潔而漿得挺直的衣裳,不合身,顯然是一個較大孩子的舊衣服。小個子,干干凈凈,很逗人喜歡。她跟同學很合得來。不久,那慌張的神色消失了,總是笑瞇瞇的,喜悅的臉色贏得了班里每個人的友誼。
她天資聰穎,過了幾個月,便離開了學校。如今我常常掛念著她。
我感謝那位相熟的婦人,很想告訴她,她的故事給我打了氣。我當時說不出自己的感受,寫下來比講出來容易。也許有一天她會看到這篇文字,便會知道當時我想對她說的話了。
回程中,我靜靜思量,有了另一個決定:“決不放棄教書生涯!”
我又有信心,又起勁了。我要替我的閱讀課另外想個辦法,我要改變對瓊斯太太的態度,上床之前定要找到校長要的那份鬼報告。我教書,也許談不上什么專業精神,但每天盡心工作,就是賞心樂事。
將來年老不再教孩子念書時,想到阿達林娜的小臉,她那么天真地把我的照片拿給公共汽車站的一個陌生人看,我的心頭會永遠感到溫暖。
不教書嗎?不教書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