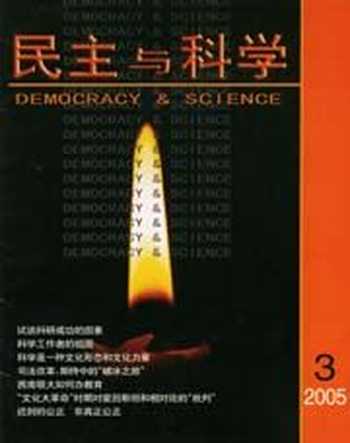作為法律人的費孝通
支振鋒
費先生的學術理論影響和成就,以及他以其終生的學術實踐所展示的對于這個民族的愛,都在對法學的成長、改造發(fā)生著重大且深刻的影響。
——著名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教授朱蘇力
朵朵白花,點點哀思。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靜靜地走完了他95年的漫漫人生。費老的不凡之處在于,他既是一位具有國際盛譽的社會人類學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社會活動家。然而,社會學家與社會活動家的光環(huán)卻掩蓋了他同樣杰出的法律思想。事實上,他也完全可以稱得上一位杰出的法律人。翻開一頁頁費老留下的文字,感嘆著思想相較于人生的悠遠,我們也謹以我們的文字,寄托我們對于費老的緬懷與敬意。
重新閱讀費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我發(fā)現(xiàn)了理解中國法律制度的一系列關鍵,包括理解中國當代社會和法律變革的關鍵。我力求以費先生為榜樣從不起眼的細節(jié)人手,用平實的語言和嚴格的分析,去開掘出當代中國社會的法律變革中一系列問題。
人窮了便會被看不起,羸弱了便會被欺侮。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整整做了一百多年羸弱窮人。怎么才能擺脫別人的白眼與欺侮呢?蔣介石、宋美齡倒是費了不少心思。于是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發(fā)起了一場“新生活運動”,號稱要“改造社會、復興國家”。這場活動聲勢浩大,席卷全國,其效果如何呢?中國近代外交家顧維鈞的第三任妻子黃蕙蘭在其回憶錄中說,中國駐外人員常有外遇而導致婚變,故在抗戰(zhàn)前外交界即戲稱新生活運動為“新妻子運動”。然而,更富有戲劇性的情節(jié)則發(fā)生在“鄉(xiāng)下人”身上,沈從文的未竟長篇《長河》將之描述得活靈活現(xiàn):
劃船的進城被女學生罰站,因為他走路“不講規(guī)矩”,可他實在不知“什么是規(guī)矩”,或者說“這到底是什么規(guī)矩”,只好站在商貨鋪門口,看著掛在半空中的臘肉臘魚口饞心饞。
所以,鄉(xiāng)下人便說:“我以為這事在鄉(xiāng)下辦不通。”
鄉(xiāng)紳接過話頭:“自然嘍,城里人想起的事情,有幾件鄉(xiāng)下人辦得通?”
其實,沈從文并沒有寫得這么集中,這個故事是許章潤教授根據(jù)原著輯集的。先生慧眼識珠,片言碎語里看出了袖里乾坤、微言大義:外在的規(guī)則如何能夠真正地約束人世生活,進而成為人們心中的信守?特別是對于那些平時只見得老牛斜陽、柳樹炊煙的“鄉(xiāng)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我只管老老實實地生活,即是天王老子又能奈我何?
于是,“鄉(xiāng)下人問題”就成了近世中國變革的經(jīng)典命題。毛澤東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十年之后的1935年,又有一顆灼熱的靈魂將目光投向了農村。他就是一代巨匠費孝通。欲研究中國法律,必先研究中國社會,他的理論在60年之后,又啟發(fā)了朱蘇力等中國杰出的法學家。
費孝通的貢獻絕不僅僅限于社會人類學。他對鄉(xiāng)土社會的權威與秩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參與了新中國憲法的起草工作。費孝通的博土生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是當時世界人類學家之領袖,其著作除《文化論》外最為重要的就是《原始人的犯罪與習俗》,然而這是一本奠基性的法律人類學著作。費孝通真正體會到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的整體性。這是費孝通關于文化問題的學術思想的發(fā)展,同時為他從靜態(tài)的“文化功能論”轉向動態(tài)的“文化變遷論”打通了關節(jié)。
費老的60年學術實踐已經(jīng)告訴我們,人類學家并不只是研究異族文化的專家,對于本土社會即使是工業(yè)化的本土社會,他們的研究與那些著名經(jīng)濟學家的研究一樣有價值。如果我們再往前推進一步,他們的研究何嘗不是經(jīng)典的法學著作呢?
一百余年來,以“五四”精神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法律與社會精英們,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從器物到制度到價值觀的種種方面進行了無情的肅清。在法律思想上,他們對西方法律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深信不已,堅持認為中國法律的出路是進行以“西方法律”為藍本的現(xiàn)代化,否認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tǒng)中具有可資借鑒的法律資源。20、21兩個世紀之交,他們又有了新的理論基礎:市場經(jīng)濟具有共同規(guī)律,西方發(fā)達市場經(jīng)濟的現(xiàn)在就是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未來,因此西方現(xiàn)有法律完全可以為我所用;相信人類理性有預測未來的能力,因此要大膽進行超前立法。正如有論者言,這是一種不加反思、不加質疑、不僅激進而且樂觀的論斷。然而,是不是鄉(xiāng)下人進城就完事了呢?實際上,中國的法律“現(xiàn)代化”某種意義上不就是“鄉(xiāng)下的”中國人進作為“城里人”的西方之“城”嗎?
費孝通對中西法學的看法不是單一的:一方面,他認為西洋在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劃分了界限,把國家弄成一個為每個分子謀利益的機構,于是有憲法、法治,而中國傳統(tǒng)里只有克己,沒有對群、對皇帝的界限劃定和權力制約。但另一方面,傳統(tǒng)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秩序的維持,有很多方面和現(xiàn)代社會的維持是不相同的。所不同的并不是說鄉(xiāng)土社會是“無法五天”,或者“無需規(guī)律”。假如我們把法律限于以國家權力所維持的規(guī)則,我們可以說這是個“無法”的社會;但是“無法”并不影響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秩序,因為鄉(xiāng)土社會是“禮治社會”。法治和禮治是發(fā)生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情態(tài)中。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tǒng)規(guī)則的服膺。這種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禮治是每個人都自動地守規(guī)矩,不必有外在的監(jiān)督。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社會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么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xiāng),結果,法治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fā)生了。
實際上,費孝通早在1947年便指出,“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xiāng)土性的”,“那些被稱為土頭土腦的鄉(xiāng)下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鄉(xiāng)土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陌生人所組成的現(xiàn)代社會是無法用鄉(xiāng)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在鄉(xiāng)土社會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會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權威、教化以及鄉(xiāng)民對社區(qū)中規(guī)矩的熟悉和他們服膺于傳統(tǒng)的習慣來保證。在費老《鄉(xiāng)土中國》一書中那些諸如“差序格局”、“維系著私人的道德”、“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等等,這些不正是一本法學著作所應討論的對象嗎?朱蘇力便承認,費老的著作為其提供了無盡的思想、知識與方法論資源。朱蘇力在法學界提出了著名的法律本土化的觀點:“尋求本土資源,注重本國的傳統(tǒng),往往容易被理解為從歷史中尋找,特別是從歷史典籍規(guī)章中去尋找。這種資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尋找。研究歷史只是借助本土資源的一種方式。但本土資源并非只是存在于歷史中,當代人的社會實踐中已經(jīng)形成或正在萌芽發(fā)展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資源。”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費孝通的“鄉(xiāng)土社會”仍是一個認識和了解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及變遷的有力分析工具。秋菊辛辛苦苦不斷上訪,要個“說法兒”,但她甚至得不到自己丈夫的支持,而最后法律終于給她“說法兒”的時候,站在滿是灰塵的大路上她卻更為迷惑了,因為法律給的并不是她所想要的。當善良公正的山杠爺被“大蓋帽”帶走時,也給鄉(xiāng)親們留下了無盡的疑惑與煩惱,因為他們不理解。于是,有人說了,這正體現(xiàn)了普法與法治的重要性,然而如果一種法律其規(guī)則不能為人們所理解與體認,它怎能贏得人們心中的信守,從而在社會扎根呢?是法律要適應社會,還是社會要迎合法律?如何解決秋菊們與山杠爺們的困惑?費孝通的努力,或許可以解釋這些煩惱,也許還可以消除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