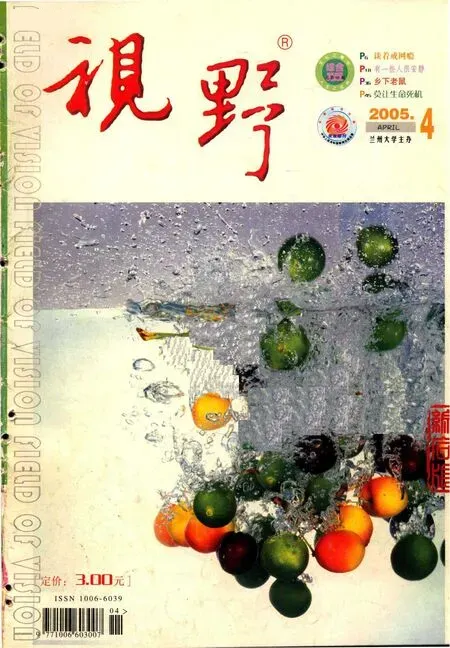物非人非
伍曉亮
真想回到從前,但事實不能倒帶重放。
人在高四,總有那么一點言不由衷,明明覺得事情應該這樣,而結果卻往往相反。無疑,我們會遇到成長的煩惱,這需要時間,一切,只有走下去才算數。
桌子是我悲慘命運的見證,它那斑駁的傷疤,懷舊的顏色,我不忍去看,于是鋪上了一層讓我難以忘懷的報紙。那可憐的報紙也依然變得“斑駁”,或者說是“光怪陸離”,已經被蹂躪得滿臉開花。可是我卻不想換掉它,因為它確實是一份真實的記錄,記錄著我的榮辱,記載著我辛勤的汗水和失意苦澀的淚滴:
“苦苦苦有盡,不苦苦無窮。”
“每一條走過來的路都有不得不這樣跋涉的理由,每一條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這樣選擇的方向。”
“我們總是懷念過去,總有一天,我們也會懷念今天,正如我們懷念逝去的一天。”
……
我倉皇地抄下寫在它身上的字句,生怕它們逃了,逃到很遠的遠方,就像我的大學一樣,是那么清晰而又遙不可及。
今晚,作最后一次守候,明天,它就要over了。因為月考又過去了,又要排座位了,它的新主人絕不愿看到它的,他(她)會毫不猶豫地把它撕破,然后惡狠狠地摔在地板上。于是,我提前給它作個悼念,否則,我會心疼。
別了,我的報紙。
對任何事,我總是保持一種藍調,但不快樂的成分很少。只是那種固有的淡漠,讓我把一切表現得那么純粹而又真實,真實得可怕,這造就了我的漫不經心。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悄悄地流淚,默默地嘆息,也有甜甜的微笑,對高四,對大學。
陳奕迅唱《十年》,唱得驚心動魄,唱得我止不住清淚漣漣。那豈止是十年?人生中最寶貴的十年用來邂逅和解除邂逅,還有什么比這更凄慘的呢?物非物,人非人。
如果一個手指代表十年,那么我雙手緊握著十個這樣的璀璨年華,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一個而且即將又有一個不屬于我,剩下八個更加艱難、平穩地滑動,而我又不可能將它們一個個認真地數過。我仔仔細細對比著紋絡的繁雜程度,以便預測以后的道路是曲折還是通途。一條條手紋螺旋盤繞,我的手指,我的生活……
“人生思幼日”,誰都有重溫童夢的瞬間,那騎在父親肩頭的日子,那毫無憂慮毫無顧忌的童言稚語,那校園小道上的漫步……
回來吧!我的童年,你回來呀!
歲月變遷,時光飛逝,不知當初怎么想的,奮不顧身地逃到這荒涼的運城北郊,來默守孤獨。有時,我會看著大街上一輛輛飛馳的跑車,它們像極了我們的匆匆步履,帶走高四的一天又一天。
忽然間,想起我悲切的高中生活。面對高考這只貓,我只是一只小老鼠,一只膽小而懦弱的鼠,它一點一點地把我的勇氣抹掉,最后,連我一起吞下去。
在別人為自己的前途精心裝潢時,我卻把道路鬧得千瘡百孔,然后,再用一年的時間去修補,這洞能補得那么精美嗎?我有很好的朋友,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不得已又成為尖銳的朋友。再有一個老師那樣“寵”著自己,該是怎樣幸福的回憶呢?哪怕是無意間的一句話,甚至是批評。
水手在講臺上講一些讓我無法聽懂的句子,為了鍛煉我的耐力,我努力強迫自己去聽,努力地從腦海中拉出所有的與其相關的字母,但都無濟于事,最終我以失敗告終,我只好將夢中的主人公拉出來對話。我又開始討厭人類,為什么總是那么世故,人心可當光滑平面來使用。原來臉蛋有屏蔽作用,它遮住了真正神圣的面孔,這面孔就是思想,它天生就是演員,狠狠地抓住了話語權。而我,還是單純幼稚的生命,我很難適應啊!我傷心地將本來一會就可以忘記的晦氣的話寫下來,它們像雕塑一樣清晰和確鑿,抹也抹不掉。
蒼蠅以為自己是夜鶯,聲音婉轉動聽,卻不知自己頂著個惡心的綠帽子橫沖直撞,為所欲為地停留在任何可能的角落,沾沾自喜地好像在向人類宣戰:“你們就是拿我沒辦法。”這種行為是多么令人作嘔!
我討厭后悔,甚至討厭一丁點的不滿情緒在臉上蕩漾,因為這樣不會讓我笑,而我是愛笑的孩子呀!
有些東西是要寫出來的,而不僅僅是說能表達的,必要時還得配上特制的音調,這樣就可以有更堅強的確證,不像潑出的水那樣了無印跡。我瀟灑地簽上名字,作為對高四生活的一種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