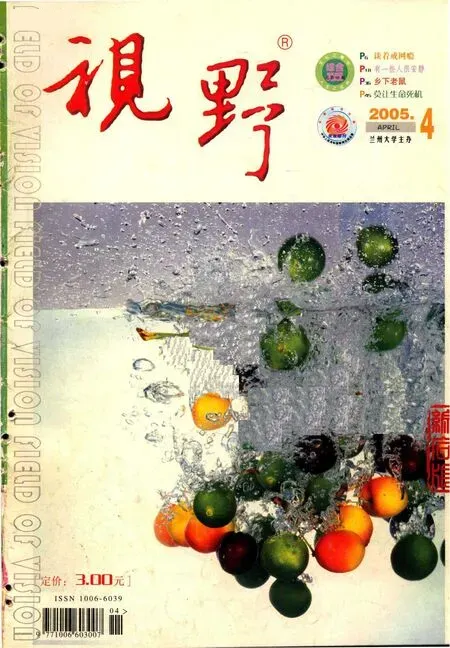漢娜的手提箱
丁 林
漢娜的故事是從一只手提箱開始的,開始在日本東京。
東京,一排簡樸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幾間門面,上額的開首是一個六角星的圖案,接著是一行并不大的字:東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資料中心。六角星是猶太人的標志;英語的“浩劫”(holocaust)在歷史上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專指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這幾間房子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民間非營利組織,其宗旨是讓日本孩子了解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浩劫。
博物館的對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關的實物,可是日本本土沒有浩劫文物。歐美的浩劫博物館雖然藏品豐富,可是他們不會冒這樣的風險,將珍貴歷史文物外借給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物館。史子還是決心試一試。結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禮貌的謝絕信。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蘭旅行。當年納粹設置的猶太人集中營,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氣室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死亡營——奧斯威辛集中營。
史子去了奧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館負責人助理,懇切地陳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兒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請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動,答應考慮。幾個月后,2000年初,史子真的收到一個來自奧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小罐納粹在奧斯威辛用于屠殺的毒氣,其他都是兒童囚徒遺留在那里的東西:一只小小的襪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手提箱深色的箱面上,用粗粗的白漆寫著“625”的編號和漢娜·布蘭迪的名字,還有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觸目的大字:Waisen Kind(德語:孤兒)。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標有姓名的物品。
史子組織了一個孩子們自己的小團體——“小翅膀”。他們定期活動,出版他們的報紙,擴展浩劫歷史的教育。“小翅膀”們圍著手提箱,提出一堆問題:這只手提箱的主人漢娜,她是誰?漢娜活下來了沒有?史子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了解漢娜的情況。但是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一封短信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里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堅實信息。她開始尋找資料。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里津(Terexin),1800年為關押囚犯而建。“二戰”期間,曾經有14萬猶太人在這里住過,其中包括15000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在特里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里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做心理疏導。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最后,史子讀到,在特里津,居然有4500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被奇跡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里也有漢娜的畫?她給特里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幾個星期之后,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里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里,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從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炭筆畫。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著:漢娜·布蘭迪。
特里津,這是惟一可能揭開漢娜手提箱之謎的地方。機會終于來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終于抵達特里津鎮。
她按照索引,找出了漢娜·布蘭迪的姓名和生日。她發現在漢娜的名字上面,是另一個和漢娜同姓的名字:喬治·布蘭迪。他會不會是漢娜的家人?因為納粹做的名單經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還發現,名單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個折鉤的記號,有的名字卻沒有。有折鉤的,都沒能幸存下來。史子看了一下漢娜的名字,有一個折鉤。這不是一個太大的意外,但是,她還是很難過。而喬治·布蘭迪的名字旁,沒有這個死亡折鉤。
漢娜可能有個哥哥,她的哥哥可能還活著!幾經周折,史子終于查到:喬治·布蘭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多倫多。
2000年8月,72歲的布蘭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他打開信,“親愛的布蘭迪先生……請原諒我的信可能給您帶來傷害,提起您對過去艱難經歷的回憶……”他一陣眩暈。從信封里他抽出幾張照片,那是小漢娜的畫,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漢娜的手提箱。
一個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終于從多倫多來到東京。她在辦公室打開信封,止不住激動地叫起來。那是個多美麗的女孩。她手里是漢娜的照片。她開始哭起來。她終于喚出了漢娜,一個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紀30年代,漢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個美麗小鎮。漢娜和哥哥是鎮上僅有的猶太孩子。可是,他們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有許多朋友,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父母熱愛藝術,為謀生開著一家小商店。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1939年3月15日,德軍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國土。漢娜一家的生活永遠地被改變了。和所有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先是必須申報所有的財產。后來,他們不得進入電影院,不得進入任何運動或娛樂場所,接著,漢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年,漢娜要開始讀三年級的時候,猶太孩子被禁止上學。漢娜傷心的是:她永遠也當不成教師了,那曾經是她最大的夢想。那年3月,蓋世太保命令漢娜的母親去報到,她再也沒有回來。秋天,外面傳來一陣粗暴的砸門聲,他們的父親也被納粹抓走了。留下漢娜10歲,喬治13歲。
他們被好心的姑父領到自己家里。1942年5月,納粹一紙通知,限令兄妹倆報到。隨后,他們被送入了特里西恩施塔特猶太人集中居住區。臨走前,他們回到自己的家。漢娜從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這個故事的手提箱。漢娜和哥哥提著各自的箱子離開家,先坐火車,又提著它吃力地步行,從火車站走到集中居住區。就在門口登記的時候,納粹士兵在這個箱蓋上寫下了漢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沒有父母隨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釋:“孤兒。”
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漢娜被迫和哥哥分開居住。但他們還能夠找機會見面。在居住區的三年里,漢娜和哥哥看到他們年老的祖母也從布拉格被抓來,又很快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納粹德國已經接近崩潰。他們開始加速將居住區的猶太人向死亡營轉送。先是喬治被送走。13歲的漢娜突然失去相依為命的哥哥,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點聯系。終于,漢娜也接到了被轉送的通知。她行裝簡單,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幾件衣服,她自己畫的、最喜歡的一張畫,還有居住區小朋友送給她的一本故事書。她什么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線希望:也許,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喬治;也許,還能在那里和爸爸媽媽團聚。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漢娜和許多猶太人在一陣陣吆喝聲中,直接被送進毒氣室。喬治正關押在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媽媽,1942年,漢娜的父母卡瑞爾和瑪柯塔,也在這里被殺害。這是波蘭。這里,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
2001年3月的東京,史子和她的孩子們,終于盼來了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他還帶來了自己的女兒、17歲的拉拉·漢娜。在半個多世紀后的日本,他重新見到了妹妹漢娜的特殊遺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頭,傷心地哭了。可是,幾分鐘后,他恢復了平靜。他覺得,妹妹漢娜的愿望實現了——她終于成為一個教師,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喬治,漢娜的哥哥,作為一個浩劫幸存者,他戰后的經歷,也在對今天的日本孩子表達著什么。他告訴他們,這么多年,他去過很多地方,他始終帶著他最為珍貴的家庭相冊,那是姑姑、姑父為他保存下來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訴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雖然經歷一切,卻能夠讓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喬治告訴日本的孩子,對他來說,他從苦難經歷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價值是:寬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這也是漢娜要告訴大家的。也許,能夠將極端負面的教訓,轉化為正面的生活價值,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至2003年5月,史子組織的展覽巡回在日本的六個地方展出,參觀者超過六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