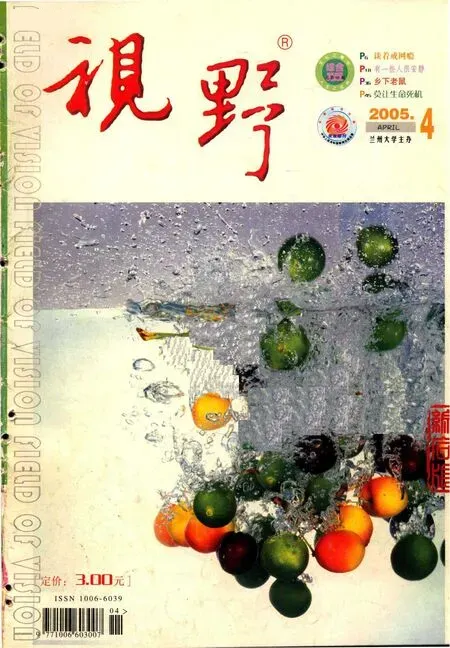暢銷50年的“憂愁”
曾 焱
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的青春也是貼了標識的:牛仔褲、披頭士、塞林格的守望,還有薩岡的憂愁。
你的薩岡
“這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以煩惱而又甘甜的滋味在我心頭縈繞,對于它,我猶豫不決,不知冠以‘憂愁這個莊重而優美的名字是否合適。”1954年,以這經典開頭叩開文壇的時候,薩岡只有18歲。她完全預想不到,自己的賭氣之作會在幾個月后帶來84萬冊的銷售記錄,而且幾十年后仍然不曾有人逾越。
一個膽大妄為的女孩,寫了一本“不道德的小說”,這是評論家對它的第一觀感,但卻令人無法釋手。當時為《世界報》擔當文學版專欄作家的是法蘭西學院院士艾米爾·昂里奧,老先生在自己的評論文章里毫無保留地說出了對這本小說的迷戀:放在一邊,又拿到手中,讀了又讀,“看完這本書,一切都顯得淡然乏味了”。著名作家莫里亞克屬于持批評意見的一派,他反對將齊名龔古爾文學獎的批評獎授予薩岡,并且連她的名字也不屑說,代之以“那個18歲的明星”。隨后這位大作家在《費加羅雜志》上發表了對這本小說的專題評論,同樣連作者名和書名都沒有點出,不過他在文中還是承認,小姑娘“以最簡單的語言把握了青春生活的一切”。獲獎,以及莫里亞克的批評,都拉升了銷售。出版社開印4500冊,之后不斷加印,三個月后賣到10萬冊,很快突破20萬冊,等到年底的時候已經超過80萬冊了。一本純文學讀物,成了“二戰”之后法國最暢銷的書籍,1954年度最受歡迎的法國制造。薩岡成了千萬富翁。24年后,薩岡回憶這本書出版那一天的情形,依然很清晰:“第一批樣書到的時候,我是在朋友那里看到的。我把書都藏起來了,覺得好像所有人都會來問我,這書是你寫的嗎?”
如果說小說具備了一場悲劇的所有要素,那么薩岡便具備了暢銷和變身名流的全部潛質——年輕、漂亮、富有才氣,再加上一點離經叛道。她出生于法國南部小鎮一個優裕的大家族,父親是企業主,舉家移居巴黎后生意做大,生活更加奢華。對于薩岡的任性,父親一向聽之任之,給她全部自由。像她這種家境的女孩子,上的都是高級教會學校,可她厭惡那種環境,變得十分反叛。小說里賽西爾的生活,完全可以描述薩岡本人的中學時代:“我認為我那時的大部分快樂都歸功于金錢,坐車快速兜風的快樂,有件新連衣裙的快樂,買唱片、書籍、鮮花的快樂。我現在仍不為這些輕易獲得的快樂而羞恥。再說我稱它們為輕易獲得的快樂,僅僅是因為聽到別人這么說。也許我更容易悔恨,否認我的憂愁和內心的恐慌。不過愛好快樂與幸福代表了我性格中惟一協調的方面……”因為長期曠課,第一所學校將她開除了;第二所學校也無法容忍她的不馴,直到第三所學校出于同情接受她,薩岡才得以完成中學學業。惟一合乎規范的優點是喜歡讀小說和詩歌,視司湯達、蘭波、普魯斯特、紀德和薩特為偶像。寫小說的時候,薩岡已經進入索邦大學文學系預科班,因為在晉升考試中落榜,她決定用寫作來獲得心理平衡,證明自己并非一無是處。小說隨手寫在一冊小學生練習本上,第一個讀者是她的閨中密友弗羅蘭斯·馬爾羅,大作家馬爾羅的女兒。弗羅蘭斯看完后,半夜3點打電話叫醒薩岡,宣布:“你是一個作家!”幾星期后,薩岡拿著于手稿出去自薦,在素不相識的女導演雅克琳娜幫助下,她將手稿同時交給了兩個出版社。最后,其中一家搶先一步對這個小姑娘說了“你好薩岡”,也搶到了滾滾財源。
完情城堡
薩岡盡情享受出名帶給自己的快樂。她用掙來的錢買了一輛二手美洲豹四處飆車,結果一場車禍差點要了她的命。不過這是幾年以后的事了,在1960年以前,薩岡在寫作上一直爆發出巨大能量,以可觀的速度構筑自己的憂愁世界,幾乎是一年一本書:《那么一種微笑》、《一個月后一年后》、《你愛勃拉姆斯嗎》。她的書賣得很好,不愁吃穿,而評論界也依然褒貶各半,有人可能不喜歡她的故事,但不否認她在語言敘述上的簡潔、聰明和從容,已將法語的優美完全表現出來。1960年她轉向戲劇創作,《瑞典城堡》再次大獲成功。但此后寫作狀態漸漸下滑,薩岡將精力部分移情于社交和政治,她先后是蓬皮杜和密特朗兩屆法國總統的座上賓。
至于薩岡自己的感情歷程,就像飆車,每一站都轉瞬即逝。1958年,她和出版人居伊·斯肖萊爾結婚,兩年后離異。1962年,旅居美國時她嫁給了美國畫家羅伯特,但生下一個兒子后也分手了。薩岡最后被媒體關注的一段情感,是和她少女時代的偶像薩特。1978年薩特雙目失明,疾病纏身,薩岡聽說后,寫了那封著名的《給讓-保爾·薩特的情書》在報上發表,傾訴自己對大師的仰慕和愛戀,鼓勵他帶著勇氣生活。薩特請人念了這封信,很感動,他約薩岡見面吃飯,談天說地,以后兩人每十天就單獨見一次面,忘年之戀在圈子里傳為美談。為了讓薩特能隨時隨地聽到自己的“情書”,薩岡用整整三個小時重新朗讀并錄制了那封長信,留給薩特在深夜獨自回味。他們的這段交往直到1980年薩特去世才結束。
薩岡曾評價自己,“我可能不是偉大的作家,但我是出版現象”。一本小說,50年后還有文字來專門紀念它的出版,多少證明這小說的價值。在2000年到來前夕,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戲劇家井上廈有過一次著名的“世紀末對話”,兩人臧否上世紀各個年代影響深遠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事件,被媒體廣為轉載。聊到50年代的時候,大江健三郎說了這么一段:“我認為1953年是非常重要的(指斯大林之死和科學家發現DNA)。第二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石礁進行氫彈爆炸試驗。同年,弗朗索瓦茲·薩岡嶄露文壇。我買的第一本法語書就是她的《你好,憂愁》。與我同年的薩岡在巴黎出版小說的時候,我才剛開始學法語,這令我非常沮喪。”接下來被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提及的同期文化事件,也就只有披頭士樂隊的出現了。雖說是個人記憶,但難以否認,在上世紀50年代,他們的青春也是貼了標識的:牛仔褲、披頭士、塞林格的守望、薩岡的憂愁。對于同代人而言,薩岡就是難忘的年華符號,她和“麥田守望者”塞林格一起略懷憂傷,向成人世界所代表的秩序作了文字的反抗。
幾十年過去,薩岡依然是法國出版界的雙重布景,同時映襯著青春文學和暢銷文學,隔三岔五地被拿出來展示一番。1998年,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私生女兒皮諾特以自傳體小說《第一部小說》闖入文壇,高居暢銷書榜首,媒體書評便將其與薩岡作比較,以顯示她的成功有多么轟動。1999年,法國文壇又冒新人,女作家安娜·加瓦爾達憑一本《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成為出版業的新寵,而她在接受訪問時說,薩岡永遠是自己的偶像。而薩岡,她仍然住在巴黎,多病,不再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