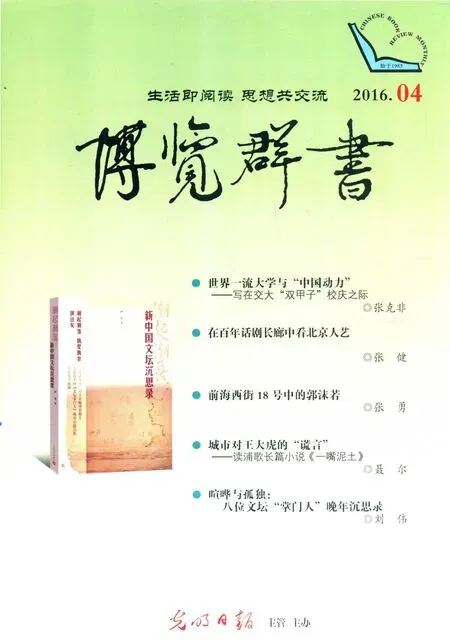余三定《新時期學術發展的回瞻》序
麻天祥
巴陵勝境,俊彩星馳,余君三定居其間矣。其為學也精,碩果累累;為人也和,勝友如云;為官也勉,朝乾夕惕。余以為;高校工作,科研、教學、管理,得其一而致優者,已屬不易,然則余君兼三事于一身,且能運斤成風,于“文藝湘軍”乃至學界也堪稱翹楚。余居湘中,嘗聞余君之雅望,遷移江城,常借洞庭一水與之以通心印。近余君集多年嘔心之作,刊刻流布,囑予作序以記。余欣然為之,亦勉力為之。
之所以成就余君者,傳統文化精髓耳。余君嘗言,學者之社會責任,正是高懸岳陽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與“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價值觀念,故能以熱心腸既繼往圣之學于當世,亦以一家之言觀百家之說,行學術批評之責于現在。柳詒徵嘗云:“講求學術必先虛心”,“不可挾一偏之見舞文飾說。”余君學術批評得其主旨,低調、平實,既重基礎理論之探索,尤重現實、現象之剖判,綜合概括,平情立言,為學術之深化、學術之自潔,實踐其繼學、“立言、立功的人生夙命”。文學評論家之譽當之無愧矣。
與眾多學者不同,余君專就當代學術立言,透文化之表象,析學理之深奧,尤重宏觀把握,突出理論求索與創新。余君藉《光明日報》立論曰:“面向世界,,平等對話是未來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并謂“單向輸入”或云“學術逆差”,與“翻譯、介紹、照搬多,而辯正地消化、吸收、有批判地融入我們學術理論的血肉中則做得不夠”,乃“其存在的兩個方面的明顯缺陷”,而“最大的缺陷是浮躁乃至腐敗”。文既呈其平實低調之色,亦顯大氣磅礴之風。雖為一家之言,亦可謂不易之論。
余致力學術研究多年,時至今日,于“學術”二宇茫然而無所措辭。學術之內涵、外延,始于何人、何時,不可考,亦不必考。或云“系統、專門之學問”,或云“學問與方法”,或具體曰“國學”(曹聚仁等語),或概而言之曰與“形質”相對之“精神”、“時代思潮”(梁啟超語)。如此大而化之之說,雖人言人殊,然皆視之“研究之研究”,或“專門知識之研究”也。若中國古代學術乃義理、辭章、訓詁之研究也。其根柢于專門,倚重于研究。英文以Academic research譯學術,亦彰顯專門與研究之義。當代學術亦如是。然則其固非無源之水,亦為近代學術承上啟下者。梁啟超論近三百年學術主潮為“厭棄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其“支流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錢穆斷言,近代學術導源于宋,道咸以下,“漢宋兼采”,乾嘉而后,“不識宋學則無以識近代”。二說不同,然以復古為形式,以創新為鵠的,視客觀為托命,古今中西,去粗取精,棄偽存真,實乃近世諸于同趨之途。“清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當代學術既承前代之余緒而有所揚棄,重新學理之探索,重客觀之實證:棄置復古之形式,開拓創新之道路。辛夷盡往,桃李之花盛開今世,余君自覺于前,條分縷析于后,而有《新時期學術發展之回瞻》,論引介之得失,中創新之肯綮,可謂領宗得意者也。
文化依積淀而有傳承,一代自有一代學術。清代學者、詩人趙翼有詩曰:“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豈止談詩,學術尤其如此。余君三定為當代學術推濤助浪,中國學者亦當致力新時期中國學術于百家爭鳴,花團錦簇中再領風騷。
是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