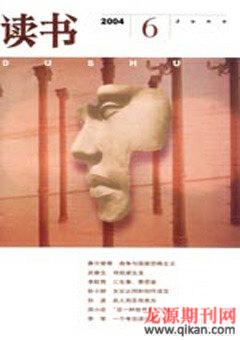短長書
李昌平等
取消農(nóng)業(yè)稅將引發(fā)一系列深刻變革
李昌平
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溫總理宣布要用五年的時間取消農(nóng)業(yè)稅。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如果按照總理所說的農(nóng)業(yè)稅率每年減少一個百分點,三年后農(nóng)業(yè)稅率就減少到了5%以下。當農(nóng)業(yè)稅率減少到5%以下時,就沒有必要再收農(nóng)業(yè)稅了——因為征收的成本會大于征收的稅額。如此大的力度解決三農(nóng)問題,確實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農(nóng)業(yè)稅取消的意義,不僅在于每年減少農(nóng)民人均五十元的負擔,更重要的是標志著“以農(nóng)養(yǎng)政”的時代即將結束,由此會引發(fā)一系列深刻的變革。
“農(nóng)不養(yǎng)政”鄉(xiāng)鎮(zhèn)體制和機構改革要來真的了
改革開放以來,鄉(xiāng)鎮(zhèn)政府部門以農(nóng)業(yè)稅為載體,派生出從農(nóng)民、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攫取剩余的數(shù)百種稅費負擔,且“取之于民”不是為了“用之于民”,而是為了解決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吃飯和福利的需求。中西部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部門的職能進入了一個怪圈——“收錢—養(yǎng)人—養(yǎng)更多的人—收更多的錢”;政府=干部=收錢=管理=尋租;政府財政=干部飯碗=農(nóng)民口袋=農(nóng)業(yè)稅費。
面對日益膨脹的機構和越來越龐大的干部隊伍,中央部署過三次鄉(xiāng)鎮(zhèn)機構改革,目的就是要精簡機構和人員,提高政府服務效能,促進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回顧歷次鄉(xiāng)鎮(zhèn)機構改革,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每次機構改革都是加強條條的權力,削弱地方塊塊的權力,上收農(nóng)民的權力。北京的各個強勢部委的權力是要加強的;地方政府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應付中央,一般情況下,地方的權力也難以削弱;每次改革的結果是農(nóng)民的權力更小了,管農(nóng)民的權力部門越來越大了,農(nóng)民身上的繩索越來越緊了。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市場配置人才、技術、資本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不利的,農(nóng)民需要技術服務和金融服務,但是每次改革都是削弱農(nóng)村技術服務和金融服務部門。
一般認為鄉(xiāng)鎮(zhèn)機構改革失敗的原因是沒有抓住轉變職能——“收刮”職能轉變?yōu)榉章毮苓@個關鍵。其實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縣鄉(xiāng)依然靠“以農(nóng)養(yǎng)政”,“收刮”農(nóng)民依然是縣鄉(xiāng)財政的主要來源。中央財政不養(yǎng)縣鄉(xiāng)政權,上面發(fā)帽子,農(nóng)民開票子,中央、省市各級不會產(chǎn)生真正改革鄉(xiāng)鎮(zhèn)體制和機構的動力。而農(nóng)民有改革鄉(xiāng)鎮(zhèn)體制和機構的動力,但農(nóng)民沒有權力。只有縣鄉(xiāng)政權靠中央財政統(tǒng)籌,縣鄉(xiāng)政權的基本職能才有可能轉變?yōu)榉辙r(nóng)民。中央政府才會下決心解決縣鄉(xiāng)如此龐大的機構和官僚隊伍。
隨著農(nóng)業(yè)稅的取消,“農(nóng)不養(yǎng)政”變?yōu)楝F(xiàn)實,縣鄉(xiāng)體制和機構改革不得不真正開始了。
“農(nóng)不養(yǎng)政”開創(chuàng)鄉(xiāng)村社會“民本位”新時代
在我國的中西部農(nóng)業(yè)地區(qū),農(nóng)業(yè)稅既是縣鄉(xiāng)“收刮”體制存在的理由,又是其存在的經(jīng)濟基礎;“收刮”體制的存在既是“官本位”體制的存在理由,又是其存在的經(jīng)濟基礎。只要縣鄉(xiāng)“官本位”體制存在,民主容易成為欺騙人民的招牌,法制容易成為桎梏人民的工具,市場容易成為權力和資本合謀的平臺,中央轉移支付的資金就難以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公共財政就難以建立起來,服務型政府是一個無法兌現(xiàn)的白條,建立公民社會也是一個無法實現(xiàn)的目標。
取消農(nóng)業(yè)稅后,鄉(xiāng)鎮(zhèn)的財政來源主要就是上級政府的撥款,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一致性——向上級爭取資源和優(yōu)化配置本鄉(xiāng)本土資源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和民眾共同的基本目標。取消農(nóng)業(yè)稅后,“收刮”體制就沒有了合法性和經(jīng)濟基礎,鄉(xiāng)鎮(zhèn)政府必然轉向服務型政府。在另一個層面,當縣級政府不找鄉(xiāng)鎮(zhèn)政府要錢了,而是反過來給錢,縣長對鄉(xiāng)長的要求主要就是把下?lián)艿挠邢拶Y源用好,以保證鄉(xiāng)民安居樂業(yè)。誰當鄉(xiāng)鎮(zhèn)長對縣長而言不是特別重要,只要人民滿意就行,這時縣政府和人民群眾的目標也是高度一致的。民選鄉(xiāng)鎮(zhèn)政府、讓人民群眾監(jiān)督管理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同樣的道理,當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不找農(nóng)民收錢了,誰當村長對鄉(xiāng)鎮(zhèn)長不是很重要,只要農(nóng)民滿意誰當都行,這時村民自治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當村長和鄉(xiāng)鎮(zhèn)長都是民選民管的,當鄉(xiāng)鎮(zhèn)政府和縣級政府不找小農(nóng)要錢,而是給錢時,官方控制鄉(xiāng)村社會最佳的選擇是提高民間社會的組織化水平,以降低鄉(xiāng)村社會的管理成本;反過來,鄉(xiāng)村社會組織化程度提高,民間力量得到增強,有利于一個健康的市場經(jīng)濟的、民主的、法制的、公平公正的自治為主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建立。很明顯,農(nóng)業(yè)稅取消后,支撐鄉(xiāng)鎮(zhèn)“官本位”體制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倒下了,預示著一個“民本位”的鄉(xiāng)村社會開始發(fā)育。
實行“稅轉租”開啟鄉(xiāng)村組織發(fā)展和村民自治新時代
過去是國家權力下鄉(xiāng),推行“稅外費”、“費改稅”,剝奪了土地集體所有者權利,所收的正稅、附稅和各種費都掌控在官方的手上,村自治組織成了一個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空架子,民間組織成了無本之木。官方掌控了鄉(xiāng)村社會的一切經(jīng)濟資源,民選的弱勢的村長不得不向官權乞討,民選的強勢的村長也會遭到掌控資源的官權贖買,如果贖買不成,官權也可以對強勢的村長行使合法的“加害權”。這就是十幾年來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只是“選舉游戲”的根本原因,也是民間組織艱難生長的根本原因。
取消農(nóng)業(yè)稅后,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重要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三年后,當農(nóng)業(yè)稅取消了,農(nóng)民種地還要不要交負擔?
在一般的學者和政策研究者看來,農(nóng)民種地再不要交任何負擔。實際上這是不對的,農(nóng)民種地一定要交費。第一,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或五十年不變的政策,導致農(nóng)民占用土地極不平衡,不收費就無法體現(xiàn)公平。特別是貧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惟一資料,不占用土地的農(nóng)民如果得不到相宜的補償,就等于他們的基本生存權被剝奪了,這是違反憲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須盡快修改);第二,土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所有者的權益通過什么來體現(xiàn)呢?第三,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必須要有自治的財政基礎;第四,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作為一個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水利、道路、技術服務、合作互助、發(fā)展基金、五保照顧等,必須擁有一定的資源;第五,農(nóng)民放棄土地的權益要進城發(fā)展,必須要拿一筆錢加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這筆錢從哪里來,應該由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支付——從地租或承包費中支付。
時下在減農(nóng)業(yè)稅的同時,要研究“稅轉費”或“稅轉租”的相關政策。種地的農(nóng)民一定要向村集體交納承包費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費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國家未來的農(nóng)村養(yǎng)老制度、合作醫(yī)療制度、義務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農(nóng)村人口轉移制度等等,都必須加緊研究、統(tǒng)籌安排。
隨著村民自治和民間組織的發(fā)展,長期困擾鄉(xiāng)村社會進步的諸多問題會得到突破:小農(nóng)戶無力應對大市場、大資本的局面會有改善,生產(chǎn)成本會大大降低,生產(chǎn)收益會顯著提高;鄉(xiāng)村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會大大提高,管理成本會大大降低,鄉(xiāng)村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會大大增強。“政府只管該管的事,不該政府管的事民間自然有組織去管”會成為現(xiàn)實;民主政治有了組織保障,農(nóng)村民主不再是少數(shù)人操縱的民主;法制社會才有基礎。如果窮人不是生活在一定的組織之中,法律是不能夠平等地保護窮人權利的,弱勢的人沒有組織做后盾,法律就會成為強勢者欺負弱勢人的工具。總之,民間組織是好的市場經(jīng)濟和好的法制社會的基石。
二十五年后又一個新起點
中國農(nóng)村改革改什么?開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高度壟斷的經(jīng)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弊端;開放就是要對內(nèi)和對外開放國營壟斷經(jīng)營的領域,總的目標是建立“市場經(jīng)濟、民主政治、法制國家”。在一個高度計劃和高度集權的體制下,構成農(nóng)村社會的三大基本要素:農(nóng)民、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都在嚴格的管制之中,整個鄉(xiāng)村社會缺乏活力和效率。改革的必然邏輯過程就是:放活農(nóng)民、放活基層組織、放活鄉(xiāng)鎮(zhèn)政府。
中國農(nóng)村的改革開放正是從放活農(nóng)民開始的。
二十五年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發(fā)展的根本障礙是人民公社把個人、家庭和大隊管得過死,在以“收刮”為主要職能的人民公社的體制中,大隊沒有生產(chǎn)主動性和積極性,家庭更沒有生產(chǎn)的權力,社員消極怠工,整個鄉(xiāng)村社會沒有活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公社制度不僅不能為國家的工業(yè)化提供更多的農(nóng)業(yè)剩余,相反,隨著越來越多的拖拉機、化肥、農(nóng)藥、鋼材等“支農(nóng)”物資下鄉(xiāng),國家通過公社獲取的農(nóng)業(yè)剩余相對減少了;另一方面,隨著支農(nóng)物資越來越多的下鄉(xiāng),農(nóng)民從公社得到的分配越來越少,吃飽飯越來越困難了。公社體制維持到七十年代后期,既不能滿足國家利益,又不能滿足集體和農(nóng)民的利益,國家、集體和農(nóng)民都在困境中突圍,這就決定了公社體制必然滅亡的命運。
小崗村的家庭承包經(jīng)營——分田單干沖破公社體制的牢籠,家庭有了活力,農(nóng)村勞動力的生產(chǎn)積極性得以釋放,糧食的單位面積產(chǎn)量大幅提高。由于家庭經(jīng)營制度的制度收益在“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后,還有“更多自己的”,所以,微觀的家庭經(jīng)營制度沖破貌似強大的公社制度和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像黎明的太陽,騰空而出。不僅如此,隨著“留夠集體的、剩下自己的”不斷積累,大隊和家庭有了發(fā)展的本錢,在當時的短缺經(jīng)濟的環(huán)境條件下,社隊(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家庭非農(nóng)經(jīng)濟——民本經(jīng)濟也獲得了飛速發(fā)展。
隨著民本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壯大,民間和地方政府也有了經(jīng)濟力量,越來越不滿意國家對農(nóng)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的速度和力度,財政“遞增包干、分灶吃飯”的制度隨之產(chǎn)生了——家庭承包發(fā)展為“政府承包”了。這種財政包干制度在一定的時期確實調(diào)動了地方政府和村集體發(fā)展經(jīng)濟的積極性,地方的基礎設施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但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在于“官本位”的“收刮”體制沒有任何的改變,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雖然“承包”了,但不是對等的法律主體之間的“承包”。
隨著時間的推移,上級政府得到的經(jīng)濟發(fā)展的好處越來越多,下級政府得到的越來越少;上級政府為了控制下級政府,延伸到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發(fā)帽子)越來越多,下級政府權利越來越少而“開票子”越來越多;上級政府甩給下級政府事權和達標升級工作越來越多,下級政府背在身上的包袱和套在脖子上的繩索越來越多。村一級是“收刮”體制的最末端,因此,捆的最死,受害也最深重。
從家庭承包到“政府承包”,二十五年過去了。放眼二十五年,我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社會的問題和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有驚人的相似性——鄉(xiāng)政府中央不滿意,村委會不滿意、農(nóng)民不滿意;現(xiàn)在的財政遞增包干體制,鄉(xiāng)政府沒有積極性、村委會沒有積極性、老百姓沒有積極性;現(xiàn)在的農(nóng)村稅費政策,地方政府捆死了沒有活力,村集體捆死了沒有活力,農(nóng)民也面臨“十幾頂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的遭遇。
所不同的是,現(xiàn)在的農(nóng)民比公社時期的農(nóng)民有了流動就業(yè)和在土地以外發(fā)展的自由,農(nóng)村經(jīng)濟制度和結構發(fā)生了深刻變化,民本經(jīng)濟已經(jīng)成為鄉(xiāng)村社會經(jīng)濟主體的現(xiàn)實無法逆轉了。在“放活農(nóng)民、放活組織、放活基層政府”的農(nóng)村改革中,我們用了二十五年,竟然還沒有走完“放活農(nóng)民”這一步啊!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當一種聲音——“農(nóng)民真苦、農(nóng)村真窮、農(nóng)業(yè)真危險”終于成為共識的時候,當“取消農(nóng)民負擔”、“農(nóng)不養(yǎng)政”成為現(xiàn)實的時候,我們終于欣喜地看到民間組織每年將獲得數(shù)百億的資源,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即將從“官本位”的“收刮”體制中解放出來,久違的、一個充滿活力的鄉(xiāng)村社會即將來臨了。
二十五年前的“放活農(nóng)民”引發(fā)了民本經(jīng)濟大發(fā)展,促進中國經(jīng)濟制度發(fā)生了深刻變革。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的“放活基層組織”也必然會引發(fā)鄉(xiāng)村社會的新一輪經(jīng)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將促進鄉(xiāng)村社會的治理制度和組織結構發(fā)生深刻的變革。我們必須果斷地抓住歷史性的機遇,推進鄉(xiāng)村社會朝著“民本位”的正確方向前進,以促進中國政治制度發(fā)生深刻的變化。
小崗村的悖論
王曉毅
研究中國農(nóng)村的人很少不知道安徽小崗村的故事,全村的十多戶人家聚在一起商量包產(chǎn)到戶,最后村里的干部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決定包產(chǎn)到戶。同時村里人商定,一旦干部因為包產(chǎn)到戶被捕,那么他們負責將其子女養(yǎng)到十八歲。正是這樣一個事件引發(fā)了全國的農(nóng)村改革。
這個故事不能不說是很悲壯的,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悖論卻是難以解釋的。如果說小崗村的農(nóng)民那么齊心,愿意承擔那么大的政治風險(包括經(jīng)濟風險),為什么他們卻不能在公共的土地上共同勞動?承擔這樣大的風險無疑是需要作出犧牲的,愿意作出如此大犧牲的人可以被假設為具有很強的集體主義精神,用集體主義精神去促成集體的瓦解,在邏輯上很難解釋得通。如果像以后所解釋的,他們有很強的個體主義精神,聚在一起的社員不愿意出工出力,只有分田單干,個人利益與個人勞動直接掛鉤才能發(fā)揮人的積極性,那么甚至為別人多犧牲一些汗水都不愿意的人,為什么能夠集體承擔如此大的風險?我們?nèi)绻蝗ヌ接憵v史的真實而去關注這則寓言所隱含的道理,可以看出農(nóng)村社會的兩種傾向:第一種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個人主義,每個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他們不希望受到其他人的拖累,這種觀念在中國農(nóng)村社會應該說是一直存在的。前輩先賢對此多有論述,如說中國農(nóng)民的“私”、“散漫”等等。在官方對小崗村故事的詮釋中,一直強調(diào)的是農(nóng)民對家庭經(jīng)營的熱愛,農(nóng)民對集體、對大鍋飯的抵制和拒絕,也就是農(nóng)民的個人主義。區(qū)別只在于,前輩先賢對農(nóng)民的個體主義多持否定態(tài)度,而改革以后對農(nóng)民的個體主義卻給予了很高的贊頌,在很大程度上將中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歸結為對個人主義的解放。
與個人主義相對應的應該是集體主義,農(nóng)民要形成社會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集體主義。甚至在小崗村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如果全村的農(nóng)民不能聚在一起開會,一起承擔責任,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會將土地承包到戶。不論是在中國或者西方,人們一直追求依靠農(nóng)民集體來克服農(nóng)村社會的困難,從家族、村莊的構建,到合作社和集體農(nóng)莊。生存?zhèn)惱砗偷懒x經(jīng)濟曾經(jīng)對農(nóng)民的集體主義做過一些解釋,因為農(nóng)民處于生存壓力之下,它們需要村莊為他們提供保護。此外國家遠離村莊也是村莊集體主義得以保持的條件之一,當然人們更多地從功能的角度去理解和設計集體主義。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農(nóng)村的個人主義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集體主義,這幾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問題在于,這種個人主義的盛行帶來了什么結果,以及這種個人主義是如何來的。從現(xiàn)代化的觀點來看,個人主義無疑是一種進步,個人主義帶來了理性化和效率。理性的農(nóng)民是精于計算的農(nóng)民,他們知道如何才能達到利益最大化。理性農(nóng)民是最容易接受利益信號的,他們受到利益的驅(qū)使。理性農(nóng)民也是關注個體的,他們不再受原有傳統(tǒng)的束縛。理性農(nóng)民只是市場上的一個行動者,或者購買,或者出售,包括他們的產(chǎn)品和自身的勞動力。當然在個人主義后面隱含對效率的高度關注,因為個人主義是現(xiàn)代的,所以符合個人主義的制度安排才能提高效率。最符合個人主義的無疑是清晰的產(chǎn)權,也就是將所有能夠產(chǎn)生收入的資源都加以清晰的劃分,歸屬到個人的名下,個人對它們有全部的權利,特別是使用權和收益權。在這種假設下,村莊被一步步地劃分到個人名下,土地承包了,村辦工業(yè)被分了,集體的山林也被發(fā)包給個人,甚至荒山荒地也被拍賣了。而所有這些舉措的背后都是對個人主義與效率的關注。但是農(nóng)村的事情可能要復雜得多,因為并非一包就靈,因為人畢竟生活在社會關系中。如何現(xiàn)代化,人還是生活在社會中的,現(xiàn)代主義者也不會斷然否認個人之上的集體,只是他們希望以政府和功能主義的集體來代替原有的集體。政府是先賦的,要承擔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責任;人們?yōu)榱藗€人的利益,也可以組成一些群體,但這個群體的成員是以個人身份加入的,他們加入組織是為了擴大個人利益,因此有加入的自由,也有退出的自由。
盡管現(xiàn)代化的理論在邏輯上是清晰的,但是在實踐上并不是如此清晰,首先農(nóng)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我們很難設想農(nóng)民的需要都能靠功能性的組織來完成。盡管現(xiàn)在這種功能性的組織越來越多,如合作醫(yī)療服務于農(nóng)民的健康,專業(yè)技術協(xié)會滿足農(nóng)民的技術需求,甚至一些地方成立了家長學校以發(fā)揮家長與學校共同教育的作用。但是他們存在著兩個困難,首先是功能組織不能適應農(nóng)民多樣性的要求,農(nóng)民的日常生活中遠遠不是只有這么簡單的幾個方面需求,他們的需求是多樣化的,靠幾個專業(yè)組織很難完成。我們也不可能設想為農(nóng)民的每一種需求建立一個組織;其次,即使是在功能化組織的范圍之內(nèi),他們也只能服務很少的人,甚至有許多組織與所預期的功能已經(jīng)相去甚遠。
盡管政府承擔了許多公共職能,但是我們很難想像政府直接面對公民的社會格局。首先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還不強,受到財政和技術能力的限制,政府提供的服務在很多時候是低效的;其次政府是凌駕于社會之上,不僅不能服務社會,甚至主要的努力用于控制社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的目標要高于服務的目標。因此當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農(nóng)村個人主義代替集體主義以后,盡管收入可能有所提高,但是農(nóng)民被投入到巨大的不安全當中,因為他們?nèi)鄙倭思w的保護。在他們收入提高的時候,他們的社會生活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比如醫(yī)療水平降低了,社會變得更不安全了,人際關系惡化了。人們所預期的隨著個人主義而一同到來的普遍法制化環(huán)境、功能組織發(fā)育似乎還遙不可及。
農(nóng)民集體主義的解體不能不說是農(nóng)民的悲哀。這里所說的集體主義解體主要不是指人民公社的解體,這是一個整體的結構變遷過程,包括隨著國家進入對村莊原有結構形成的破壞,集體主義倫理解體等等,甚至包括人民公社的建立。這個過程并非是過去二十年的事情,可以追溯更遙遠的歷史。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農(nóng)民的個人主義不僅僅是社會現(xiàn)代化(包括市場經(jīng)濟)的自然發(fā)展過程,就像小崗村的故事中所顯現(xiàn)的,經(jīng)過二十年的詮釋,個人主義已經(jīng)被稱為主導的話語,而非自然發(fā)展過程。實際上,不能不說個人主義是有意識建構的結果。從意識形態(tài)到制度安排都在不斷地強化個人主義,而這又是在發(fā)展和效率的名義下進行的。如果說農(nóng)村社會都有個體和集體主義兩個方面,現(xiàn)在也可能需要在制度安排上考慮一下集體主義了,這正是社區(qū)發(fā)展的基礎。
第一位關注環(huán)保的經(jīng)濟學家
秦勝軍
《讀書》二○○四年第一期、第二期分別刊登雷啟立先生《堅持一種可能》和王諾先生《“生態(tài)整體主義”辯》的文章。兩文介紹的均是從生態(tài)、環(huán)保角度反思工業(yè)文明、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著作。雷文介紹的書的作者是一位中國學者;王文則在自己書中把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一些關注生態(tài)的學者的觀點做了簡介。可見,從一九六二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生態(tài)、人類生存環(huán)境逐漸成為東西方的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東西方學者終于走到一起。不過,兩文均沒有提及一位最早反思經(jīng)濟發(fā)展就是“硬道理”的西方學者,其他類似的著述也常常忽略這位倡導環(huán)保的著名政治經(jīng)濟學家。他就是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亞里士多德”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處于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十九世紀的一位經(jīng)濟學家竟然反對經(jīng)濟的無限增長,反對人們對奢侈豪華的物質(zhì)生活的追求,這的確令人疑惑。但如果我們簡單了解他的經(jīng)歷,他的社會理想,也許就不再感到費解。
關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經(jīng)濟學家必然熱愛環(huán)境、熱愛大自然。密爾正是這樣一個經(jīng)濟學家。密爾對自然的熱愛大致有兩個原因。首先,它是父親詹姆斯·密爾影響的結果。密爾在《自傳》中說,父親不僅親自教授他各科知識,還在自己很小(七歲)的時候就帶著他四處遠足旅行,教他學會領略大自然的美(John Stuart Mill, Autog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6.)。密爾對自然的迷戀在他十四歲游學法國時得到加強,法國南部的自然美景給密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給在異國他鄉(xiāng)獨自求學的密爾以心靈的慰藉。其次,密爾二十歲時那次“精神危機”的解除有自然力的襄助。密爾從小接受邊沁功利主義的教育,他堅持“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的信條。但密爾在二十歲時突然懷疑自己的信仰與理想。這部分是他父親只注重“智性”教育、忽視“情感”培育的結果。此時,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歌中描述的自然美景和沉醉于美景中的情感喚醒了密爾的生命力,這是密爾從危機中得以漸漸解脫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經(jīng)歷使密爾認識到情感培育在人類幸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大自然在培育情感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密爾對自然的熱愛終其一生。在不算長的一生中,他游歷過許多地方,英倫三島的景區(qū)自不待言(密爾寫了大量的游記),密爾還經(jīng)常到歐洲大陸旅行,法國、意大利、希臘、德國都遍布他的足跡。
密爾對生態(tài)的關注和保護、對自然的愛體現(xiàn)在他的具體行動上。密爾的一位傳記作家兼密友亞歷山大·貝恩(Alexander Bain)記述了幾件密爾的軼事,表明密爾對自然真切的愛。其一,密爾曾惟恐下院關于圈地的法律會損害自然景觀,會減少風景旅游區(qū)的面積。這是密爾改革土地法“五點”主張之一。其二,他曾在一八三六年寫文章表明:過多的鐵路建設會造成英國鄉(xiāng)間風景的大破壞(他父親也持這樣的觀點)。另外,一次倫敦市一條街道要拓寬,需砍伐格林公園(Green Park)的一排樹。密爾聞訊后,立即介入此事,經(jīng)過有關方面的斡旋,大樹最終得以保存。
不過,密爾熱愛自然、保護環(huán)境的信念在他的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中有雖簡潔卻更為有力的體現(xiàn)。
在其幾乎影響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一書的第四編第六章中,密爾專門論述了一些“著作家們所懼怕和嫌惡”的所謂財富與人口的 “靜止狀態(tài)”。密爾說,人們所謂社會的經(jīng)濟進步通常指的是資本的增加、人口的增長以及生產(chǎn)技術的改進。前兩代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們普遍認為,經(jīng)濟進步會有終點,“人類工業(yè)的水流最終將不可抗拒地匯入表面平靜的大海”,他們認為這是個令人不快的、使人沮喪的前景。因為這些經(jīng)濟學家總是把經(jīng)濟上美好的東西同、而且僅僅同進步狀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經(jīng)濟學家中甚至包括著名的亞當·斯密。密爾說,他則不“以厭惡的心情看待資本和財富的靜止狀態(tài)”。他指出,毫無疑問,如果生產(chǎn)技術進一步得到改良,資本繼續(xù)增長的話,整個世界的人口,就仍有大大增長的余地。但即使人口增長是無害的,也沒有理由再讓人口增長。密爾認為,現(xiàn)在,在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人口密度都已達到使人類能夠從合作與社會交往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限度。即使人人都能得到充足的糧食和衣物供應,人口仍然有可能過分擁擠。接著,密爾表達了自己獨特的觀點:人擠人、人碰人的狀態(tài)是不好的。孤獨,即人能經(jīng)常一個人獨處,是思想深刻和性格沉穩(wěn)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一個人面對大自然的美和壯麗,則是使人產(chǎn)生思想和抱負的搖籃,具有思想和抱負不僅對個人是有益的,而且對整個社會也是有益的。他說,一想到世界將喪失其生機盎然的景象,變得一片光禿,每一寸能為人類種糧食的土地將被耕種,每一塊長滿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將被耕翻,所有野生禽獸都將因與人爭食而滅絕,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將在農(nóng)業(yè)改良的名義下被當作野草而予以鏟除,想到這樣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密爾的這些預言很不幸地變成了當代的現(xiàn)實。密爾進一步說道,如果僅僅為了使地球能養(yǎng)活更多的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財富和人口的無限增長將消滅地球給我們以快樂的許多事物,那我則為了子孫后代的利益而真誠地希望,我們的子孫最好能早一些滿足于靜止狀態(tài),而不要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滿足于靜止狀態(tài)(《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
密爾持這樣的“異見”的原因還在于,他相信當時的技術已能夠使人類免于匱乏,一部分人(如工人階級)的貧困在于缺乏公平的分配制度。在這種情況下,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不過使有事可做的富人變成“無所事事的富人”,窮人則無法從經(jīng)濟增長中得到好處。由此可見,密爾對建立良好的分配制度以使物質(zhì)財富惠及所有人的強調(diào),也與當代環(huán)保主義者對窮國富國間公平分配財富以保護環(huán)境有共通之處。
由密爾所引發(fā)的保護自然、熱愛自然的清風,現(xiàn)在已掀起巨大的綠色潮流。我們希望這潮流有助于遏制人類對自然無止境的貪欲,使人類對“發(fā)展”持更加謹慎的態(tài)度,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和諧一些,使當代人和他們的子孫后代,在從大自然中獲得基本的物質(zhì)資料時,能更多地獲得精神方面的享受。
三只眼睛看英語
顏治強
眾所周知,英國的殖民擴張從十六世紀開始,英語也隨之附麗而出。前三百年,其影響所及主要限于殖民地,歐洲大陸不在意,亞非拉文明社會也不恐慌。第一次大戰(zhàn)助英語成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虎添翼,致使其近幾十年有橫掃六合,凈吞天下語言之勢,于是有人凱歌高奏,有人警鐘長鳴,有人目瞪口呆。五個主要的母語國面向海外的語言政策措施和相關組織構成了凱旋曲中的一個個音符。喜在天下畢竟有仗義者,從英國殺出來的菲利普森先生就是這樣一位義士。積數(shù)十年奔走各國教學和研究之經(jīng)驗,他禁不住不斷地驚呼:“謹防上當!”其《語言領域的帝國主義》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真佩服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在這種曖昧時代居然敢于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放出來;也佩服何南林先生,在人家迫不及待地向英語示愛時,敢于站出來說:“她不是處女!”最后還佩服《讀書》雜志,當英語的光輝使別人暈眩,甚至聾啞時,敢于當眾指出:“它背面是黑的!”
不過客觀地說,英語之有今天并不全靠英美政客的陰謀策劃,而是得力于三種力量:母語使用者、第二語言使用者和外語使用者。俠義如菲利普森,也不過忠實地、坦誠地把第一組人的眼睛看到的外部英語世界剖析給我們看。另外兩只眼睛在哪里?它們從英語看到了什么?
第一只眼睛來自英語國家,尤其是英國從前的殖民地。在講英語的白人到達之前,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就有文明,有語言。由于受到自然、宗教和民族條件的限制,它們多多少少處于事實上的分裂狀態(tài),既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也沒有統(tǒng)一的語言。西方征服靠的是軟硬兩手,硬的是堅船利炮,軟的是分化懷柔。兩手能夠奏效是因為當?shù)叵忍觳蛔悖至训锰珔柡Γ热缬《鹊恼Z言和方言竟然多達一千六百五十二種,因而不能避免衰弱和陷落。這種解釋至少對整個印度次大陸和非洲來說都是正確的。印度擁有人口和山河之利,自己不亂,英國絕對不能以人數(shù)少得可憐的遠征軍使其臣服。長期以來,帝國主義勢力以我為敵,使我們不得不處于緊張的備戰(zhàn)狀態(tài),研究為政治宣傳服務,只采信其殖民統(tǒng)治血腥的一面,不提縱橫捭闔與懷柔,難免使讀者有偏信之嫌。英國入主以后,是否對原住民采取過英語化政策?幾乎從來沒有。相反,鑒于殖民地的廣大和推行英語的困難,英國人不得不從一開始就嘗試以印度人治印度人,與此相應的政策是出資幫助當?shù)厝私ǜ嗟蔫笳Z學校。此議一開,殖民政府內(nèi)部人士的臧否姑且不表,立即引起印度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印度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羅伊憤怒地說,這是使這個國家保持愚昧的最好政策。他接著說,為了改進本地人的知識水平,政府應該創(chuàng)立一種比梵語更加益智的教育體系,延請在歐洲受過教育的博學之士,傳授有用的科學知識。不言自明的是,這種體系只能使用英語。事隔十余年,時任英印公共教育委員會主席的英國著名作家和歷史學家麥考利決心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場爭論:“與梵語或者阿拉伯語相比,英語更值得印度人去學;原住民也渴望接受英語,而不是接受梵語或者阿拉伯語教育……現(xiàn)在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去培養(yǎng)一個新的階級,它可以在我們和被我們統(tǒng)治的千百萬人之間充當翻譯。它是這樣一個階級,血液和皮膚是印度的,而情趣、觀念、道德、心智是英國的。我們交給這個階級的任務是:凈化這個國家的方言土語,用從西方借來的術語改造它們,使之成為向大眾傳播知識的工具。”登載這些言論的《麥考利備忘錄》后來成為對印度次大陸影響最深遠的語言政策文件。作為旁觀者,我最感興趣的是來自不同世界的兩只眼睛看同一個事物時折射出來的影像:羅伊看到的是脫貧和重新站立起來的希望,麥考利看到的是馴服和控制的工具,真是各人打各人的算盤。給我們提供這個畫面的是南亞籍美國英語教授卡奇魯。
南亞的分裂和英國君臨造成的一個結果是,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政黨是用英語組織的,它們的領袖驅(qū)逐英國人的號召是用英語發(fā)出的,甚至連圣雄甘地和尼赫魯結束使用英語的呼吁也不得不靠英語來發(fā)起。在獨立即將實現(xiàn)時,尼赫魯斷言英語將于二十年內(nèi)從印度消失。五十多年過去,今天英語在他的國家與印地語分庭抗禮。討厭的英國人走了,美國人沒來,誰在那里賣力地推廣英語?是印度人自己。原因很簡單,趕走異族統(tǒng)治者后,國家內(nèi)部的民族和部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誰也不想看到另一個民族的語言壓在自己的語言頭上,成為國家的官方語言,從而使自己屈居下位,結果是由政府承認的地方語言交替上升,競相與印地語爭雄。其次是技術原因。印度近現(xiàn)代教育的框架是用英語構建的,覆蓋初中高三個階段,當?shù)卣Z言無法匹敵。要舍棄英語重來,社會沒有這種承受能力,更不用說大學——通天塔的頂端——幾乎只對英語使用者開放,少小不學,老大連往那兒擠的分都沒有。因此各種地區(qū)語言和印地語學校都不如英語學校好招生,質(zhì)量也不能與其匹敵。從印度土壤中沒有產(chǎn)生相當于我們普通話的語言,但是政治統(tǒng)一和現(xiàn)代化建設又需要它,正好英國人走了,原先的民族仇恨淡化,英語變得在感情上比當?shù)氐膹妱菡Z言較能令人接受。現(xiàn)在,作為跨地區(qū)、跨宗教、跨文化的內(nèi)部交流工具,它與印地語共享普通話的地位。最后,不容忽略的是,教育政策是政府中那些受過最好的英語教育、現(xiàn)在有子女在接受最好的英語教育、將來要把子女送進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去接受教育的人定的,他們當然要想方設法加強英語教育。難怪卡奇魯挖苦他們:“對待英語,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有兩副嘴臉:公開地反對英語的嘴臉和暗地里親英語的嘴臉。”由于這些因素的作用,印度現(xiàn)在有三千多萬人熟練使用英語,多少會一點的人則不計其數(shù);英文出版物種類和數(shù)量緊隨美國和英國,超過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另一只眼睛來自沒有被英語國家殖民征服過的國家和地區(qū),包括咱們中國。英語在這個類型區(qū)傳播的主要動力是各國經(jīng)濟的國際化——國際化的經(jīng)濟需要國際化的語言。受其驅(qū)動,不但曾幾何時自給自足的人們回過頭來,就連一貫傲視英國的法國人都趕著要靠英語擠進地球村的曬場上去分公糧。令人辛酸的是,村里的分配采取的并不是平均原則,而是附帶若干的要求和規(guī)定。國際化的技術條件是工業(yè)化和信息化,這些都要花錢,對那些農(nóng)業(yè)人口超過一半、甚至高達百分之八九十的國家來說,福澤仍然十分遙遠。再說,外語型英語圈也有中心與邊緣,位置不是由學費,甚至也不是由學習年限來決定,而更多地取決于地理位置、幅員以及就業(yè)和居住地的類型。日本既是經(jīng)濟最發(fā)達,又是在英語上投入資金和人力最大的國家,教員有十萬之眾,再加一萬老外,國民幾乎百分之百受過六年以上英語教育,結果會說的人遠遠未達到百分之五,與我們差不多。為什么費力不討好?第一怪單一民族,沒有內(nèi)部交流的需要;第二怪大洋環(huán)繞,油門踩爛到不了外國;第三怪身處人口爆炸中心,自己與鄰國都不愿意向?qū)Ψ綇氐组_放就業(yè)與居住空間。人家荷蘭沒費這么大勁,說英語的達到百分之四十;丹麥和挪威嫌雙語麻煩,竟然有人倡議大學里面只用英語算了;在法國,因為受了英語的滋潤,保護法語協(xié)會如雨后春筍。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歐洲大陸瘋狂地推廣英語嗎?非也,是歐洲聯(lián)盟要求各成員國彼此開放就業(yè)和居住地的措施把人們逼到了創(chuàng)造通用語的路上。在所謂的大歐羅巴流動最方便的語言就是英語。正因為如此,連一貫對大英帝國的擴張懷著醋意的大陸人也不得不承認:“英語可能是大不列顛對歐洲的惟一貢獻。”
我國的英語問題的癥結是只管耕耘,不問收獲。千萬人過獨木橋,上不去和擠下河的不在少數(shù)。當事者迷,已經(jīng)受了痛苦和損失,就不責備他們了。可恨的是有些清醒的旁觀者,明明知道人多了過不去,偏偏要起勁地宣傳、組織和鼓動過河。對外漢語辦一九九○年出版的一本匯編就說,當時我國大約有五六千萬人在學英語。張中載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估計,現(xiàn)在向英語投資的人數(shù)可能又翻了一翻,從業(yè)人員自不待言。結果怎么樣,沒有人調(diào)查過,恐怕不會比日本好。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人人都想把投資和時間變成利潤,夢想沒有實現(xiàn),自然要罵吸收資金者,所以一九九○年代以來英語教學界逐漸成為眾矢之的,贏得了“費時低效”的美譽。都是活天冤枉,其實我們教書的又沒有叫人盲目投資,更沒有能耐脅迫買股。據(jù)我觀察和研究,英語教育在我國有實熱與虛熱兩面。經(jīng)濟發(fā)展,對外交流增加,對英語的需求有所增長,培養(yǎng)出來的使用者也增長了。同時虛熱也很嚴重。本來,財富照耀窮人就像月亮和星星照耀夜空,求才之路光輝燦爛,誰也不需要指點。英語有用沒有用,有大用還是小用,學過幾年的知道,人民知道。國家關心和干預的應該是中學教育,大學生和就業(yè)人員學不學,學多少應該走放開搞活的道路,讓市場和職業(yè)決定:好大學多教,中等大學少教,劣等大學不教。專業(yè)技術人員按門類和等級區(qū)別對待:從西方傳入的學科宜考,中國土生土長的學科不必考;要考的學科,以及高級的、研究性的職稱要認真考,把那些真正懂,而且會用的人選拔出來。為了避免腐敗和勞民傷財——這兩者常常珠聯(lián)璧合,必須把發(fā)文件通知考試的政府部門同組織印書和收費的部門嚴格分開,建立獨立的、向政府納稅的考試機構。既然社會對英語技能的需要是通過具體工作表現(xiàn)出來的,那么,要不要合格證書,要什么等級的合格證就是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事,學校管不著,政府也不要無事忙。
目前,全球?qū)W過英語的人四分之三生活在二語區(qū)和外語區(qū),所以他們才是推進英語世界化的根本動力。各國自己的需要是內(nèi)因,美英再妖媚,援助再誘人,也不過是外因。有了英語,通天塔是否可以建成暫且不表,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它不能使世界各國的各階層立即實現(xiàn)共同富裕。因此眼下應該關心的是:就中國的客觀條件而論,大規(guī)模英語教育的結果是像日本還是像歐盟大陸?現(xiàn)代化是不是等于英語化?推行英語教育是否應該以犧牲漢語和其他學科為代價?以我之見,這種問題對我國人民和我國文化的重要性絕不亞于“工業(yè)化是否應該以犧牲農(nóng)民為代價?”一類討論。
心里的琴弦是怎樣撥響的
劉亞丁
語文教學實非小節(jié),它事關民族的精神素質(zhì),所以不可小看。《讀書》去年十期諸君的座談,今年一期蔡可先生的《“語文”、“文學”宜分科》,為日益邊緣化的文學在學校中吁請安身立命之地,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實我們不妨把眼光放開闊點,看看左鄰右舍如何在中小學教文學,可以為改革我們的語文教學提供佐證。
近十來年說起俄羅斯的經(jīng)濟大家都會惋惜,說起俄羅斯民族卻少有不稱贊素質(zhì)高的。對塑造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素質(zhì)來說,大學前的文學教育、藝術教育功不可沒。大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畢生致力于具體的教育工作,他非常重視美育,認為,實行德、智、體、美和勞動教育,并不僅僅意味著使兒童分別在這些方面得到收獲,而最根本的在于形成兒童統(tǒng)一的、豐滿的精神世界。他說:“每一個孩子就天性來說都是詩人,但是,要讓他的心里的琴弦響起來,要打開他創(chuàng)作的源泉。”(蘇霍姆林斯基:《給教師的建議》,杜殿坤編譯,教育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蘇聯(lián)大學前的文學教育,似乎就是要撥響學生心里的這根詩的琴弦。蘇聯(lián)的基礎教育一般是十一年制,從八年級起可以進中專,也可繼續(xù)受基礎教育。因此本文中使用的“中學”一詞實際上相當于我國的中小學。他們的課程分為自然類:數(shù)學、物理、化學、自然、地理;社會類:語言、文學、歷史、經(jīng)濟地理;還有思維、勞動等課程。語言課在講俄語的地區(qū)就叫“俄語”。文學課叫“俄羅斯文學”或“祖國文學”,這門課的分量重得令人難以置信。
五十年代的“俄羅斯文學”課的教材搜羅豐富的文學作品,誘導學生大量讀作品,在閱讀、品評中來開啟性靈,培養(yǎng)審美感知能力,雕琢和諧向善的心靈。一九五○年出版的七年級的《祖國文學》教材,六百三十七頁,除了在剛好兩頁的引言中談了點作家的階級性、文學的教育性等大道理,全書都是作家的作品,附加必要的注釋、思考題和個別名詞術語解釋。十九世紀文學部分:普希金,傳記、《波里斯·戈都諾夫》片段、十六首詩;萊蒙托夫,兩首詩、《童僧》、《塔曼》;果戈理,簡略年譜、《欽差大臣》全劇;屠格涅夫,兩個短篇;亞·奧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人好算賬》全劇;還有涅克拉索夫、謝德林、大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作品。蘇聯(lián)文學部分有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杰米揚·別德內(nèi)、吉洪諾夫、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特瓦爾多夫斯基、小托爾斯泰、法捷耶夫、伊薩科夫斯基、希巴喬夫、肖洛霍夫、西蒙諾夫以及另外四位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九年級下期的《俄羅斯文學》篇幅減少了,三百九十頁,作家作品數(shù)量也少,但大作品更多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選了四章,涅克拉索夫的《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選了大半篇幅,還有《戰(zhàn)爭與和平》等大作品的章節(jié)、契訶夫的《櫻桃園》全劇、丘特切夫和費特的詩等。在后一本書中,還有一些閱讀作品的參考資料,比如在契訶夫的《櫻桃園》后附有契氏談該劇的三封信的片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生活和藝術》中的談《櫻桃園》的三頁文字。這樣的十年開下來,大致相當于咱們大學中文系開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選”兩門課。
從高年級開始,除了讀作品外,還要開“俄羅斯文學史”課。一九五三年版供九年級使用的《俄羅斯文學史》,四百三十一頁,有三四十年代、別林斯基、赫爾岑、六十年代、岡察洛夫、亞·奧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七八十年代、謝德林、大托爾斯泰、契訶夫和九十年代等章。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的俄羅斯文學盡在此書之中,當然除了當時還在禁區(qū)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外。蘇聯(lián)解體后,中學的文學課依然是重頭戲,二○○二年莫斯科大鴇鳥出版社出的《文學·高考輔導資料》包括很多俄羅斯重要作家,只是去掉了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增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瑪托娃、米·布爾加科夫和索爾仁尼琴等。我國作為學術著作或大學教材翻譯的布洛茨基《俄國文學史》、科瓦廖夫《蘇聯(lián)文學史》、阿格諾索夫《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其實都是他們的中學教材。經(jīng)過中學如此這般的文學強勢誘導,利根之人加上勤于誦讀,大半俄國文學便爛熟于心;鈍根之人也不至于將文學先賢張冠李戴。更何況他們高年級還要開寫作一類的課程。
北方鄰居就這樣開文學課,缺陷明擺在那里,講來講去全是他自己的東西。這樣開文學課收益也是大大的,在心里詩的琴弦撥響,自然會吟唱動聽的旋律。二○○二年一月三日我同高爾基文學院院長、作家謝爾蓋·葉辛聊天:二十多年前學文學、當詩人曾是我國青年的理想,現(xiàn)在愿意讀中文系的人已經(jīng)很少了。你們高爾基文學院好招生嗎?他回答說:在我們國家只是部分地出現(xiàn)了類似的情況,我們的民族是讓人驚訝的非實用主義的民族。我可以樂觀地說,俄羅斯的青年感到作家的職業(yè)是一種崇高的職業(yè),盡管作家可能很貧困——他是苦行僧,他是必將到來的新生活的編織者。(詳見拙作:《風雨俄羅斯》,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二○○二年東正教歷圣誕節(jié)時,我在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里遇到個跟我討酒錢的五十開外的男子,自稱是建筑工人,他同我熱烈地談論起了米·布爾加科夫的小說。——落魄與高雅就這樣奇異地混雜在一起。我曾見到,一位教數(shù)學的副教授用俄文大段大段地背誦《紅樓夢》和《西游記》中的詩詞。瀏覽《二十世紀俄羅斯作家傳記辭典》會發(fā)現(xiàn),馬卡寧、索羅金、佩列文這些俄羅斯當紅作家好多是理工科出身,率爾操觚靠的還不是中學墊下的文學底子。瞧瞧,美的種子已然掛果。
讀者也許要問,蘇聯(lián)或俄羅斯的中學生哪有那么多時間來讀文學作品?答案是:當初俄羅斯的中學生有幸免受“黑色七月”的煎熬。原來俄羅斯沒有國家統(tǒng)一的高校入學考試,由各大學自主命題考試,猜題押寶自然無從做起,學生不必陪老師玩應試教育那一套榨取腦漿和生命的游戲,自然樂得細嚼慢咽普希金、布爾加科夫們烹調(diào)的精神美食。請注意,我用了“當初”兩個字。二○○三年九月二日出版的《結果》周刊上載有俄羅斯聯(lián)邦教育部長費利波夫的訪談錄,他莊嚴宣布:已經(jīng)開始逐步向國家統(tǒng)一的單一高考過渡,二○○六年秋季將實行新的中學課標。上帝保佑,但愿全國統(tǒng)考和新課標溫柔點,不要鹵莽扯斷北國少男少女心里詩的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