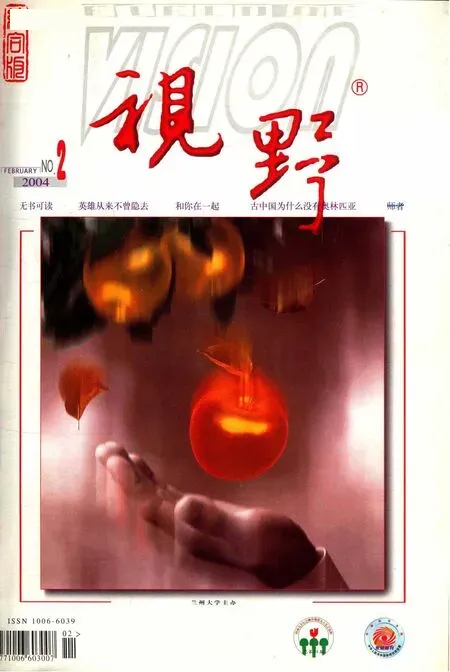待葬的姑娘
劉志成
編者按
人生的旅途可能正是因為無數的偶然和變數才讓人充滿了期待和遐想,結局的不確定更讓我們一路忐忑一路走。
所以,預見和命定的人生是無趣的,而文中主人公的人生之旅似乎就是這樣:沒有過程,只有確定不疑的等待死亡。
九月的風透著徹骨的寒意,我和患了癡呆癥的表哥二拴沿著一條如繩的小路拐上一個圪梁后,就看見了那排廢棄了的土窯洞,老遠就見窯臉裂了縫,如果連續下幾場猛雨,它絕對會倒塌的。泥打的院墻只剩半截子,院中荒草很密,聽得見風翻動的嗚嗚聲。
我的腳步無比沉重,拉遠的目光在風中哆嗦。
還是昨天時,來姑母家做客的我遭遇了大雨。在村口,我猛地聽見風雨中傳來微弱的呵呵聲時,我愕然了。窯洞里呆著一個癱瘓了的啞巴女孩。那是二拴的二叔——一個16年前死去的男人新“娶”回來的媳婦。當姑母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時,我的心就緊縮得發疼。在陜北,12歲以上的男性死了,就要埋入祖墳,倘是光棍,親屬會買來未出嫁女孩子的死骨殖,同其一起安葬。當時,姑母仿佛讀出了我眼中那一種并不輕松的東西。二拴的二叔死時,家里窮得買不起女骨,就草草地埋了。姑母解釋時,眼圈里蕩漾出郁郁的漣漪。你們這是犯罪,我的心情無比沉痛。但姑母的眼光里滿是迷惘。老命,這幾年家里年年死大牲口,請得陰陽先生,說是二拴他二叔在做怪,姑母的聲音中滲滿了無奈。你姑父多方打聽,才在幾十里外的一個小山村里,和一戶急著用錢娶媳婦的人家用4000塊錢買來了那個病重的癱子,誰知養了半年了還不死。聽著姑母發狠的聲音,我的心在發冷,但我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嘴唇兒緊閉著終于什么也沒說……
窯里的光線很暗,地上鋪了一層糜草,一條爛氈子展在草上,幾只老鼠在咯吱咯吱地嚼著草頭。我們的出現,驚憂了它們。只有一只小老鼠和我對視了幾秒,其余的皆放下嘴頭的活,匆匆鉆進草堆不見了。空氣里溢滿了尿騷味,我不由得捂住了鼻子。那個女孩蜷縮在毛氈上,默默地用蓬亂的目光展開了一個午后的光芒。女孩像四五歲的孩子大小(實際年齡已21歲了),從窯里左角上的一個木頭樁子上系著的一條粗布繩子拴在了她的腰上,繃得筆直。涂了蠟似的臉色浮腫得如遭了霜的農作物蔫蔫地提不起精神,眼眶深陷下去,那種本該像雨后的玉米葉子樣的鮮活也不見了,代之的是一種令人無法言明的渾濁。干裂的嘴唇布滿了血痂,一張一合地扯著微弱的氣息。下身蓋著一塊極臟的紅布,一角已被她抓在雞爪似的手里,極慢地抖動著。半截沾滿了屎尿的裸腿露了出來,瘦得像漚過的麻材。氈子濕濕的,那截露出的腿浸得暗紅,被指甲摳得爛糊糊的,發了膿,已經看不出有一塊完好的皮膚了……溽熱的陽光沉重地掉在了女孩的腿上,寬容著數十只蒼蠅丑陋的笑聲。我幾乎要窒息了,心好似千斤重石壓著。生命只有一次,而她主宰了自己嗎?生活的無奈,使女孩的親人們呈現出怎樣的一種瘋狂呀!他們的心中留下的慘痛會惦念成額上的皺紋嗎?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呵,一根血脈連著,又怎能不懸著心呢?……想著這些,我驚駭地閉上了眼睛。痛苦是不能轉嫁的,如果能,這時候我愿意替代。
……脆弱的女孩是否能挺過即將到來的冬天?我內心擎起的疼痛是否能堅持到明春花開?我盡力壓制著自己的情緒,艱難地睜開眼睛。女孩舞動紅布的手已耷拉下來,驚恐地看著我們。女孩無語。我也無言。窯洞浸在發霉的陽光里。
二拴掀起紅布,我看見一只小老鼠的身子埋在草層里,只露出了頭,有些遲鈍地看著我們。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二拴的一只腳已落在了鼠身上。二拴的腳抬起的時候,鼠已成了一個扁形狀,眼睛瞪得大大的。鼠的嘴角有血慢慢滲出。二拴的腳在跺死鼠時,也跺疼了我的心臟。我憂傷的思緒隨著淚水漸漸展開:那是怎樣的一種生命的情境呀!為了恪守自己靈魂中的一縷蔥綠,在銅臭與丑陋飛舞的季節中,我成了怎樣的一塊孤獨的石頭……眼前的鼠之死,是由于丟失了天性的戒備,但我呢,我的真誠,我的癡氣,我春天的品質淪為隔膜和譏笑,又是丟失了什么?這使我在很多年后,還一直困惑不已。
二拴踏下去的那一聲脆響,勾去了女孩的目光。此時,我看見女孩的眼睫毛上浮起了絲絲縷縷的憂傷,隨即有兩滴清淚從她的臉頰上滾落。她的喉嚨里發出了含糊不清的呵呵聲,艱難地將手抬了起來,一點一點探向了死鼠。女孩的這個動作和她的眼淚,是多年來惟一誘我落淚的因子。一剎那,我才恍然悟出女孩在那半年多的岑寂里,是那些老鼠在陪著她……我蹲了下來,在淚雨掩面中將死鼠揀了出來,塞在女孩手里。我知道,我改變不了女孩在彌留日子里破碎的凄涼,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病痛和人性的那種丑惡一點一點地蠶食掉她脆弱的夢想。也許,這是我對無助的女孩的惟一一點慰藉。
女孩握著死鼠緊貼著臉頰,久久不放。我忽然發現鼠死后的面部很安詳,嘴角猶帶笑意,我不知道死鼠為什么會有這種表情。但我確信它飛天的靈魂中潛伏著一種具備了神力的東西。我看見了女孩浸在鼠聲吱吱里的一臉燦爛,我聽見了女孩在風雨中微弱的呵呵聲……
二拴已打開了我們帶來的飯盒,端到了她嘴邊,用飯匙喂她的時候,她的嘴巴一直緊閉著,眼光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不耐煩了的二拴就一拳打在了她的鼻子上,隨即便有淡紫的血從她的鼻孔涌出。女孩的呼吸變得粗重了,發出了人臨死時的那種哈啦哈啦的聲音。這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最慘痛的一幕,從此以后,我的心常常如鞭抽過似的疼痛不已。
我感到臉在扭曲,頭腦昏昏的,哆嗦著手一拳砸向了二拴。二拴抱著頭一屁股跌在地上干嚎起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這才明白過來我是為了一個弱者把拳頭砸向了另一個弱者。
窯內陽光如簫聲流動,它該是惟一能包扎女孩傷口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