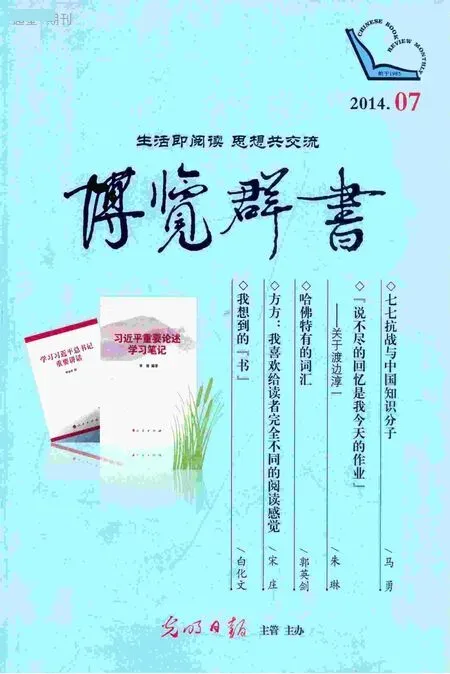滇西北文明:正被揭示的與將被毀滅的
老 峽 蕭亮中
問(老峽):首先祝賀你的新作《車軸》問世。記得在2000年,《南方周末》地方版曾發表過你的一篇題為《車軸村風俗觀察記》的文章,為讀者提供了關于車軸村的一個小片斷,而《車軸》一書又寫到這個村落。你是如何想到這一個村落的?
答:(蕭亮中)云南中甸是我的家鄉。我從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學習人類學后,我更是發現這樣的文化形態在西南一帶是一個很普遍的類型,而這又與移民和土著、中央和邊疆政治力量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系。還有,在新時期,這樣一個小村落對全球化的反應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類學的慣例,我照例要選取一個村子做調查,從民族志的角度來以小看大。就我個人來講,我首先是一個當地人,但又有著異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經歷,并經過一定的人類學科班訓練。我想,自己能不能嘗試去跨越“外來者”和“當地人”兩種不同的角色?這種嘗試也包括去跨越外來人類學者和本土人類學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問:你覺得你做到了嗎?
答: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離和客觀化的同時仍然有一種親切感。人類學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參與觀察。參與觀察其實就是一種學文化的過程:調查者要不斷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這樣才會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認為這很容易做到,因為一個調查者進入社區,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生理、價值觀這樣一些變化,而我一直認為這些對我是應該沒有障礙的。
問:我認為你是在城鄉之間自由地穿行……
答:可以這樣說吧。但盡管我在語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進入當地社區,但我還是覺出了自己的不適,像價值觀這類東西,我就已經與當地人有了很大的區別。這一點我起初也沒有想到。
問:你畢竟從金沙江邊走出來一些年頭了。
答:是吧。我在適應城市的同時也與鄉村發生了一定疏離。所以,我也一直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就拿訪談內容來說,我設計了框架,重點設計了一些很感興趣的問題,但當地的老百姓卻覺得有些問題沒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無法回答;而他們覺得有意思的,我卻又一直在熟視無睹。
問:我覺得你還是最大限度地走了進去,對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實描摹。我想這是不是與田野調查的方法有很大的關系?你在書里一直強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似乎有一種學科“準入證”的味道。我想問這里的田野調查有什么具體要求和規范?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各種對文化的探尋方法和田野調查的區別?
答:這里有個前提,作為民族志來說,如果我們從“記載”這個層面上來理解“志”,那就應該是完全真實的,是對地方文化的實錄。但盡管這樣,學界對人類學作品的真實性爭論還是由來已久,個別人從田野調查資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會受到其他人的質疑。客觀地講,每個人從自己角度出發的研究其實都先天地帶著自己獨特的視角,這樣的視角表現在作品里,也是對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詮釋,但這樣的詮釋是要能自圓其說的。學者認知文化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但人類學有一套獨特的手段,那就是嚴格要求通過田野調查來獲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調查也被稱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如果是在這個層面說,它被稱為“準人證”也未嘗不可。田野調查有一套嚴謹的規范:包括與被調查對象住在一起,學習、使用他們的語言,參加日常生活,建立社會關系,還要隨時隨地進行單調、費時的觀察記錄。更為苛刻地是,由于調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地方族群進行縝密觀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對調查時限都有著嚴格限制,這就是至少要求調查者在被調查社區度過不少于一個年度周期的生活。
問:這樣看來,人類學家與記者采訪和文人采風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絕不是到處跑來跑去,而是要能在一個地方長期呆下來,集中精力應付瑣碎的日常生活。
答:當年就有個叫霍滕斯·波德馬克(Hortense Poudermaker)的人類學家在《陌生人與朋友——一個人類學家的心路歷程》(Stranger and Friend:The Wayof an Anthropologist,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66)一書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亞萊蘇島田野調查的故事。她說盡管身體健康,資料收集也越來越多,但實在無法忍受貧乏無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當兩個陪同的人離開時,自己就像獨處的魯濱遜,甚至還沒有仆人“星期五”。確實,田野工作有一點顯得非常絕對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復一日的參與觀察中,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人性與文化。人類學的作品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會不斷地反觀自身,對自己遵循的文化體系提出質疑、修正。這和書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這也可以被視為人類學人世的一種表現。
問:讀《車軸》一書,我覺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對當地“家號”的總結就非常有意思。
答:家號是我在車軸田野調查中比較得意的一個發現。這要感謝當地幾位非常關鍵的報道人。家號是至今仍在當地民間使用的一種與漢姓、家族不同的認知體系,這方面的研究尚無人觸及。家號對住戶畛別有著明顯的標識作用,這類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個層面與姓氏截然不同。簡單說,家號是一些原生態和直接描摹的沒有經過修飾的標識符號;而姓氏則是經過簡約、抽象化的畛域系統,即便這樣的畛域性也有逐漸模糊的趨勢,就像民諺所說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這樣相反的提法。還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緣群體上,除特殊情況,一般不會因為遷徙或者其他原因改變;而家號相反,即便住戶遷徙或另換屋基,家號也不會跟著“帶走”。車軸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原住戶遷走后,新到戶往往承襲了原住戶的家號,接著喚作“某某家”。
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這種限定發生了變化。這與改土歸流后漢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對傳統家號體系的影響相關。納西族家號是一個綿密而又系統的認知體系,在漢姓進入納西社會之前,社區完全靠這一套系統區分自己與他者。漢文化或者說是姓氏文化和漢人的家族觀念進來后,這一套體系曾有過積極的文化調適。像對早期遷到當地的客籍戶,一定會對他們冠以一個家號,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陳家”這樣的漢姓稱呼。
因此,接下來就有大量的“家族襲奪”現象發生。家族襲奪讓家族制與家號系統相互作用,但雙方并沒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結果是一種互補;只是相對來看,家族更為彰顯,而家號則相對隱性一些。襲奪現象讓我們看到父權制的發展對一個地方社區文化習俗的巨大影響。可以說這是一種巨大的但又隱身于日常實踐中的潛移默化的力量。
問:你這里的襲奪概念是從地理學借用過來的。你是怎樣把兩者關聯起來,并提出這樣一個新概念的?
答:說來有意思。我在車軸村調查了一段時間,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也接觸到了大量的這一類個案。這時我感覺到自己可能會有一個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鎮趕集。石鼓在江邊一帶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張整個長江第一灣的片子。我在對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幾個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幾乎是爬到了那一帶最高的一座山頭。我見到金沙江以石鼓為中心,繞一個“V”字型大拐彎轉而北上。我為長江第一灣的地貌震撼了。這個地貌曾長期被解釋為河流襲奪。有了這樣的意向,我回到車軸后就自然地將家族結構變遷中奪取承祧、財產甚至家號、屋基等有形無形資源的現象與“襲奪”概念聯系到一起。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襲奪家庭發生了承祧斷裂,它重新續過襲奪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際序列的記憶,而這又與襲奪河和被奪河的特點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將它與河流襲奪的各個概念一一對應起來。很多被襲奪家族消失了,但它們的一些特征會保存在襲奪家族中,形成一種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襲奪發生后,我們可以在斷頭河的河谷形態沉積物中覓見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來,很多調查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問:讀這本書,覺得文本上同樣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你不斷地穿梭于故事內外,從作者到讀者都能共享文本的內容。你在作品中也沒有一味地追求標準的論文寫作,也不像時下流行的散寫體,一抒發起感覺來就開始無邊無際。你的書里既有對話、雜感、隨筆,同時也有標準的結論。
答:我是希望能盡量給予讀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觀的素材,引發讀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體轉換的嘗試,這樣的努力確實還等著讀者們的批評。
問:你把車軸村的變遷概括為自在社區、新邊疆和后革命這樣漸次推進的過程,而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國家、國家和全球化三個不同時期。你是怎樣得出這樣的結論?
答:在對車軸的歷史進行剖析時,我對改土歸流進行了很細致的考察。這樣的事件在正史中是從權力中心外延的單維向度來思考。其實改土歸流對西南一地的影響非常巨大,它帶來的文化變遷和文化調適仍然影響到今天的當地族群。對車軸這樣的村落來說,它的影響力恐怕只有1950年和平解放才能與之相比。所以,我從這兩個時間點上就基本上可以看出前后變化的不同;從國家力量的介入來觀察,它基本上又與變遷過程有著重合與不重合的地方。改土歸流后進入一種新邊疆時期的同時基本上也就邁入了國家控制時段;一直到1950年和平解放,新邊疆狀態才告結束,但國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續,直到今日在本質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變化。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權力開始進行地方自治的嘗試,這就是車軸村2001年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另外,與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樣,它同時也開始面臨著全球化的壓力。所以說,從村落來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經開始走向兩極:一端是國家繼續控制,另外一端是對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漸感受。從對村落的觀察、村民的言語里,我們時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車軸這樣邊遠的傳統村落,也已經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種超出國家力量的外部勢力存在并且開始作用……
問:在具體的事情上有什么樣的表現呢?
答:具體地講例子很多。像中甸縣對“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對東方、對前工業時代的一種想象。現在,就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也將自己目前的處境與所謂的“國際”、“外國”聯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說,一些替代確實是在悄悄地發生。全球化不是一種想象,而是真真實實的一種力量,并且已經切人到傳統中國所謂的草根社會深處。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他也以通過這種表達獲得他在其中的權力想象,也可以說他會敏銳地利用其中的關系來進行一種類似討價還價的交換。當然,就目前來說,尤其像中國,民族國家的范疇格局確實是抵擋國際上不平等交換的一個屏障,應該說這樣避免了草根社會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壓力。應該說草根社會、民族國家和全球化力量三者之間有一個微妙的關系,并且逐漸抵達互相制衡。但我想,他們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其實,國家也開始在向基層草根社會讓權,比如車軸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就是這么一個具體的過程。盡管這樣的嘗試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會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像車軸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團體集結的趨勢;但我對這樣的開端仍然非常激賞,有時候,不同利益通過一種程序博弈也是一種公平的游戲,最后的結果會是一個中和各方面意見的雜合體,這也許會更接近民意。通過我對車軸村的追蹤采訪,新的班子確實也在有效地實施一系列工作。確實,這樣的事實也讓我改變了原先對選舉結果的消極觀點。
問:但農村還有更多的問題,像車軸這樣位于邊疆,備方面原生態保持更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會與內地同構的。
答:在很多問題上,不管邊疆、內地還是不同的民族,中國的農村具有相當的同質性;當然,像車軸這樣的村子會比內地農村慢半拍,矛盾也會相對弱化一些。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呢?我想歷史終結的一個過程表現——戰爭、革命將不再是
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辦法。這不僅僅是因為上面強調的力量懸殊過大,這也與政府權力逐漸縮小,不再像過去一樣幾乎可以毫無顧忌地做各種事情密切相關。
問:政府應該與民眾商量,建立一個合理輸導和耗散的機制,但事實呢?
答:事實要復雜得多。就在離車軸不遠的村子,1997年由于鉛鋅礦開發導致水資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擁進鄉政府把鄉長捆了。
問:比較激烈?這樣的事件在歷史發展中怎樣定位呢?
答:不管歷史最后是“最后的人”還是“共產主義”,它總之是要走向“終結”的。人的活動不同,這個過程也會多種多樣:可能較為平緩,可能通過戰爭、暴力。當然,過程不同,最后的結果也一定會有很大的區別;甚至,這個終結同時就是毀滅。像車軸這樣的小村落,在這樣的過程中它是被徹底侵蝕掉,還是保留自己的獨特性作為一個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預設,如果進程被人為打斷,這個終結過程無疑會增加很多危險性,會走上無法預估的彎路。
問:現在有這樣的危險嗎?
答:我當然做不了一個準確的預計,但我一直在對車軸村做追蹤調查。去年7月份,滇西北的“三江并流”自然景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車軸村和沿江一帶都包括在內;而我聽到的消息卻是:當地正在醞釀虎跳峽大壩的修建,并說已經有了規劃,很快就要上馬。這類信息越講越多,鄉間已經開始有了恐慌。
問:這顯然有悖于自然遺產保護宗旨,這樣一塊接近原生態的地方,保持它恰恰是對地球最大的貢獻。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沒有任何解釋?
答:至少我沒有聽到。
問: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庫的“經驗”,先不做聲張,不吸引媒體的眼球,暗渡陳倉?
答:在開發的名義下,有時自然遺產的名頭只是一個對外的廣告語。中甸就有這樣的說法:申請“三江并流”搞錯了,現在做什么事都縮手縮腳的,放不開,還談什么發展?另外,1997年電力系統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離,能源部撤銷,成立了中國電力總公司。現在公司化向進一步縱深發展,國家電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當然就來到西南圈水圈地,讓大自然成為他們公司的資產。這是一種典型的公司行為。
問:完全聽不到政府的聲音?
答:至少目前是這樣。政府應該把一切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眾,包括現在是怎樣一種運作方式,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要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最終決定是否修建大壩的應該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眾。地方民眾要和電力公司進行平等對話,在知情、沒有壓制和利誘的情況下商談,因為地方民眾在對話中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而現在,他們的聲音一點也聽不到,現在的聲音都是那些受益群體,地方民眾還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沒有參與進來。
問:其實商業上以效益為目的的河流開發,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建壩最大的問題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在這樣的商業行為中,地方民眾這樣的弱勢群體只會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貧困,像云南省漫灣電站建成后,當地群眾并沒有像當地政府承諾的那樣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現實情況是越來越貧困,甚至還不如建壩之前的生活。
答: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現在江邊的老百姓告訴我,已經有人來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積,但還是沒有一個說法。我與當地的一些報道人是經常溝通的,他們很緊張。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應該會知道得多一些,可我又能說什么呢?我只能寬慰,說“相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