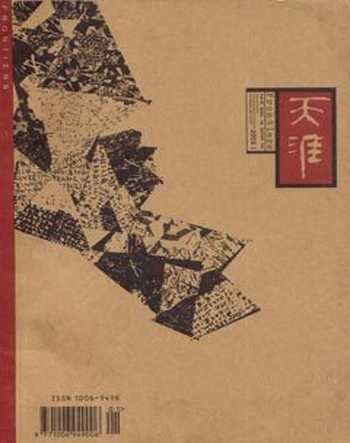自我檢討書(1952)
開場白
思想改造,當得自動,不能被動;不過人類通病,自屎不覺臭,旁觀者清;所以發動群眾,幫助自己改造;最好自己不要掩藏自己的思想,欺騙群眾,得到通過;寧可通不過,將我心里癥結所在,赤裸裸地給群眾看;通過,固好;不通過,正好鞭策我自己的反省!我現在檢討我自己的思想,不過有些思想,根源知識;有些思想,涉及環境;所以檢討不能不涉及多方面。
(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過不放棄我中國人的立場。
人家說我思想頑固;其實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從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過不容許我放棄自己是一中國人的立場,這是無可諱言的,而且我自認為當然的。
我祖父教書,我伯父和父親教書,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親哥哥都教書。我從小跟著我伯父和父親、哥哥讀書;因為我祖上累代教書,所以家庭環境,適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熱烈!我十一歲,讀完四書五經不算,加上《周禮》、《爾雅》、及《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綱鑒易知錄》,自己當小說看過一遍;下年十二歲,碰到戊戌政變;我父親要我知道一些時務,定《申報》一份,每日晚上,督我自己用朱筆點報上論說一篇,作余課;偶爾我哥哥借到人家看的《格致新報》,乃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發行,月出一期,中間登著嚴復譯的赫胥黎《天演論》;我讀了,覺得耳目一新;從此對于生物學,自然科學發生興趣。有人告我“研究自然科學,必懂算學”。然而閉門家里坐,無師傳授!我和我的弟弟商量自己學;向母親要錢,到書鋪買到《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幾何備旨》及《八線備旨》四種;所有習題,通通演過;如有題演不出,則和弟弟兩人相互咨討;從此舍棄經史,認為不切時務;而一心想研究科學,然而苦于無錢買科學書看!有時即瞞著父兄,取家中藏的經史,到書鋪去換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種物理化學書看。從此求知之范圍,推而益廣。戊戌亡命客及國內留學生在日本出版各種雜志,亦時向書鋪借著看;梁啟超《新民叢報》,尤合口味!那年壬寅,我年十六,讀了梁啟超作的《中國地理大勢論》,殊未滿意;因為梁氏譯日本人著的一篇論文,而自己附一些意見進去。我就拿自己的意見,做了一篇《中國輿地大勢論》寄去,約四萬多字,在癸卯年《新民叢報》登出,連續了四期。梁啟超且給了我一封信,鼓勵我。因為我看到西北地方文化,自唐以后,停滯衰落,講到東南文化,受之西北,當還以灌溉西北;不免說得過火,惹起于右任的怒,和我打筆墨官司。那時,上海交通大學,先叫作南洋公學,早已開辦。蘇州成立高等學堂。我父輩裘葆良先生,勸我父親送我兄弟去投考。我父親因為負擔我兄弟兩人學費,不免太累;躊躇。我兄弟亦知道家庭的經濟,不敢要求。我們那時做青年,不比現在青年,能夠得到社會的重視,政府的照顧;所以我始終未受到學校教育。一切知識,只靠我自己力量去追求。我當時應《國粹學報》的征文,得到銀幣二十元的獎金。因為我讀了同鄉丁福保著的《東文問答》一書,略懂一些日本文;就拿這筆獎金,寄到上海日本書店,買到許多日本文自然科學書,約二十多冊;其中最大者,為飯盛挺造《物理學》,三厚冊;三好大《植物學》,兩巨冊。我自己看,日本文尚無大困難;而內容不夠了解;尤苦于物理學,得不到儀器實驗!我姊丈曹仁化約我組織理科研究會,糾合同志四十人,每人出會費四十元,買儀器,請講師。華實孚先生講物理和化學;顧紹衣先生(中國最早研究飛機制造之一人,民國元年《東方》雜志登載先生飛機論文許多篇)講動植礦物和地質學;皆吾鄉老理化會員。教本用日文本,由會員與講師協定;物理學即用飯盛挺造本;會員不懂日文者多,指定我譯成中文,用謄寫版印發。會員年齡最高者,四十多歲;我年最輕,每日聽講六小時;晚上譯日文,有時亦替會中同學,補習代數幾何;原定兩年畢業,無寒暑假,后以教材多,延長半年;第一年會費四十元,以買儀器不夠,加繳十元,共五十元;我母親允許替我出。第二年,因為里中大姓薛氏請我教兒子算學,每日下午去三小時,有月薪二十元;我可以自己出了!那時,我年十九歲,從此打開職業的門,直到現在六十六歲,總算社會照顧我,沒有一天許我閑過。我沒有一天失業,我也沒有一天不配合著我的職業,開拓我的知識;有的伴著當前的環境;有的跟著時代的演變;我把握住時間空間,從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過我先天是中國人,我有我深根固柢的民族文化素養;一切新事物,我有我中國人的看法。譬如“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罷!我們古人說“專欲難成”,又說“謂人莫己若者亡”,就是教我們走群眾路線,不要“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又如當前三反運動,我給朋友的信說:“二三十年前,我和人家講:‘不貪為寶,‘儉以養廉,‘集眾思,廣眾益,這一切話,無不看作老生常談;而今乃給吾們以人生之現實體驗!”我們子孫不肖,我們祖宗何嘗容許子孫做!新社會何必不與舊道德一致!我們不要拿外來沾染之民族污點,就看作先天之“民族文化”;充分認識我們的民族文化,我們民族乃有前途!我們現在貪吃懶做,生活腐化;如果我祖宗早就如此,必然絕子絕孫,早經人種淘汰,必不能有四千年之悠久歷史,牢守著一萬多方哩之廣大地產;所以我從不看輕自己一個中國人的立場!
我的思想,和胡適思想不相容;而毛澤東思想中,未必不容許存在!胡適主張全盤接受歐化;他的考古學,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只有降服之一途;絕不承認民族文化!然而民族文化,在毛澤東思想中,有其相當立場;毛澤東集人人讀,不必我多談!
我認為社會主義,須看作民族文化之復活;而后社會主義,乃在中國深根不拔;國際主義乃與愛國主義結合!此中存在許多矛盾,當然有;然而矛盾之中,要理會到統一;毛澤東矛盾論,也曾明白指示我們。
(二)我的社會意識很濃厚,而革命性則缺乏。
也有人說我不近人情,因為我不容易和私人妥協;尤其不受人抬舉,人家不容易親近我!其實我的社會意識很濃厚;我不甚沾戀自己利益以出賣自身,出賣社會;不過我缺乏革命性,當然也有我的因素。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年二十三歲。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讀了我的文章,認為我青年可以有為,就托我同鄉廉南湖先生介紹,邀我到江西去籌辦司法改良。我一到江西,看到司法黑暗重重,省城發審局刑訊酷濫;按察使署刑幕把持。首席刑名老夫子陳繩之,徒子法孫,播滿全省各府各縣;府縣人民上控案件,幾乎無一準理!陳繩之因為我是陶臬臺特約的人;我一到,就來看我,和我商量,案件不必過問,各府縣一年四季節敬(端陽中秋,冬至和年)分我一股。我當然堅決謝絕,恐怕他心里不安,告訴他說:“陶臬臺約我來,商量司法制度如何改良;并不要我問案件。老夫子辦案辛苦;府縣節敬,我如何敢分潤!”因就和他商量司法改良,當前從兩事下手:一停止刑訊。一改良監獄。他一口贊成。我草一說帖,上陶臬臺。陶臬臺人極長厚,認為積習難挽,然而不妨做;商量先從省城發審局做起。發審局提調,系南昌府知府;我的說帖交去;發審委員一致說:“刑訊停止,供無從問!”此事就告擱淺!我退一步,想專致力于監獄改良;我去看新建縣知縣梁某,請求參觀監獄。梁知縣陪我巡視一周;當然講不到“人道”兩字;然而我覺得走馬看花,不夠了解;因為典史管監獄,典史衙門就在監獄旁面;自己請示在典史衙門住半月;吊監犯名冊,每日提一兩個犯人,隨便閑話。梁知縣大不安,早晚來陪我談天。我勸他回去治事,不要陪我。他不肯。住了三天,我也只得回去,見陶臬臺,告以所見。陶臬臺惻然,籌了一筆經費,并且自己捐了二百兩銀子,交梁知縣,吩咐他:“監房一律離地五尺,鋪木板。監溝淤塞,一律開浚。”梁知縣亦捐了俸銀一百兩。又指名一老犯人,所謂龍頭者,以其虐待同犯,無惡不作;由梁知縣自己吊案重辦,詳申改徒為流,充軍到邊遠地方去;講不到如何改良,暫時減少一些殘酷!到了明年,陶臬臺死在任上,我也就回家鄉;然而問刑衙門之刑訊不人道,深深埋在我的心頭!適江蘇諮議局成立,同縣當選議員七人;我就致書請他們提案停止問刑衙門刑訊以重人道。諮議局方在準備提案;而我有個表兄孫鶴卿,年齡大我十五六歲;他鄉下倉廳,吊打佃戶兩人,致傷。我寫信告訴他,認為不對,勸他約束管事,撫恤佃戶,養傷退租。他置之不理。我發怒,叫受傷佃戶到縣驗傷,告他的管事孫渭波。當時無錫縣知縣趙某,不知道孫渭波是孫鶴卿的管事,驗準傷,就出票拘提。孫鶴卿是浙江候補道,在鄉,任信成銀行經理,無錫縣商會會長。我舅舅及表兄表弟,京官、外任官都有。趙知縣當然不得罪于巨室,知道謂波是鶴卿管事,出票是拘錯了人;然而佃戶傷已驗準,案無法銷;就一面將案擱,一面托人向我疏通。我說:“我非和鶴卿一個人下不去;我要使一般豪紳,明白佃戶亦有人權,私刑拷打之非法!”我就聯合常州府八縣同志,呈請江蘇巡撫程德全,申明法律,嚴禁各大姓倉廳私刑拷打,通飭各縣,勒石永禁。程巡撫批準行縣。我就據了到縣催審。辛亥革命起了,我的朋友秦效魯起而組織無錫軍政分府,招兵一團,軍餉須有人籌,邀鶴卿出主軍政分府財政部,代他疏通,居間仲裁,退佃養傷結案。
軍政分府,最初我亦參與,然而革命雖然成功,人民并未抬頭!一般國民黨員,暴橫不可以理喻,視舊式紳士尤利害!所有地方惡霸,爭求入黨,作護身符;一隸黨籍,言出為憲;良懦惕息,惡霸抬頭;軍政分府的人,欲得黨為后盾,又多藉手假公濟私,勾結一起。我一開口,就說我不革命,乃至殺人不問供;以農民抗租,派兵下鄉,強奸女人;鄉民抬婦女入城喊冤;兵士攔阻不許。我入告秦效魯,雖派軍法官出驗婦女的傷;而以革命軍人,含胡了事!秦效魯疑我別有作用,私交因此大傷!我就自動退出,覺得革命并沒有像理想一般美妙;革命仍是以大眾的痛苦,造就少數人的地位與煊赫;革命情緒,從此萎縮。我回家,閉了門,研究法國革命史,要看看外國人的革命,比我們怎樣。乃知道一樣糟;法蘭西文明古國,并不高明許多。我的弟弟得到兩大冊張東蓀譯的《美國平民政治》,送給我看,其中說到美國選舉費消耗之龐大;民主共和兩黨爭取選舉之花樣百出,大資本家之把持選舉,非法圖利;以及地方小政客之販賣選民,弋取一官半職;舉國若狂,真非我一個中國人所能想象;然而中國命則革了,民主前途,實不能想;當日只想自己少造孽!到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陸軍總長黃興,以張勛蟠踞浦口,任我同鄉顧忠琛做援淮軍總司令,派人到無錫邀我去代理副官長;后來南北議和成功,援淮軍改編陸軍第十六師;我仍原職,隨司令部移駐鎮江。蘇州周怡春持國民黨黨員證,來司令部,征求入黨。我意稍躊躇,欲考慮黨綱一二日。周怡春肝火甚旺,驟然發怒,說:“你不依我簽黨證,以后沒有你的地方吃飯!”我也怒,應道:“革命僅為自己混飯吃嗎!”怡春憤然帶著黨證走!我當日看到革命軍人嫖賭腐化,不問軍政!陳其美是個革命領袖,做滬軍都督,而有楊梅都督之稱,恬不知羞!即就我自己在十六師說罷!副官處稟承參謀處,而參謀處常常無人;一到晚上,司令部只有衛兵,守著幾十間空屋!明知軍佐非我本行;不過既然做了,也得做一行,像一行!我向師長獻議,參謀官值日;然值日參謀官,也往往跑掉,無法接洽!我心中實在氣悶;我就拿著日本參謀部頒發一本“參謀須知”小冊,乃一日本留學陸軍朋友寄給我的;我就譯成中文,送給參謀長李竟成看,擱在他桌上半個月,未揭一頁!我就自動取回,添入一些中國兵家理論,改題做“參謀論”,寄上海民立日報,登載了半個月,頗有些反應;然而來通信者,都是些非軍人;足見革命軍人在當日,并不認為打仗要什么學問!后來宋教仁被刺,江南革命空氣極濃。有一天晚上,顧師長在公館來電話招我去,問我意見?我對:“第二次革命不免;不過勝利無把握!”師長問:“何故?”我說:“別省不知道!現在江南營連長以上軍官,有些非軍隊出身,作戰能力本差;有些軍隊出身,而是從前第九鎮新軍目兵,因為參加革命提升;從前執槍,能夠發槍;發一粒子彈,殺一個敵人;而今握著指揮刀,并不能指揮,而發一粒子彈之用也失了。”師長默然。既而江蘇都督程德全改編江蘇陸軍,成立三師。第十六師司令部取銷了;我調都督府差遣,其實回家閑住;不過每月須到南京應一次卯,領薪;我覺得這不是事;我索性呈請都督府,開去差遣職務;另做打算。回家不兩個月,第二次革命發動,立即失敗;袁世凱成了一世之雄,唯我獨尊;南方政客,紛紛到北京去活動;直隸都督趙秉鈞,不知聽了什么人話,忽而來一函,聘我去做秘書。當然我非國民黨;黃興之以我江南發動第二次革命,鹵莽滅裂,自己一走了事,地方受累無窮;在我江南人心里,當然恨;然也未必就愿向袁世凱服輸;除非混飯吃。我想飯吃,我不愿混了吃,就回信謝絕了!然而我當時,年未三十——二十七歲,上有老父,下有一妻兩子,手頭無一些積蓄,目前一家吃飯,亟須打主意!我當日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在本地當個紳士,地方上亦尚有人信用。一條路,靠我筆下尚來得,外間也有人知道,投到北京去活動,做一小政客。不過我覺得我自己有些危險性!我身體不健康,膽氣也不夠;不過我有些小聰明,能用吾腦,碰到一些事,能夠正反面看,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萬一被人利用著我打歹主意,我將誤用我的聰明害人!所以我決定選擇一環境,限制我的用腦,沒有機會打歹主意;還是教書!恰巧我的朋友沈西園,是我理科研究會同學,在無錫縣立第一小學教國文兼理科;中途有人邀他到江蘇高等審判廳去當書記官;學校的聘書須到暑假期滿,要覓一人代課,每周授課二十四小時,兼一級任,月薪二十元;來和我商量。我欣然答應;從此做教書匠,回復我祖父三代老本行;其時為民國二年十二月,直到今天,歷小學,中學,師范以到大學,總算教課沒有什么講不下去;有些學生覺得我頑固,然也感到我認真勤懇,和我親近;我對學生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可我犯著錯誤,決弗口不應心!
我極愛護所在之學校,然而決不顧戀自身在學校之地位和利益。茍其和我中國人的立場有抵觸,我沒有不決然舍去。其一,為我之去上海圣約翰大學。圣約翰大學,系教會大學;我進圣約翰,因為孟憲承先生邀我。我和孟憲承本不相識;孟憲承在中學生時代,讀過我寫的辛亥革命軍人“吳祿貞傳”;又聽得人說我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教國文認真;就到無錫來看我,說:“江蘇省教育會黃任之先生,參觀南京上海各教會大學,認為學生認真讀英文,而國文課絕不當一回事,幾乎忘掉自己是哪一國的人!國文教員,也有若無;向各教會大學校長提議整頓國文課。現在圣約翰校長卜舫濟,邀我去當國文主任。我想非得一位于國文有堅強自信心,不怕和學生麻煩者同去,恐風氣不易挽轉,幸勿見辭!”我當日聽了,認此一問題嚴重,一口答應去。及到圣約翰,一上課,方才知道學生上國文課,只自管自手里拿一本英文書讀;國文老師,則在教臺上,攤一本國文,低著頭,有聲無氣的自管自咬文嚼字,而絕不過問學生手里拿的書,是國文,還是英文?乃至點起名來,則正襟危坐著,叫:“密斯脫某”!“密斯脫某”!一六十多歲之老孝廉公,也不能例外。不但學生忘記掉自己是中國人,即國文老師,也自己忘其所以。我第一堂點名,不喊“密斯脫”,學生便覺聽不慣。有些學生,一聽自己名點過,便出課堂,自管自去!我想我不和學生先申明約束,我不決心和學生以去就爭,我如何教得下去。明天第二堂,我不點名;我開口第一句問:“諸位!請問是哪一國的國籍?”學生目瞪口呆,無一人對。接下去,我就說:“諸位!毫無問題是中國人;然而諸位一心讀英文,不讀國文;各位的心,已不是中國人的心!我聽說諸位到圣約翰讀書,每年花費須五百多元;我想諸位家里,花了五百元一年,賣掉你們做外國人!我想諸位祖宗有知,在地下要哭!我今天已不是圣約翰雇聘的一個國文教員;而是一中國父老的身份,看你們作子弟,挽你們的心,回向中國!我想你們不愿,也得愿;因為你們身里有中國人的血!”我意氣憤昂,聲音愈說愈響;而學生仰面朝著我,寂然無嘩!我知學生心里已感動,就提兩點:“一,以后上國文課,不得帶英文書;如帶,我必沒收,送教務處。二,本系系務會議,議決我開文學史一課,提起諸位興趣;我不想講古代文學,惹諸位的厭;我想講近三十年文學演變以到胡適,其人皆現在;而姓名,皆諸位在報上看到,必能發生興趣;然而舊演變,形形色色;中國四千年文學之演變,亦可縮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諸位如贊同,舉手!”四十多學生,一齊舉手。上課不到一個月,學生興趣大增,常常帶著講義到我房間來,覺得聞所未聞!我寫現代中國文學史,就是在圣約翰時起手。那時,上海有四個大學,代表“嫖”“賭”“吃”“著”四字;圣約翰大學,沾“著”字;學生無不西裝筆挺。冬天,有一學生穿新大衣,華貴異常;許多學生圍了他問價;他得意地說:“伍拾元!”我見了,就笑說:“一個人伍拾元;如果同學每個人看了樣,做一件;現在圣約翰大中學同學,合八百多人,積少成多,西服店很是一筆生意;然而一切材料,來自外國;圣約翰學生,就變成外國貨的推銷員;一天一天下去,我們中國就不行了!我們在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要學他的科學,不要學他的生活;學他的生活,我們自身就成本國漏卮!”也有學生穿了西裝,和著我說以為不錯!我很高興,覺得一個人的國民性,終是不可汩沒,只愁沒有機會啟發。我在圣約翰,第一年聘書,一年期滿;到了暑假期近,送來聘書,續聘三年。然而開了年,是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起,英國工部局開槍打死許多手無寸鐵的中國人;那時,我對于政治,實在不感興趣;不過那天我恰路過工部局,看見中國人的血汩汩沾衢;三道頭帶領著印度阿三,三三兩兩,騎著馬,背了槍梭巡,耀武揚威;心中有些氣不過;然而回到校,中國同事相看著不發一言!明天是六月初一,我早起第一堂有課;上堂,我第一句開口,就說:“我提議我們今天靜默十分鐘,自己想一想!我們中國人講孔孟之道,不過‘仁‘義二字!現在我們眼看著許多自家人無緣無故被打死了;我們自管自讀書,心里沒有一些同情;不得算做‘仁!我們眼看著外國人打死我們自家人,不開一句口,不伸一伸手;‘義氣何在!”午后,學生會通知教授會,響應本埠各大學,一致罷課。孟憲承召集國文系同仁會議。孟憲承說:“就教師立場說,斷無贊成學生罷課的道理;然而就國家立場說,豈有坐視我們自己人,被外國人殺死的道理!”我應著說:“禮,大功輟業;輟業,就是讀書者不讀書,辦事者停辦事;大功,是從伯叔,從兄弟死了,服九個月的喪。現在我們同胞被外國人殺死許多,至少比得從兄弟,從伯叔的喪;我們罷課表示哀悼,也是理所當然!”到了晚上,卜舫濟校長召開教授會;國籍教職員,無一開口;只聽得英美同事操著外國語,意氣揚揚,咭咭呱呱。我起立說:“工部局這件慘案,關涉到我們中國人許多性命;我一個中國人,有權利要求知道究竟什么罪名!外國先生的話,我不懂;我請求校長指定一人翻譯給我聽!”有一美國人激昂著說:“圣約翰在英國工部局管轄之下;如果容許校內學生宣傳反英,這是叛逆行為!況且中國人一碰到匪禍兵災,就逃到我們外國人租界里來;也當得共同維持租界的治安!”我聽了,實在受不住,就起立說:“我今天要操我們的國語,說我們中國人心里所要說的話!我們中國人,手里沒有一根槍;在英國工部局門前,殺死許多,尸橫血流;假使這件事發生在你們美國;你們美國人,恐怕早已和英國人打起來;決不像我們中國人沒出息,現在還在這兒請求您卜校長答應罷課!卜校長和在座諸位外國先生,都自認是中國的好朋友;然而我們中國人被英國人殺死許多,連我們喊一聲冤枉都不許!我們不敢自己忘記是卜校長聘任的一個圣約翰教員;然而尤其不愿忘記自己是一中國人!我請求孟先生翻譯給外國先生聽!”孟憲承一面翻譯,一面揮涕。國籍同事,亦漸激昂,紛紛發言。然卜校長堅持不許學生罷課!其后投票表決,三十一票對十九票通過罷課。然而卜校長又聲明:“校長有自由處分校事之權,絕不受教授會的議決案束縛!”中間幾經波折,終究學生散學,成立光華大學,都見報紙,不涉我個人思想反映,而表示我所以脫離圣約翰的理由。其次,我之脫離清華大學。清華,是美國退回庚子賠款辦的;原系留美預備學校,那年,籌改新制大學,就招孟憲承和我一同去了。清華的洋化生活,和圣約翰一樣;而同事的拜金主義,尤其嚴重!同事談話,公開的計較薪水多少,卻是我到清華第一次聽到!有一次,曹云翔校長,因為校中醞釀風潮,召開教授會。同事紛紛發言,有一位聲訴薪水的不平。我當即說:“我們不要談薪水!我們的薪水,是美國庚子賠款;庚子賠款,是全國四萬萬人,吃了許多苦的血債!我們拿來受用,心里本覺得難受;少拿些,少擔些罪孽,也心安理得!”薪水問題,會場上就算一句話抹過!散了會,我就拿這一層意思,寫信告訴我弟弟,并且附加幾句話,說:“現在讀書人,眼睛只看見錢;不問錢的來源,干凈不干凈!這樣惟利是圖,從前人講的‘見利思義,沒有人肯去思;只要有人給他錢,一切可以做;照此下去,中國前途,不堪設想!”不知道怎樣,上海申報附張自由談,將我信里這一段話登載了!有一天,在校內工字廳,碰到余日章的弟弟余日宣,就指著這一段自由談問我?我知道此君心地極厚,并無惡意;我就向他說明我的意思。余日宣也以為然。那(哪)知后來有人告我,曹校長因此很不痛快我,且囑向我致意,不要發不利本校的意見。我就答:“很容易!曹校長認我不利本校;我到暑假跑就好了!我也知道現在全國大學的待遇,沒有一個比得上清華!這一只金飯碗,沒有人舍得拋;我有決心拋給曹校長看。”到了暑假將近,校長室送了續聘三年的約書,我就退回了!校長室送了三次,我勉強接了;然而我一回到南邊,我七十八歲的父親死了;我心里悲哀,我決心不去了!后來我知道曹校長很后悔。這是我脫離清華的所以。最后一次,是民國十六年暑期,從前南京的東南大學,改組第四中山大學,校長張乃燕招我去當國文系主任;我住了半個月就走;外間尤莫名所以!我和張乃燕一面不識,到今未見一面;突而一次兩次的信來,招我去;最后托孟憲承君(當時任第四中山大學秘書)致意;我同鄉胡剛復任理學院長,也來電催。及我去,而張校長不在南京;晤文學院長梅光迪,乃知國文系須從新改組;而各方面推薦教授、副教授的信,已成堆!梅院長告我從中挑選,提名呈校長聘任。我說:“我不能以意去取!教授,副教授,有相當之資格;聘任有聘任之規則;不能隨便聽人推薦!我們須得東大從前教授,副教授及講師助教聘任條例一看,斟酌起草國文系聘任條件,呈校長提教授會通過;然后拆推薦信,按照條例提名呈校長聘任,乃無流弊。”梅院長就囑我起草;然而謁客紛紛,有認識,有不認識;有一天,梅院長領一先生到我房間,說:“你和錢先生談罷!”又向我說:“這是支偉成先生;蔣總司令介紹給張校長!”支先生拿著蔣中正的信,給我看。我說:“總司令給校長的信,我不敢看!不過我覺得總司令可以委任一軍長,師長,而沒有資格聘用一小學教員;因為不在他職權以內;并且小學教員,需要那(哪)一種人和那(哪)一種知識,做總司令的人,他不會了解!”支先生疑我系一老頑固,手里挾著一包信,中間檢出段祺瑞、孫傳芳的兩封信,因為他寄贈所著清代樸學大師傳,復他的信,恭維他。我說:“大著讀過,極佩宏通;不過因著段祺瑞、孫傳芳的話,價值卻減低了!從前孔子作春秋,沒有聽到送給季孫、陳恒看,得到恭維!”支先生怫然,問:“國文系能不能聘我做教授?”我答:“一定奉屈!不過我現在正和梅先生商訂本系教授副教授講師聘任條例,提出教授會通過;如果先生資歷相符,即無總司令的信,亦不敢不奉屈!”支先生大怒,不辭而出。我起身送他,亦不理;我心中正不好過,而胡剛復來,交我一條子,用紅墨水寫著:“某某某某某某三人可國文系教授。”下署“蔡元培”三大字。我笑說:“這是朱批上諭。”我覺得職權無從行使;我就留一信給梅院長告辭,并托致意張校長,挈著我的手提箱,趕火車跑回無錫了。后來張校長又來一信一電;我覺得不能為地位以遷就一切,不如不去!直到陽歷十月,張校長聘汪東做國文系主任,而我如釋重負。支先生如愿以償,而后來因為學生不上他的課,一氣嘔血,而同事都冷眼看他,遂病不起;我聞之,甚為惋惜;拿學問論,支先生實苦心下過一番功夫;不過躁進欲速,吃了虧;這是我出于衷心的一句公道話。
我興趣在教學,而不喜攬事權,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嘗以事不干己,置身事外;而恫心怵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學的黨獄!當國民黨得意時候,大學的學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黨的金錢津貼;做特務工作,監視同學,按月報告;有的因邀功,有的為挾嫌,常常無事生風,興起黨獄,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據我旁觀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幾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學,被捕二百多人;那時,我在光華大學,一天,是冬至的隔夜,夜間十二時,電燈熄,我已上床,聽得足聲歷落;旋有人叩吾房門;開視,乃吾兒子鐘書,披衣赤足,低聲說:“張杰被捕!”張杰,是附中國文教員;鐘書,是大學英文講師;兩人同住吾隔壁房間,對面床;據稱:“正將入眠,聽得房門鎖響;疑為竊賊,叱問。乃門開;見一人持手槍,一人持手電筒,揭帳問‘你是什么人?一聽是‘錢鐘書;就轉身喝張杰起,背綁而出。”我叫鐘書相陪去看附中主任廖世承,去到樓底頭,有一人持手槍喝禁,不許動。到天明,乃知上海各大學一夜捉人不少;光華則張杰以外,有民眾夜校主任薛熾濤,和男女學生十四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陸姓,在我班上有課,耳微聾,見人羞縮,而也當政治犯捉!有同學來告我:“同學何某,為潘公展所派之暗探,平日手槍不離身!”何某也上我課;我就以私人名義,相招一問;何某不承認。我見他西裝腰廝勢穡就接著問:“何以身上帶著手槍?”他乃似承認,非承認,說:“某某兩同學政治確有問題!”我問:“此外同學怎樣?”他說:“不要誤會我有什么關系!”張壽鏞校長來通知開緊急校務會議。我到,校長室人已坐滿。我報告何某談話情形,說:“事從根上起;校長何不招何生一問所以?”校長招何生來,沒有椅坐。校長起立招呼,喊工友添椅。我說:“現在談話要緊!校長坐著和學生談話,也不算不禮貌!”不料何某態度驟然強硬,說:“同學自己有政治問題,校長也沒有辦法;我更不消說得!”轉身就走!大家面面相覷;校長干笑著!校長也就出去合著各大學校長,一同看上海市長吳鐵城,教育局長潘公展,請求釋放。到下午四時回校,乃知各大學被捕的人,已從上海市公安局移解警備司令部。各大學校長和吳鐵城、潘公展談話沒有結果,就請求一看被捕的人,總算沒有拒絕;因為一切人,都是半夜從熱被窩中拖出,絨衫短襖,衣服不及穿齊;有些還赤著腳,凍得面無人色!校長回來,趕緊送被捕各人的衣被去;從此關了,一直過冬!各大學校長南京上海奔跑著請求,只是不放!陸姓女生的母親,是一寡婦,只此一女,不時到校長室吵著哭。有一天,張校長招我說:“吳稚暉,是同鄉嗎?”我說:“是!不過多年不見面!”張校長說:“這一案件,正式向黨政機關請求,已僵;最好有人從旁講一句話。”我說:“不管有效無效,我可以寫一信給吳稚暉!”晚上,我就寫信,尤其強調女生陸姓的情況,說明此女乃是中等人家一個平凡女兒,斷不會有政治問題;依此而推,其中有政治問題者決不多而無辜系累;最后說:“從來政治領袖,只知道抓緊政權,不懂得牢系人心;政權抓得愈緊,人心離得愈遠!現在大學學生,一見到哪個同學是國民黨員,就暗暗跑開;做一個黨員的人,已經鬧到眾叛親離;國民政府失掉國民的擁護,不言而喻!一切下級黨員做的事,將來須得整個國民黨負責!”明天,送給校長看。張校長說:“好!”就拿去發了。吳稚暉因為前一年漢口行營密電拿我,而他知道得晚,對我有些抱歉,就復我信,說:“轉呈委員長了!”我就給張校長看。張校長聽得蔣中正回奉化掃墓;就跑到奉化去,見了面解釋,總算取得手諭,由各大學取保釋放。這件事方才結案。講到漢口行營何以密電拿我?我至今莫明其妙;這是前一年一二八上海戰爭的那年。上海戰爭發生,我寒假回無錫,當然我參加地方國難會的組織;當然我也有些意見,向政府表示;然而戰爭熄了;我依舊到光華,回到我教書匠的崗位。有一天,一個朋友看我,說:“你當心!你兄弟兩人名字,已在黑名單上,聽說在六七名之間!”我想我安分守己的教書,何至惹禍;我不相信!不料有一天,星期六,有一個省督學金某來看我的同居徐景銓。徐景銓和金某是東大同學;然而早先卻在師范跟我學;停一會,就來看我,告訴我:“金某是奉省教廳周佛海廳長命令,查辦先生;教廳奉到漢口行營據探報來電,說:‘先生是國家主義派,和曾琦很要好;在上海,天天晚上,帶著學生李懷清,到小西門開會。”那時,我實在惘然!我和曾琦,不但沒有見面,而且只字沒有來往!我在光華,和現在在華中一樣,除了回無錫,雇一輛人力車,通過馬路,到車站;平時簡直杜門不出。不錯,我有個學生,叫理懷清,并不姓李;然而國專畢業,早已不知去向!不知這位探子先生,從何處捕風捉影,和我開玩笑!后來我才知道漢口行營,最初電南京衛戌司令部拿辦。有一位參謀遲疑,說:“我在小學,讀過錢某編的教科書,算來相當老年,不應該再有政治活動!”其實電教廳查辦,而無拿辦字樣,事已松動了!然而嚇得我老妻一夜睡不著!我就寫信吳稚暉,問其所以。后來稚暉復我信,聲明“誤會”了事!這也可以見得特務之無事生風,徒然害人,而于政府威信,有損無益。又有一起黨案,和我無干,而我參預解決的,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我在湖南藍田師范學院;那時,我身體病,解除國文系主任職,專任教課;不過院長廖世承,和我在光華十年共事,所以有事,都就我商。一天早起,院長相看,示我薛岳一件密電抄文,內稱:“據報安化藍田鎮奸偽活動,以國立師范學院為大本營。該黨湘省委辦公處亦在該院。該黨刻正向新化錫礦山工人方面發展。查錫礦山有工人數萬,一旦奸偽參入,隱憂實大!查該鎮目下僅以當地警察分所長及三民主義青年團藍田分團部半公開的擔任消極監視工作,顯少成效!合行令仰該縣長及附近軍警,協力偵查,嚴密防范,具報為要!”我看了,就說:“倘不趕早消弭,可能如上海從前各大學來一圍捕。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第一須得給薛岳一電,詰問他據什么人報;并抄稿寄湖南省黨部備案。次則也須呈報重慶教育部,派員會同湖南省政府查以明究竟。吾們不能坐著,等軍警來圍捕。”院長以我的意見為然;就招秘書諸君達起草,送給我看。我說:“不對!討饒無用,須得抗議!我們理直氣壯,告密人一虛百虛!現在銻業不振,錫礦山礦歇工散,是否工人數萬,最是事實不諍;倘就此點勘究,其他不辯自明。誣告反坐,入后尤須扼重!”院長就囑我重起草。我因提一意見,說:“同事周邦式教授,是國民黨黨員,和省黨部也有聯系。我看院長最好一征取他意見!此公心地明白;我草起好了,也得和他商量!”院長就先去看周教授。周教授聽了駭然,說:“我得先去省黨部一信!”我起完草,送周教授看,修改了一些,發出。后來薛岳復電,說:“屢得報告,不敢操切!”教育部也來一電,說:“聽候中央黨部查辦!”這件事也就擱過了!哪知到了十二月初一日,是師范學院五周紀念日;院中正在舉行祝典。周教授忽告院長說:“遠東飯店來一客,似特派員;院長何妨逕去看他,請來院察勘,解釋一切!”哪知院長到遠東飯店,謁此怪客;已有學生兩人先在,見院長,大窘!院長請客赴院。客說:“不必!一切已經明白,惟兩生不得處分,并宣布姓名!”客又好語安慰兩生,好好讀書!這件案乃算真正消了!不過我覺得國民政府,枉派了許多特務,報告的真實性,實在折扣得太多,而徒然誣陷一些不相干的人;人心一天一天的離,政權也一天一天的抓不住;而他卻自以為得計;真是至愚極笨!更有一天,晚上,一個客人推我房門進,說:“先生!認得我嗎?”我想不出。客說:“我是夏賡英。”我才想起是十年前的學生;他胖了,我認不得。他問了我的生活和身體;他才低聲告訴我,說:“有人報本院訓導主任陳定謨,有奸偽嫌疑,奉派來查。”我答:“陳定謨,相識不久;不過我有一句話:‘現在你們國民黨當家,要看得全國的人,個個人同家人骨肉一樣;才有辦法。如果今天疑這個,明天疑那個,看得全國無一人靠得住;弄得人人自危;黨離了國民,黨亦不存!”夏賡英笑說:“先生意氣,還是早年一樣!”后來陳定謨也就一查了事,不過認他講經濟,有些左傾!這些黨獄經過,我還留些文件作紀念。
我財產觀念極薄;錢到手就空。然而“吃”“喝”“嫖”“賭”四字,我不犯一字;連紙煙都不吸。我一生不喜肉吃,到現在,往往買了半斤豬肉,我和老妻兩人,兩天吃不完,就給女傭吃了;至于雞,非過年祭祖不殺,一年難得有一回兩回殺!蔬菜,則我老妻自己種了吃,很少賣。衣服,鞋子,到現在,還是我老妻親手裁,親手縫給我穿;不必勞縫工。我老妻一生,手沒有摸過牌,嘴沒有銜過紙煙;講到娛樂,生在上海附近,從沒有進過影戲院的門;其他不講了!我教書上海,前后幾十年;然而我不知道影戲院的門,如何進;我生平只看過一回戲,就是在清華那年;孟憲承說:“如何到北京,不看梅蘭芳的戲!”雙十節那天,就約我去了;哪兒知道梅蘭芳掛了牌,沒有出演;始終沒有瞻仰到。我有三個兒子,和媳婦,沒有一人懂得賭;三個媳婦和大兒子,也不吸紙煙;所以我家庭用度很省。然而我十九歲就館,月薪就銀幣二十元;到了二十三歲,游幕江西,每月送我銀百兩,合銀幣一百四十元左右;直到民國二年,我二十七歲,月入最多時,一百六十元;少則百元。后來做小學教員,第一年,月薪二十二元;第二年,就加十元。我初進中學,月薪五十元;到民國十二年,已加到每月九十五元。下半年,我到圣約翰大學,月薪一百五十元;到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發生的那年,我在浙江大學,已加到每月三百六十元。在抗戰最后一年,教部按級支薪,我底薪伍百四十元,比之最初每月二十元的收入,是二十七倍;然而我一家生活,不過加十倍;我三個兒子,一出學校,也沒有一人一天閑住過;然而我未買一畝田;銀行儲蓄,從未開過戶;我無錫許多大工廠,大商店,沒有一家有我一股兩股的股金。我不愿積了錢,供一家享用奢侈;我寧可送給人家用!我不愿送人家的禮物;而人家緩急,沒有不量力應付!自我早年已如此;我深知社會罪惡,一切在占有;我不愿占有;做事四十八年,不失我的寒酸;總算幸免于罪。
(三)我不能勞動,而人家勞動的果實,則不敢糟蹋!
我生平頂恨自己不勞動,而糟蹋人家勞動的果實。我則因為自己怕勞動,勞動不得;而知人家勞動之不易;所以勞動的果實,格外愛惜;這是由于我家庭的教養。
我父親最愛惜谷粒。我小時同他吃飯,有一兩粒飯米落在地下,他老人家必叱喝著,叫喊檢(撿)在口中吃下去;常常說:“碗中一粒米;農民一身汗!”我還記得,有一天,他到廚房下,看到泔腳缸里有飯,發氣說:“你們吃了現成飯,哪兒知道鄉下人種田的辛苦!”女傭應著說:“飯餿了,所以倒掉!”他更發氣,說:“你看我吃下!”就取一個淘籮,將飯瀝出,取開水一泡,就吃下了;大家嚇得不敢做聲。后來我到江蘇省立第三師范教書,飯廳上掛著“盤中粒粒皆辛苦”七個字的橫匾;學生也還珍重米粒!及到上海,看見許多大學生,往往一碗飯吃了半碗,倒在地下了;粒米狼戾,勸說一兩句;大家覺得我有些土氣。知識分子,這樣缺乏勞動觀念,不愛惜勞動果實;我看到我們上一代,還不至這樣!乃至日本戰爭發生,我隨著戰爭的蔓延,逃到江西,逃到湖南,到處聽到,看到難胞沒有飯吃,跑不動,就僵仆路上;然而一到學校,一般青年學生,吃了國家公費的飯,依舊不知道物力艱難。有一次,我和學生吃飯,一女生吃饅頭,撕了皮吃,狼藉滿桌。飯畢,余招問所以?她說:“因為臟,不衛生!”我厲聲說:“國難嚴重到這般地步,全國同胞,餓肚皮,吃不到這般臟,這般不衛生的饅頭皮者,不知多少!你不要看見外國人吃面包,不吃皮,定要學樣!”我想現在知識分子,經過下鄉土改,看到今天工農當家之老農家,辛苦種了田,沒有好飯吃,這種觀念,當得正確些!
我愛惜一塊古玉,一只古鼎,像愛惜一粒谷一樣,因為同一是勞動的果實;不過一是古代的,一是現代的。然而一粒谷,可以吃飽我們的肚皮;一年古器,可以充實我們的文化。我們看了一件古器,可以想見我們祖宗藝術的優美,民族文化開發的老早。我常常認為這是民族歷史的物證,社會文化的遺產!“社會是勞動的產物”,這個口號喚出了;然而社會勞動的果實——產物,并沒有得到我們真正的發心愛護!人民政府雖然三令五申,不論物質的,文化的,到處看到浪費,甚至糟蹋和毀壞;這是我們當得知道警惕的。
辛亥以來,四十年過程中,社會財產——勞動的果實,無條件整批毀滅,我看到實在可怕。其實共產,先決條件,須得有產可共。我自己沒有一些財產;然而我常常想法保護一些社會財產,盡可能免得無目的、無意識的破壞。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武漢將近解放,第一紗廠經理程子菊,卷了資本,向香港一跑,工友索薪無著,引起各廠恐慌。我因為兒子鐘緯在漢口申新四廠,當副廠長;那時,有朋友寄給我一本“轉變中之北平”小冊子;我就帶了過江去看兒子,知道經理副經理以及高級職員,大多嚇跑了;廠長病倒在上海醫院!我到,恰恰有一技師,從前是我兒子的學生,苦苦請求準假回江南。我說:“資本家有錢望(往)香港跑;你們拋掉機器,就沒有生活!”我就檢(揀)小冊子中于工廠部分,指點給兒子看,說:“從前你是副廠長,現在須得站起來當家!召集工廠大會,聲明你自己的立場和不跑。調度廠中所有的物質,保證工友的生活,決不像第一紗廠不發工資。安了工友的心,然后如實提示三點:一、保護民族工業,并鼓勵工人竭力保護,乃共產黨新經濟政策綱要之一。本廠是民族工業,工友們當得全力保護。二、工友們,茍不斷生產;無論時局怎樣,必代表廠方以保障工友的生活。三、工友保護本廠機器不毀壞,生產不間斷,即保障自己的生活前途。廠主的身家性命,或者別有依存;而工友們身家性命,則必系于廠的保全。”兒子總算依我的話。我并替兒子擬一白話韻文布告,說:“本廠民族工業,不同資本官僚!民族工業能保,經濟乃有新路。工業就是生命,大家認識清楚。如有煽動毀壞,罪同坑殺工友。大家努力生產,切勿自毀前途!鄙人追隨工友,誓守崗位勿走!務望工友齊心,崗位共此牢守。”我勸兒子和其他私營工廠取聯系,交換辦法,安工友的心!我又寫信給我在上海一個弟弟,向上海各工廠,提供一些意見;其實我的弟弟早已有默契,講不到怎樣效果;然而暗中減少一些無為的糾紛。等到武漢解放,我想起我到武昌,李范一先生曾來看我一次;我就寫信給兒子,叫他去看李范一先生,報告一些武漢民營工廠的情形,供參考。
(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會;尤其不愿接受社會之腐化以腐蝕我民族本能。
我讀古人的書;我們的祖宗,總是教我們勤生節用;而現在貪污浪費,這是我們子孫的不肖,不要把責任卸給祖宗!辛亥革命,蔡孑民,吳稚暉,發起進德會,認為革命必得革心;人有不為,而后可以有為,相約以不為自律;最高的八不:是不納妾;不狎邪;不賭博;不飲酒;不吸鴉片;不吸紙煙;不做官;不做議員。會員各自認定幾不;最少三不為末級。那時我在南京,有人送了一個會章來,是白銀鑄的一個心臟,當胸懸著;說:“心,要叫我摸摸良心;銀,象征良心的純潔。”征求我入會;如果認了幾不而不遵守的;同會的人,見到他,就鞠躬,促他自覺!我那時,看到黨人,軍人,狂嫖,濫賭,生活腐化得可怕;我想著我年紀正輕;如果混著,一同下水,以后不得了!我想官和議員,也看他怎樣做!我眼前至要至緊的,是約束我的生活,不跟著人一同墮落;就認定“不納妾”;“不狎邪”;“不賭博”;“不飲酒”;“不吸紙煙”五項;出了一元銀幣,領一個進德會徽章,背鐫“五不”二字,貼心掛起。有朋友來引我逢場作戲;我就翻進德會章,指給他看,說:“我不愿同會的人,見了我鞠躬!”最初人家不高興;然而一次,兩次,連三次拒絕了;人家也不再來惹我。總算到現在六十六歲,“五不”,沒有一項犯過;不過有時參加宴會,人家敬我酒,不能不舉杯示意而已。
我生平不大歡喜受人家的請,參與宴會;我覺得宴會是一種浪費,杯盤狼藉,吃不了,剩許多!我寧可出十塊,二十塊錢,應窮親戚的急;我不愿拿十塊錢,上館子,請一個朋友吃飯;我從前就是如此。到了抗日戰爭,我逃難,沒有餓過肚皮;然而看見人家餓肚皮,更何心吃好飯。發心不受人家的請吃飯,也不請人家;然而人家往往不原諒。我在藍田,有一個冬天,同事約我吃夜飯,我苦辭。到了晚上,主人引了一個轎子來,說:“院長已到了!”我不得已,只有去,看到這朋友一個十多歲的兒子,新近跟著母親從淪陷地方出來,身穿破棉襖索索抖。我說:“某人!你有錢請大家吃飯;何如替孩子身上,添一件新棉襖。”這朋友很窘;其實這朋友何曾愿。社會的奢侈浪費,逼得窮朋友不得不做“不愿做”的事。后來日本人跑了,我回到無錫,湯恩伯總司令部駐在那兒;有一天,得到他的請帖,請地方士紳;我就在知單上,我的名下寫了幾句,說:“抗戰一起,誓不參加任何宴會。現在敵人雖退,民不聊生;誓言猶在,心領,請諒。”隔了幾天,得到地方士紳知單,公請湯恩伯,每人派出份子三萬。我拿三萬交來人,就在知單上注:“總司令饑溺斯民,敬獻三萬元以助振恤!”從此以后,我在家鄉過夏,無人再來麻煩了!
結束
我不愿泛泛認錯,我要抉發我思想的根源,供大家改造。現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至要至緊,改造“個人主義”的我,成為“社會主義”的我。我們祖宗,原來教我們“天下為公”,并沒有教我們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個人主義”,是跟著西洋資本主義,一同侵襲到中國,我本不贊成,我并沒有放縱我的私生活;不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為,雖然盡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觀念,并未根除凈盡;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沖動,沒有理由藉口誣蔑民族文化。我覺得我中國,好比一條四千年的神蛇,現在正在蛻殼,當然周身不適;他身上組成細胞,哪是老廢細胞,跟著殼蛻去以至死亡;哪是新生細胞,擴展神蛇的生命,將來發揚威力;這須看我們各個人的努力!茍其一個人,為社會,為歷史,向后瞻望,而不僅僅為自己打算;決有前途;所以我不顧慮自己改造的前途;而時時考慮我這個人,對社會有沒有用;如果沒有用,我決不以老廢細胞,妨礙神蛇的發展,做絆腳石。我愿為社會服務,我不愿社會姑息我。倘社會認我不合時代需要,應得予以清除!茍我自信所學,社會必有需要之一日;我歸而杜門,也當悉心研究,搜集材料;一旦社會需要,我就出而貢獻!倘我自念老至耄及,就當傳諸其人!
足后語
以上是交代我的歷史;不過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我讀了校刊人民華大,和思想改造,及直接問聽接聽了同仁、同學的啟示,方才覺察到舊華大,在美帝控制之下,除掉生活腐化了我們——貪污,浪費和貪小利;宗教麻醉了我們——不認識祖國;此外并沒有給我們一些知識,學問。不覺深深懊悔我教書,教了四十年,到華大來結束我教書生涯!
我早年討厭學校生活的洋化,中途脫離了上海圣約翰,脫離了北京的清華;而且脫離清華的時候,我的老友俞丹石曾誠懇的介紹我進燕京;那時,我覺得燕京也是教會大學;如果燕京可以進,當初何必脫離圣約翰;堅決的不就。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那末,我為什么老不長進,來就華大的聘?
我早年失血,以致心臟硬化,肋間神經常常作痛,往往徹夜不得貼席眠;及到日本抗戰發生,家破流亡,眼看到各地的淪陷,人民的慘痛,恐怕焦慮,加增了我的心悸,舌麻,頭痛。在湖南一住八年,到了最后,行動須人照呼,全仗同學們對我愛護,石聲淮就是其中的一人;好容易盼到日本投降,江南收復,急急回到家鄉,想要休養一下。然而我回到家鄉,怎樣呢?家鄉的人,卻希望我在千瘡百孔的戰后,出去替地方服務。然而地方的情形怎樣呢?那時,地方上稍有聲譽的人,都被偽政府指名做臨時參議員;我也不在例外!看似尊重民意;然而我覺得不能代表民意,就將聘函退回,去一信說:“我不是人民選出,民意不能由我代表!如因為我了解一些地方情形,要我貢獻意見。我一眼看到社會普遍的荒淫佚樂,沒有因為受了戰爭的痛苦,知道儆惕;而又一眼看到社會更普遍的民不聊生,絕沒有得到戰勝的利益。現在一切法令措施,不能解決社會一切;我不能附和著欺騙民眾!”議長蔣某帶了聘函,來看我說:“你不能唱高調,搖動人心,使臨參會擱淺!”我說:“你看現在政府,能不能挽回風氣,轉移人心!”蔣說:“你不要太書生氣!”我堅持著說:“臨參會,不能代表民意,至少代表戰后人民疾苦!”蔣留下聘函,說:“你身體不好,我替你請病假。”從此我得了默契不出席。不過地方上一般人,因為我平日做人尚規矩,又素不問地方事,無黨派,而從前我在中學師范教的學生,都在地方各方面做事,望著我出去主持一些計畫,緩和一些地方相互間矛盾。然而我擔心者,不在地方事業,而在地方風氣!間或到街上散步,看到酒館茶肆以及冷飲店,茶食店,望衡對宇;無一家酒館不座滿,無一家茶食店不柜臺上擠滿買客;而回過頭來,看看我的親戚朋友,有一些人,請一次客花幾十萬,做一件衣花幾十萬;然而一些人,卻因了戰爭破產失業,每天吃飯,須得設法,通融到十萬八萬,便向人感激不盡;尤其訪問當地公私立中學,看到一般相熟的教育朋友,在教員休息室中,不談功課教學,而談怎樣做生意,買空賣空,乃至高利貸;這種情形,卻是戰前沒有的。我看到那時,個個人惟利是圖,只顧自己;忍心害理,教育同人心一齊破產,至于不可收拾。有一次,江蘇省立無錫師范,招我演講,我提出一個講題,是“怎樣樹立師范,來安定民生?”有一次,在縣立女中,演講“教育的新女禍”。又有一次,在商會演講“戰后的生活當得怎樣?”演詞在地方報紙披露;大家見面,都說我按時立論,作一當頭棒喝;然而事實怎樣呢?一方面贊成我的議論,而一方面約我吃飯的請帖,如雪片的來;不到,則主人上門來邀;非說得我舌敝唇焦,不放松我。弄得我周身神經性痛大發,睡上床了。我尤恨的,恨我的力量小,不能轉移社會風氣;而社會風氣,卻來轉移我了。我那時常常睡在床上,考慮我余生怎樣自處?我和鄰近各縣朋友通信,又發覺一件事:戰前所稱各地方的好人,都站起來了。一方面反動政府,想利用他們聯系各地方的人心;而一方面也因從前各地方的當權派,自知失掉地方上的信用,而想擁戴一個地方上大家心里認為好人的人出來,做他們的擋箭牌;往往他們做壞了事,而他們擁戴的好人,出來替他們解釋;不知不覺成了同流合污!我沒有力量糾正地方的風氣!我只有同流合污!我做不到;我就想避地,避地來到我沒有什么深厚關系的地方——華大,來作客,做我的教書匠;希望我緊張的神經,衰病的身體,休息一下;不料一腳跳出了糞坑,而一腳踏入了魔窟。
連日聽了各種各式的控訴,我憤恨!我不憤恨別人,我只憤恨我在此六年,我上我的課,沒有覺察一些帝國主義的陰謀,沒有向韋校長提出一些建白;已經喪失了我素來中國人的立場!雖然因為我厭惡洋人的生活,也因為我不懂英語,沒有參與帝國主義分子的社交,也就沒有參與他們的陰謀,減輕了我的罪惡;然而這是我的麻木,我不能以此自恕。我受了美帝的豢養六年,我就不能洗清我的一身的臟!我雖沒有同流;我卻已經合污!我寫到這兒,我追想到我來到華大的第二年,有一天,到校上課,中途在轉角一家矮墻里,看到一個老頭子傴僂提了一桶水澆菜,一老婆婆隨同著;我眼看他倆生活清苦,然而園地整理得很清潔。我就立下,問他倆高壽多少?方才知道這位老先生姓李,已七十九歲,老太太小一歲,沒有兒女,也不請雇工,老夫婦兩人,勞動自給。停了一天,我就去訪問;乃知這位李老先生,是五十年前一個老留美學生;他的老太太,從前也在湖南女子中學教過書;這一幢住屋和園地,便是他倆唯一的財產,房屋門窗多破壞;家具也不全;然而打掃得很干凈,門外階沿上,擺滿了自己栽的盆花;老夫婦生活很苦,然而他倆過得很甜蜜愉快。這位老先生問我怎樣來,卻對我說:“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從前文華屢次招我教一些課,我卻不愿!”我聽了面紅,我也不好意思接下去問他所以。我回到寓里,對石聲淮說:“這位老先生一塵不染,真正叫我愧對著他。”從此我每到校上課,經過他的門口,心里常常覺到不好過。然而我還沒有知道帝國主義分子,在華大種種陰謀!現在聽了連日的控訴,益使我回味李老先生的話。假使李老先生夫婦過著優裕的生活,也還可說;然而我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這位老先生為了繳不出地價稅在那兒發愁。看到他抖顫著手拿一枝禿筆,寫申請書,請求延期繳。有一次,我去訪問他,要想對他表示一些敬意;然而一聽到他的話斬釘截鐵,我不敢開口!從此我敬他而不敢親近他!到了今天,覺得我來華大,已經喪失我中國人的立場;我只有對著這位中國老人,十二分抱疚!我的話就此住罷!
此外尚有一件事:自問親美崇美思想,尚非十分嚴重;然而對于蘇聯友好情緒,亦不濃厚;中蘇協會證書,未簽署加入。
至于哈京學會研究論文,和接受學校軍毯及黃金一兩的贈與之愿退出;以及陶美和薛洋人的請看古畫;已經以書面提供討論小組,不多贅及。
本人方音,諸位先生和同學不大懂;前經小組長李中行先生停止發言,囑以書面提供;現在仍前尊重小組長的意思,提出書面檢討,請求免予口頭宣讀,免得耗費寶貴的時間,妨礙諸位的發言。
資料寫作者:錢基博,錢鐘書先生的父親,華中大學國文系教授。此檢討書為錢基博1952年6—8月在華中大學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所寫。
資料提供者:周洪宇,教授,現居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