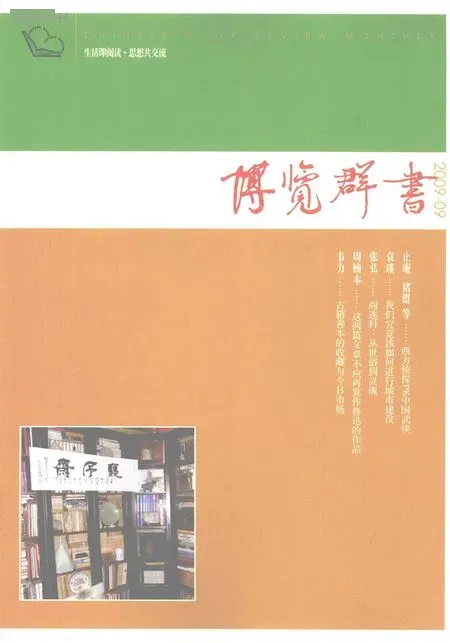全球問題: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
閔家胤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羅馬俱樂部發(fā)表了一系列報告,提出了“全球問題”,其基本含義是:隨著世界各國仿效西方發(fā)達國家紛紛走上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的道路,在各國經濟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在全球范圍出現(xiàn)三個負面效應——人口爆炸、資源短缺和環(huán)境污染,如果不加控制和改變的話,人口上升的曲線同生命支持系統(tǒng)能力下降的曲線遲早會相交,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將達到突變分叉點,將會爆發(fā)全球性的生態(tài)災難,危及人類的生存。
據(jù)我所知,E·拉茲洛是在1972年發(fā)表《系統(tǒng)哲學引論》之后引起羅馬俱樂部的注意的。這個催生了“全球問題研究”這門學問的組織邀請他“用系統(tǒng)哲學研究全球問題”,于是他組織起分布各國的120位學者,在1977年完成了一部很厚的羅馬俱樂部報告《人類的目標》。在撰寫這部報告的過程中,他突然醒悟:羅馬俱樂部第一份報告討論的“增長的極限”是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外在限度,是一些不可改變的自然常數(shù);現(xiàn)在人類社會人口、生產消費、污染等等的增長要觸及這些“極限”并引起危及人類自身生存的災變,過錯不在地球的自然環(huán)境,而在人類自己。具體說,全球問題的根源在作為工業(yè)文明的基礎的近代西方文化。于是,他在1978年獨自撰寫了《人類的內在限度——對當今價值、文化和政治的異端的反思》,從羅馬俱樂部最初注重的對地球生態(tài)環(huán)境外在限度的考察轉向對西方文化的世界觀、價值和倫理的內在限度的批判性考察。1986年他出任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顧問,組織廣義進化研究小組,主編World Futures(《世界未來》),致力于從進化規(guī)律中尋找解決全球問題的途徑。1993年撰羅馬俱樂部報告《決定命運的選擇》(中文版,三聯(lián)書店,1997年)。1993年組織布達佩斯俱樂部,發(fā)表第一份報告《第三個1000年:挑戰(zhàn)和前景》和《意識革命》(中文版,社科文獻,2001年),論證人類只有通過“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的災變。2001年發(fā)表《巨變》(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02年)。此書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將近代工業(yè)文明的進化分成四個時期,現(xiàn)在已經進入“關鍵期”或“混沌期”,在未來十年(2001~2010年)內,如果人類能夠完成一場“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人類社會就會“大躍遷”,進化出一種更高級的文明,否則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危機和瓦解。
人類當前面臨的危機實質上是西方文化的危機,西方人意識的危機。它不是依靠在表面搞一些修修補補就能解決的,而是要依靠人類從內心覺醒,在意識的深層次上產生革命性的變化才能解決。近現(xiàn)代西方主流意識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人生觀,這場“意識革命”的主要內容就是對這三者的超越和揚棄。
世界觀的轉變首先是科學范式的轉換,從機械論轉向有機論,從線性思維方式轉向非線性思維方式,然后建立一種整體論的世界觀。它把地球重新看作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或大地母親蓋雅(Gaia),她是一個單一的活機體,生命和非生命系統(tǒng)構成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一個有反饋能力的控制系統(tǒng),有自調節(jié)和自修復能力,為地球上的生命尋找最佳物理和化學環(huán)境。由此我們每個人產生出對地球母親和生命系統(tǒng)負責的意識,反思和糾正自己行為的意識。
西方輸出的最危險的東西就是工業(yè)文明的價值觀。無止境的物質追求,拼命生產,鼓勵人們購買產品,不斷擴大消費。我們集體精神錯亂和全球危機的根源正是這種意識模式。把西方目前的價值系統(tǒng)和生活方式輸入到發(fā)展中國家,是全球性自殺。因為這種物質主義或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僅在索取、占有和消費,滿足不了就失意、頹廢、酗酒、吸毒,甚至自殺。《巨變》一書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介紹了在美國和歐洲新出現(xiàn)和正在壯大的“文化創(chuàng)意派”(culture creatives)的價值觀的內容和生活方式,它是西方文化中比“傳統(tǒng)派”和“現(xiàn)代派”先進的文化派別。
價值觀的進化取決于對個人的超越,特別是對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的超越。人類必須在意識上超越以我為中心和以我們?yōu)橹行模_到“人類意識”、“全球意識”和“宇宙意識”,“個人的靈魂最終似乎與萬有同在”。這樣的個人將會充滿愛和同情,不僅熱愛和關心自己,而且熱愛和關心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生命賴以維持的環(huán)境。
拉茲洛相信,在少數(shù)人心靈當中產生的“意識革命”可以傳播開來,影響達到多數(shù)人產生“意識革命”,從而完成“文化轉型”。他把由這種未來文化創(chuàng)造出來的新文明稱做“新理性整體文明”。我們可以嘗試把它稱為超越了“工業(yè)文明”和“后工業(yè)文明”的“生態(tài)文明”。
為促成這種變化的出現(xiàn),《巨變》一書對個人提出了新誡命:想到全球,負責任地生活。再不能“我愛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者“像富有的人那樣生活”,而是要“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這是一條古老的格言,出自印度教的《奧義書》。這條新誡命顯然要求富人,特別是西方的富人,再不能不加節(jié)制地窮奢極欲,暴殄天物,而是要帶頭回歸比較節(jié)儉的生活;同時,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民也不要盲目地追求西方生活方式。
對企業(yè)提出了新誡命:創(chuàng)造一種負責任的企業(yè)文化。要承認“企業(yè)是作為包括社會系統(tǒng)、政治系統(tǒng)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復雜適應性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在運作”。要認識到企業(yè)的運作如果損害社會和環(huán)境,最終會倒過來損害企業(yè)。因此,企業(yè)再也不能只關心企業(yè)主、股東和從業(yè)人員的利益,要有“深刻的社會和生態(tài)責任意識”,并“對社會和環(huán)境問題承擔責任”。這就需要創(chuàng)造新型的企業(yè)文化,特別是企業(yè)倫理。
對政府提出的新誡命是:擴展政府的視野。各國政府要把眼光從民族國家擴展到區(qū)域聯(lián)合體、網絡社會、全球社會和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對于涉及人民的教育、就業(yè)、社會保障、社會的和經濟的公平,及當?shù)刭Y源利用方面的問題,國家政府的權力下放是迫切而重要的。對于應付我們時代的兩個迫切問題:和平與安全,及生態(tài)可持續(xù)性,權力上交又是急需的”。要建立區(qū)域安全體系,節(jié)省軍費開支用于治理環(huán)境,并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維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集體行動。
對社會提出的新誡命是:采取一種對自然的新態(tài)度。要從對現(xiàn)代科技造成的后果的反思中產生全球價值和全球倫理,這是一種生態(tài)價值和生態(tài)倫理。其中心信條是:“保持人類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資源與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環(huán)圈和生命支持系統(tǒng)之間的動態(tài)平衡”。《巨變》一書引用1997年11月28日來自七十個國家的1670個科學家,包括102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簽署的共同聲明說:“需要一種新倫理,這種倫理必須驅動一個偉大運動,說服不情愿的領袖們和不情愿的政府們,以及不情愿的人民,自己來實現(xiàn)必須的改變”。這種對自然的新態(tài)度轉換成博弈論的語言就是雙贏博弈——我贏你贏,而不是我贏你輸,亦即從人類與大自然被動的共存轉換成主動的互存。
其實上面這層意思,我國哲學家馮友蘭早就講了,而且講得比他們清楚。他的“貞元六書”中的《新原人》講人生哲學,“它認為人對宇宙人生的不同程度的覺解構成不同的人生境界。大致說來,有四種境界:一是自然境界,即一切順從本性和習慣,對宇宙人生毫無覺解;二是功利境界,即為私、為個人的利益而生活;三是道德境界,即為公、為社會的利益而生活;四是天地境界,即覺解宇宙、‘真際,徹底了解人生的意義,為宇宙的利益而生活,以至與宇宙合一,達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境界。其中前兩種是自然的賜予,后兩種是精神的創(chuàng)造,而哲學的功用就在于提高人類的覺解,使之達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264頁)
至此我們就完全明白了,人類需要完成一場“意識革命”以挽救自己;但它不是“自然的賜予”,而是“精神的創(chuàng)造”。拉茲洛組織布達佩斯俱樂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全球政治、宗教、哲學、科技、教育、藝術各界精神領袖都要動員起來,發(fā)揮各自的作用,進行精神創(chuàng)造,進行宣傳,幫助人類完成這樣一場“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