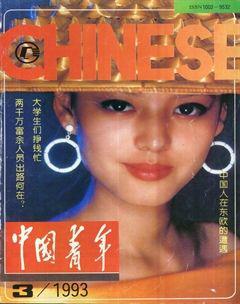在錢欲與道德中間
劉朱嬰
“下海”就該往“黑”了賺?
他曾是樂團的首席小提琴,當年,一曲“梁祝”拉得人們熱淚垂腮。如今,那雙靈巧的手把起了方向盤。
那天,我站路沿兒上攔車去機場,一輛沒“TAXI”標志的“面的”悄然停下,車窗里探出一人頭來:“要車嗎,去哪兒?”我立馬反應過來:這是一“黑車”!看我滿腹狐疑,他也有些干,說:“咱這不是干第二職業嗎?錢好商量,上車再說。”
機場路上,車跑得倍兒歡。他開了個價:“50,怎么樣:要嫌多,您往下砍。”我一楞,說:“忒便宜了,國營的還七八十的要,您還不往‘黑了宰呀?”他說:“嗨,不敢!要不,怎說咱傻呢?”
他告訴我:“這車,是和親戚攢了3萬多元買下的,沒指著發大財,先把本墊補上再說。照說,‘下海不就為了撈錢嗎?可咱有那心,沒那膽。有一天,咱從北京站拉三位外地來的客人奔阜外大街。到地兒了,我把車停下,他們問我:‘多少錢?我實打實地說:‘20!他們遞給我60。我懵了:這明明說的是20,怎么多給我兩倍的錢?您不知當時我這心里頭有多鬧騰,收下吧,覺得特虧心,這種事咱從沒干過;退給他們吧,又覺著可惜,人家既然給了,就裝一回糊涂拿著吧!就在咱犯懵這會兒,客人下車走了。我越琢磨,心里頭越不舒服。回家后對老婆一說,她說:‘敢情那仨人聽岔了,以為每人20塊錢,可不就給你60嗎?你也真敢收!”
“那天晚上,我一宿沒睡著覺,就跟無意偷了人東西似的,覺得特對不住誰。我把自個兒掰成兩半兒,讓他們‘掐架,看誰說得在理兒。前一半兒說:這年頭,誰有本事誰賺錢,大家不都是互相坑,互相蒙,互相騙嗎?既然‘下海了,就得往‘黑了賺!要不,你攢錢買車干嘛?后一半兒說:錢是該賺,但不能昧了良心。將心比心,如果你被人‘黑一回,心里啥滋味?你雖說改轍‘下海了,但還是個明白人,不能干那不明不白的事兒!前一半兒又說:別他媽的裝孫子!說白了,不就是為了錢嗎?甭又想當婊子,又想立貞節牌坊,自個兒跟自個兒過不去!要掙這錢,就別要這臉;你若要臉,就賣車走人,回樂團拉你的‘梁祝去……”
他說:“這活不好練啦!就像有人說的,每個人都有一條屬于自個兒走的道兒。在這條道兒上,你也許是個‘人精,走得特明白,特瀟灑,特讓人賓服,整好了,能名揚全國,留芳百世。可如果岔了道,你很可能就變成一個傻冒兒,整不好就‘栽了,‘折了。以前,咱多熱愛自個兒的藝術、自個兒的事業啊!可現在,整個兒倒過來了。有錢的,甭管是呆子還是傻子,倍兒受待見,咱琴拉得再好,照樣一副窮酸相。特讓人不忿兒不是?咱沒法兒不更弦!有一回,咱一咬牙,閉眼宰了人一回。那也是拉客去機場,瞅那兩人像‘大款,咱開口就要一百,還沒敢多要。結果,那兩人比咱還惡,一下車,把咱給告了,領了個警察過來,查出咱是‘黑車,不但罰了款,扣了車,還讓咱付扣車期的‘保管費。真是一著不慎,份兒跌大發了。事情鬧到樂團,領導說:‘看你小子挺老實,沒承想偷摸著在外頭干這勾當,損不損?我求領導說:‘先別罵了,趕緊想法兒幫咱把那車兒撈回來吧!要不,咱該傾家蕩產了……得虧咱平時和領導關系處得不錯,領導找路子托人把這車撈回來了,要不,今兒個您就坐不上咱這車了。”
我問他:“你‘栽了一回,還干?”他說:“有啥招兒?不干怎么辦?不同的是,上班時間,咱還得正經八百去團里練琴,而且,再不蒙人了……”
這也忒損了
現如今,一些個曾幾何時自以為在官場混得不錯的“皇糧干部”,也覺著沒法兒照先前那種活法兒往下混了:與其成天炮制那些沒用的講稿、材料、文章,不如玩點兒實在的。眼看一些特不起眼的小人物“發”了就恨恨的想我他媽的智商比你高你能賺我更沒的說!于是,火火的,成天就跟辦公室這電話干上了,三句話不離錢字。
有天,他的一個哥們兒敲來一個電話,說正在與一個港商談一筆投資生意,眼瞅著那港爺就要在投資協議書上簽字了,海外飛來個電報:港商母親病危。那港爺歸心似箭,可一時無法購得機票。哥們兒在電話里讓他想個招兒,好處費沒的說。
他立馬給機場的一個姐們兒掛通電話,也告訴對方好處費大大的。對方說:“你讓那港客今兒晚上放心睡覺,明兒一準讓他坐上頭班飛機!”
翌日清晨,一輛高級轎車把他和港商接到機場。事情辦得倍兒順,港爺走人了,他和姐們兒每人得到一個信袋,打開一瞧,是美金。
錢到手了,這通高興。但他沒忘了問問姐們兒港商機票怎么“掏”出來的。姐們兒指著一個一看就特倒楣的老人說:“呶,把他給換下來了!”
那個老人看上去足有70歲了,孤獨無依地呆坐在一堆行李中間。老人被告知:這班飛機已經滿員了,必須等下個航班,如果下個航班還有空座的話。
“如果下個航班沒他的座怎么辦?”他問。
姐們兒告訴他:“那只好請他老人家重新辦票了。”“我×,這也忒損了!”他氣憤加內疚差點兒背過氣去。這是人干的事嗎?為了一點兒好處費,愣讓一個古稀老人遭此厄運。心里這個不忍,這通自責,這份膩歪,一連幾天,他都無法從這個負罪的怪圈中掙脫出來。
后來,那個哥們兒告訴他:港商處理完母親的事,又回來了,但拒絕在投資協議書上簽字,理由是:大陸的法制不健全:他沒有訂飛機票就能夠上飛機,是因為合作者有求于他,關系好。而一旦將來與合作者有矛盾了,關系不好了,不就寸步難行嗎!
他心想:報應!
以后,但凡有人托他辦這事兒,不管許諾給多少好處費,他都一概回絕。他忘不了那個古稀老人。他對自己說:“另踅摸條來錢的道兒吧!”
這和投機倒把有啥兩樣
列車在夜色中穿行,他沒絲毫睡意。32歲的他,肩上已經有兩杠兩星—中校。同齡人中,也算得上佼佼者了。在軍校的教官中間,他的業務和能力都排在前幾名,頗得領導器重和學員的敬佩。這些,若是擱在從前,他知足了。可現如今,他覺得這些都沒啥勁,他缺點什么!缺什么?錢!
老家石油公司來人,托他買70號汽油,5000噸。北京的行情是2400元1噸,還買不著。他通過朋友了解到,大連有俄羅斯運過來的油,連運費才賣1900元1噸。如果做這筆生意,1900元買進,2200元賣出,不但比北京便宜,他們還能從中敲一筆,多少?1噸就能敲300元,5000噸就是150萬元。天吶!
緊鑼密鼓地與大連一通聯系,妥了,5000噸油沒跑。老家來的人喜得屁顛兒屁顛兒,為他全家擺了一桌上千元的飯局,并許諾事成之后額外給他一筆好處費。他一尋思,已經有100多萬了,好處費這點零頭就甭要了。于是,在老家人面前,他大度了一回。
而當他真格兒背著學校領導上了去大連的火車,心里就打鼓了:他是共產黨員,學員隊長。平常,他對學員講的盡是革命大道理。這會兒,偷偷摸摸干起了販油勾當,這絕對不該是他這種人干的!這和投機倒把有啥兩樣?
大連到了,他想,就算豁出來試一回吧!他跑海港,跑車皮,疏通各個關節,從老婆那兒預支的3000元轉眼花沒了。好不容易把俄羅斯的油輪盼來了,又聽說省里有人插進一杠子,要把這船油包圓兒。他急眼了,跟“官倒”較勁兒,這不是小胳膊擰大腿嗎?朋友出主意:兩家半劈,酒桌上談判!他急忙往家敲長途電話,讓老婆速匯2000元。不料電話那頭哭開了,說學校領導發現他“失蹤”了,已經來查問幾回了!他毛了,本來就是件見不得人的事情,這“貓兒膩”一旦讓領導知道了,這輩子不就交待啦?怎么辦?要錢,就豁出去把軍裝脫了,徹底“下海”;要不,就撥馬回府,老老實實掙工資過日子。他最終選擇了后者。他說,這趟油倒騰的,沒掙著一分錢,自個兒倒貼進去3000多塊,就算打水漂,可連聲響都沒聽見,虧大發啦!
找回道德平衡
有人說:他們仨之所以“困惑”、在行為選擇上羞羞答答、猶豫不決,是因為他們忒善,換句話說就是忒“傻”!他們的價值觀念中,原有的道德準則尚未完全崩潰,還考慮行為的合理性,不甘心直接受金錢的指使,不像有些人活得那叫“透徹”:不擇手段撕破臉皮發橫財,自己“成功”但給他人和社會造成損害。
以前,人們被捆在自己的職業上,大環境沒有提供機會和可能使之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如今,從純個體的行為選擇來說,國家提供給每個人的機會太多了。界限放寬了,尺度放松了,渠道多樣化,甚至有的監察部門還規定了拿回扣的允許范圍。“下海”撈錢幾乎無遮無擋,成為無數人羨慕和期望的經濟成功之路。那些如魚得水“發”了的人,不管是用何種手段“發”的,一時成為輿論宣傳的熱門人物。于是“困惑”出現了:道德準則,是非界限還管用不?
整個社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金錢的赤裸裸的誘惑和沖擊,金錢成為調節人們行為的原則,成為人們成功的目標之一,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不在于該不該“下海”,而在于如何使目的和手段都合理;原有的道德標準崩潰了,是否盡快讓新的準則來取代;金錢應該被法制和道德所制衡。
許多人認為:一個社會在向人們灌輸某種合理的目標的同時,還應該給人們以一種合理的手段。即:你要選擇一條路,就要依循一定的規范去走。
我們的行為在接受金錢調節的同時,道德觀念怎樣保持平衡?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指導機制是否需要盡快健全和完善呢?如果都奔著損人利己這條道兒找錢,最終大家伙兒都難逃被“損”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