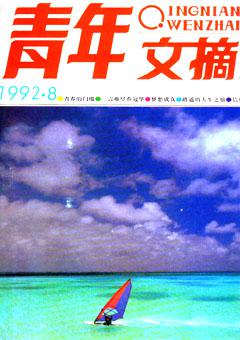夢想成真
陳婭瑋 周 青
那是1944年的圣誕前夜。當時,我正在美國海軍服役,并允準在舊金山休假一天。打牌時我贏了300美元。若在平常,這些錢早就擱不住了。可此刻,我卻感到極度的悲哀。
人們謠傳新年前我們將遠航南太平洋。我剛得到消息說一位朋友在歐洲戰死了。而我——一個18歲的青年,孑然一人卻流落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里。一切都讓我感到茫然。我將為什么而戰呢?
大半天里我都感到神思恍惚,一直漫無目的地混在歡笑快樂的人群中。下午晚些時候,我的視線突然被一個情景吸引住了。
就在一家百貨商店的櫥窗里,兩列電動火車正轟隆隆地穿過白雪皚皚的小鎮。一個9歲上下、瘦骨伶仃的小男孩站在櫥窗前,鼻子貼在玻璃上,雙眼緊盯著那兩列火車。
突然間,那個男孩仿佛變成了9年前的我,那家商店也變成了家鄉紐約城的梅西百貨商店。我能看得出、也能感覺到那種同樣的企盼和同樣無法實現的渴望。我仿佛聽到了父親無力購買這種電動火車時所發出的嘆息,我似乎也看到了他極不情愿地轉過身,然后又回過頭去,投去最后一瞥的情景。
這可是圣誕前夜啊!不知是什么力量控制住了我,我的雙臂按住了那個男孩,把他嚇得半死。
“我叫喬治。你叫什么?”我告訴他。
“我叫小杰佛里·霍力斯。”他掙扎著告訴我。
“是這樣的,小杰夫·霍力斯,”我竭力用成人的語氣說,“我們打算買下這列電動火車。”
他的眼睛突然睜大了,變得格外明亮,眼神里透露出難以言狀的興奮神情,然后順從地跟著我走過了那家商店。我知道我是瘋了,可我不在乎。突然間,我產生了一種無法控制的激情;我想再次變成一個9歲的孩子,并讓兒提時代的夢想變為現實。售貨員滿腹狐疑地看著我們——一個是衣衫襤褸的黑人小男孩,另一個是穿著不合身的藍色海軍服的黑人水手。
“我們想買櫥窗里的那列電動火車。”沒等他開口,我便脫口而出,“整套裝置都要了,多少錢?”
他哼了一聲,剛要回答,卻被一個剛走過來的人打斷了。“165美元63美分,”這個年齡稍長、滿臉慈祥微笑的人回答道,“包括送貨費。”
“我要了,”我說,“可能的話,現在就帶走。”
“水手,”那人說,“這沒問題!可他家里的其他人怎么辦?”
我彎下身,小杰夫細聲細氣地告訴我他家里除了爸媽外,還有兩個小妹妹。我給了他50美元。
“我會找個人幫他拿玩具的。”那年長的人對我說。他隨即叫了位快活的婦女用手拉著小杰夫。
在包裝電動火車時,那個人告訴我他也有兩個兒子,并且都在軍隊里服役。在多次互祝“圣誕快樂”后,送貨的小車把我們送到了男孩的家。
老杰夫·霍力斯的反應頓時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領回一個陌生人并帶回許多禮物時的神情。我能看得出他是個勤勤懇懇的人,為了全家的生計拼命工作,可對于滿足家庭的需要仍是力不從心。
“我只是個遠離家鄉的水手,霍力斯先生。”我帶著幾分尊敬地說,同時解釋了我怎樣從他兒子觀看那些陳列玩具時充滿向往的目光中看到了從前的自己。
“您難道不能讓這筆錢派上其它用場嗎?”
他聲音沙啞地問我。
“不,先生。”我答道。
他的臉變得柔和起來,歡迎我和他們共進晚餐。晚飯后,我給小杰夫和他的妹妹讀書,一直到他們上床睡覺為止。
“我想您是知道清晨前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的。”老杰夫說。一開始,他的話讓我頗感詫異;但隨后我明白了,我不再是個孩子,而是一個肩負著成年人責任的男人了。我和他一起組裝著火車。這項工作看起來需要整整一夜的時間。老杰夫的妻子瑪吉為我們準備了三明治和咖啡,并一直讓我講述著紐約的經歷。午夜時,我們停下手中的活兒,彼此祝福著“圣誕快樂”,然后又繼續著手將一個男孩的夢想變為現實的工作。
所有的活兒都做完后,我已是精疲力盡了。老杰夫對著組裝完的火車打量了許久,才輕輕地嘆了口氣,坐進那張破舊的搖椅里。
“我夢想能買下輛自行車。”他平靜地說。“那是一輛雙輪車:輻條是光燦燦的,車把是鮮黃色的,車座是真皮的。我真喜歡那種車,非常想買一輛。”
“小時候我曾在一家做女服的縫紉店櫥窗里看到一套圣誕禮服,我想要的就是那樣一套禮服。”瑪吉說。“我希望人人都夸獎說:“穿著那套漂亮禮服的小女孩多可愛啊!”
夢想,我暈暈乎乎地想著。孩提時代的夢。我猜想自己八成是在打盹兒了,因為接下來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時間已是清晨5點了;小杰夫正在推我。他想起來我還得在8點鐘之前趕回去。
“可以開了嗎?”其中的一個小女孩問道。
“是的。”老杰夫說道,“圣誕快樂。”
“哇!”孩子們帶著難以置信的喜悅嚷了起來。我們沒能像商店的櫥窗陳列員們安裝得那樣精巧,但終究還是把火車給安裝好了。
“爸爸?”小杰夫問道,“喬治?”
我和他爸交換了一下眼神,點頭同意了。這是電動火車充滿榮耀的首次正式運行。老杰夫和我各自擺弄一個控制臺,開動了火車。第2圈時,我讓小杰夫接替了我的位置。可5分鐘后,小杰夫突然停了下來,一句話也沒說就離開了房間。回來時他的手里拿著他買的禮物,臉上帶著驕傲的神情。
當他捧著盒子轉向我時,我想他是早就準備好了想說的話的。“圣誕快樂,喬治。”他輕輕地說。
我驚訝不已。禮物是一套梳子和發刷,還有一個裝其它化妝品的盒子。他伸過手來,然后又改變了主意,親熱地抱了抱我。分離的時刻是喜優參半的,因為我知道可能再也見不到霍力斯一家了。老杰夫謝了我,可我才是那個該說感謝的人呵。
當我走向車站準備乘車返回基地時,我意識到自己再也不會吹毛求疵了。這次經歷的收獲比我聽過的所有愛國演說都要多得多。
對我來說,這次經歷是一次頓悟。此刻,我明白了這場戰爭以及為此而進行的一切戰斗的意義。剎那時,一切變得如此輝煌而簡單。
(丹琳摘自《世界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