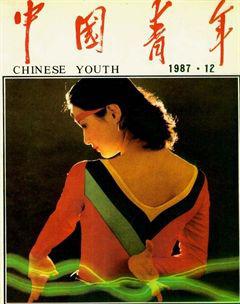關于《一個女大學生的手記》的再思考
曹明華同志:
你好!
最近一段時間,我發現你寫的《一個女大學生的手記》一書,在青年讀者、尤其是大學生中產生著強烈反響。此書出版4個月內4次印刷,已發行55萬冊,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從該書的責任編輯陳先法同志處得悉:你已收到全國各地青年讀者的近500封信;應廣大讀者要求,出版社已決定將此書再加倍印刷,增至110萬冊:你的《手記》也在文學界中引起震動,已獲得“上海市青年文學獎”……這部7萬來字的《手記》如此受到讀者青睞,這在近年來的國內出版界還是少見的。這究竟是為什么?我打算國慶前去趟上海,約請你寫篇文章,以“青年與社會”“青年與人生”為主線,圍繞青年讀者來信中提出的問題,反過來重新審視《手記》。我想,你畢竟只是一位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你對社會與人生的探索和思考,絕不會僅僅停留在《手記》上。那么,擬寫的文章可否用這樣一個題目—《關于<一個女大學生的手記>的再思考》。文章的詳細內容,待我們見面時細議。
祝愉快!
楊曉升
1987年9月10日于北京
楊曉升同志:
你好!遵命將稿子奉上,請過目。
盡可能按你的要求,采用了這樣的形式(受我第二本集子里有關談《手記》篇章的啟發)。內容基本都是讀者來信中較感興趣的,其中包括想了解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等。
乍一看也許會覺得與“青年與社會”“青年與人生”的大題目不很相符。但我信奉一句名言—真正的詩人在談著“我”時,其實是在談著普遍的事物。
我不喜歡就我不熟悉的題目去教誨人,而寧可現身說法,更多地偏重自己的體驗和感受,這大約也正是《手記》贏得人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假如稿子用的話,能否盡量不要刪?我自我感覺避免了流露任何“消極”的情緒與念頭,至于個別或許會讓旁人誤以為不夠“積極”“明亮”之處,其實是我一貫帶“個性”色彩的文風。祛除了這些“點”,也就祛除了大半“個性”。所以,我請求。
謝謝你的誠懇與熱情!你是我好長一段時間沉默以后,接待的第一個朋友。而這些天,又熱鬧起來。我終止了“自我封閉”,不再以拒絕的眼光對待外界。
但愿我沒讓你太失望!
曹明華 1987年10月8日于上海
記者見到你很高興!不過,我首先是因你的書而來的。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說你是“大陸的瓊瑤”,對此你作何感想?
曹明華不,不至于有這類嚴重的事情發生。我不會成為“大陸的瓊瑤”。至少有兩點最簡單的區別:
第一,即便同樣寫情愛吧,她是在全力以赴講故事。而我不,我對講故事天生缺乏興趣,我偏愛尋找“情節”背后的蘊含,尋找我和我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的帶有某種“真諦”性質的啟迪。
第二,瓊瑤的遺憾來自她的過分辛勤—一口氣拋出40幾部大同小異的玩意兒,自我塑造成一個“匠”。
我呢,《手記》收的是前幾年比較女性味的文字,而我一年半前在《交大研究生通訊》上寫的東西就已經讓人看了—讓北京一位博士生看了寫信來稱我為“老兄”。
不是“認識你自己,成為你自己,超越你自己”么?我深感“超越你自己”來得最夠刺激!而在原有層次上添磚加瓦的工匠活,實在不太夠意思。
記者你怎樣看待所獲得的文學獎?
曹明華我從一個比較純粹的理工科校園走來。在得文學獎當口曾讓我尋思的是,我的東西究竟“文”不“文學”?
因為首先,我信手寫來時“理工科”味很濃,就象我信中也不時地勾勒個“諧振圖”、勾個“模版圖”之類,來表達我許多“即興”的念頭(《手記》中為印刷的方便刪去了多處)。
記得在一次朋友們的聚會上,幾位男生對我的文字爭執不休。他們用“文學作品”的標準衡量我。他們大談起各類文學流派的比較,談起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談起“魔幻”和《百年孤獨》之類……然后衡量我。
是嗎?—一位和我并不熟悉的女生插言道—你們好象都在把曹明華的東西當“文學作品”來看,而我們不是。我們只感覺這是個活生生的可交流的對象,從它那兒,可以重新發現我們自己,發現我們自身的那么多微妙的體驗和感受……我在看的時候一點沒去想這是不是“文學”,是什么程度的“文學”;什么樣式的,“文學”。
記者讀了《手記》,沒見過你面的人,偏愛想象這是個性格內向、多思的人,實際上呢?
曹明華實際上人們很快發現我的兩大愛好是說話和社交。
當然,性格外向和內向并不能以是否善于表達來劃分。我喜歡表達,甚至常常喜歡用夸張的“修辭手法”,喜歡和朋友和環境達到一種氣氛上的交流,但這并不妨礙我的內心存在一個世界,一個有時候只屬于我的、純粹私人的世界。
但有一點是比較顯然的,那就是心靈的敏感。別人曾套用幾句現成的話來形容我:碰一下等于痛擊,響聲便是噪音,不如意就是悲劇,高興就是狂喜,朋友如同愛人,愛人無異于上帝,失敗不啻死亡。
再有,常常給人錯覺的就是—特別給那些單從文字上了解我的人錯覺的是,以為曹明華正滿腦子地正心情沉重地思考著啊……正滿心思考著關于“人生”,關于“社會”,關于諸如此類,等等等等。特別是《交大研究生通訊》上那篇長文的發表,更讓人想象我正在“沒有權威眩目的光暈,沒有神明幽暗的香火”中思考著,并且很可能是神情嚴肅地“思考”著……
而我自己呢,我自己深深地感覺到的,卻更多是自身那難以掩飾的、常常是充滿矛盾充滿非理性混亂的,甚至是神經質的一面。
那一個世界,那一個滿腦子,“思考”一點什么的世界,很多的時候并不感覺到它的存在。
時常地,在來去匆匆中,在平淡瑣碎中可以全然地遺忘了還有這么一個世界,一個充溢著“理性”的一個“思考”“問題”的一個富于藝術感的一個超脫飄逸的一個靈魂飛升的世界,一個,在這么一張白紙上編排句子的世界……
是的,常常全然地忘卻還有這么一個世界的存在。
可以因為買不到一件想象中的長大衣大發脾氣,可以因為想買一袋特別愛吃的“鴨肫肝”而重又充滿希望—“假如再買不到鴨肫肝,我對生活都失去信心了!”我慣用夸張的“修辭手法”。
荒唐么?也許。一個在這一刻把生活希望寄托在區區“鴨肫肝”身上的人難道不荒唐?
不過心平氣和地想,在平常的日子里,其實又確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鴨肫肝事件”充斥了我的生活啊!
當你不自覺地置身于這些個大大小小的“鴨肫肝狀態”中時,假如你被提醒,你會發現你距離所謂的“理性”很遠……你沒去想什么是正義啦什么是邪惡……離藝術也很遠,你也不會去多想關于美關于丑。
這時候更多的,是沉湎于自身生命的天地里,它并不見得寬廣,但卻確實地真切,這時候最強烈地作用于我們的,是生命的歡樂和悲哀。
是啊僅僅是歡樂和悲哀。
不過我,還是非常地感謝那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就象人類彼此間終究互相需要,需要朋友,需要語言的交流,需要聆聽和渲泄,還有彼此的啟迪和共同的沉湎……況且,還需要尋找,需要未來……
而于我,這似乎更有特殊的意義。
這畢竟是另一種讓我為之深刻沉醉的境界。是啊,一種境界。
我衷心地感謝這個世界的存在。
只是我還要承認,我想提醒別人也提醒自己承認
承認比這更寬廣更不朽的生活本身。
記者你對自己的基本估價怎樣?
曹明華我覺得我是先做人再做文,這個“人”,并不見得是個“好人”,而僅僅是個“活人”。這個活人正作著各式各樣“生”和“活”的嘗試,正作著嘗試生活……有時候碰得頭破血流。
我的文,便是那個“活人”的種種“不完美”的內心起伏和思維沖突的寫照。
我喜歡跟生命力蓬勃旺盛的人交往,喜歡他說他想說的,而不是“應該”說的;寧愿他做他想做的,而不是“應該”做的。
我每每看到我的一個好朋友熱情奔放于“迪斯科”舞場時愛穿的一件衣服—上面寫著:Still crazyafter all these years!
我總是不禁要感動。我知道我們不再會“crazy”,“after all these years”。因為“責任”和“義務”遲早要召喚我們。更本質些說,每個生命體活在世上,都需要遵循“得失平衡”的自然規律。我們這一代,到今天為止,還是向這個世界攫取的要大于付出的,而這,也是正常的社會現象。但當“after alltheseyears”,我們多少會感覺到沉重了,我們再也輕飄不起來。
然而,也正是“青春”賦予我們的這種特權,讓我們有可能享受這樣一種境界,享受我們青春的冒險和青春的妄想,放縱我們稚幼的柔情與執著的迷狂……
有權利crazy的年齡,為什么“不”呢?
—我這樣替自己解釋,這樣為自己開脫。
為一次又一次的crazy!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只有我自己知道,當然,同時也獲得了許多。
我是一個扔東西的人。
學功課也一樣,看來是學一樣,扔一樣的了。
學了理工科,我嘆口氣說,看來,將來的前景至多是高級的儀器維修工,或聰明的模仿者了。
學了些生物醫學,我恍然大悟道,原來“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也沒用”哪!于是稀里糊涂丟了公費醫療證后也不再覺得需要去補。
后來是懷著比較大的幻想去學哲學。想不到還沒學完,我就忍不住為我們的哲學現狀勾了份臉譜—
寒風凜冽中你問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冷不冷?”“哦,真冷!”她邊縮著脖子邊回答你。
而一個哲學家呢?“冷?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冷!冷相對于熱存在,沒有熱也就無所謂冷,此乃一對矛盾體,同屬一個哲學范疇。它們既對立又統一,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這種轉化,又是需要條件的,而條件……”
然后他終于側過臉來問你:“好吧,現在關于‘冷的概念徹底弄清楚了吧?現在你到底冷還是不冷?”
你于是完全糊涂!真正是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算不算“冷”了!
既然到了今天面對“文學”,也許要感謝沒有“學過”的緣故吧,我發現我還能夠幻想,還能幻想……
但這種幻想也很可能是有極限的。當然眼下,倒很有興趣試試。但我預感不久我會離開它,因為還有其他新的想法新的嘗試的渴望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