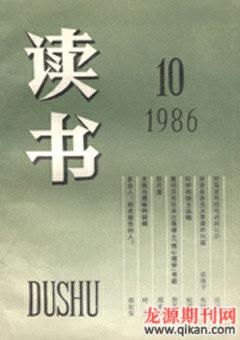尼采、法西斯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謝偉民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尼采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他是一個勇猛地向舊世界發起毀滅性攻擊的斗士,一個號召落后民族自強不息,在列強紛爭的亂世中爭得自存的思想導師——他就是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在那些最先進的中國文化人的思想、言論、著述中的。例如在魯迅《狂人日記》中,那不屈不撓、頑強與惡勢力戰斗的狂人形象身后,隱隱約約閃現著尼采的影子,我們甚至還能從狂人口中聽到分明是尼采發出的聲音,而《摩羅詩力說》中更有對尼采的直接贊美。
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世界的另一部分,尼采是德、意最反動的政治家頂禮膜拜的對象。在法西斯蒂的種族主義獨裁專政的理論里,在他們向世界人民磨刀霍霍,發出戰爭狂叫聲中,我們明明見到了幕后晃動著的尼采的幽靈。他們并不隱諱這一點。例如墨索里尼在一封復信中說:“在你給我的信上,你說我的演說及筆調有著尼采的口味,你說我研究過尼采,的確如此。十五年前,……我偶然得到他的著作。那是我從頭至尾讀破了的東西,我從那里受到很大的感染,他的著作醫治了我的社會主義”。(轉引自劉放相等《現代西方哲學》,下同)又如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說:“強者處于統治地位,而且為了不致犧牲自己的力量,不能和弱者調和,……要是這種法則不能支配著,人類就不可能有向最高生命發展的一切運動。”
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歷史現象。
一種哲學理論,即受到反動法西斯蒂的青睞,被用來宣揚種族優劣論、天才英雄創造歷史、確立暴君專制,成為帝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屠殺、殘害弱小民族的理論武器;它同時又受到被奴役被壓迫國家、民族先進思想家的重視,利用它警策人民、喚起人民反抗封建暴政、抵御帝國主義列強,成為弱小民族覺醒反抗的理論推動力。一個是民族自救,一個是毀滅他民族,這種現象多么矛盾,又多么尖銳地對立。一種哲學本身為什么會造成兩種極其不同的實踐后果呢?
如果我們再注意到同屬一種哲學思潮且為其先聲的叔本華哲學同樣為上述兩種人冷淡和漠視,那么這個問題的探討就愈發顯得必要而有意思了,它涉及到的是一個相當普遍而帶有規律性的現象。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一種理論的被選擇和接受,在多大程度和范圍、哪些方面得到接受,主要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決定:一是這種理論自身所具有的人類共同因素,與特定時代、民族、階級、集團政治經濟利益的契合度,一是特定時代、民族、階級、集團對這種理論的需求程度。換言之,即理論本身的內容特質與特定政治集團對它的要求。理論愈能反映出時代、民族特點,愈能反映特定階級、集團的觀念、愿望、情緒和要求,愈具實踐性,那么它被特定階級、集團所接受的可能性越大,程度愈深,范圍愈廣。理論本身具備的滿足對象的特點與對象對它的歡迎接受程度是成正比的。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處于兩種文化大碰撞大融匯時期的中國,曾經引進了幾乎所有西方人文哲學思潮、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黑格爾、培根、休謨、笛卡爾、斯賓諾莎、直覺主義、實用主義、唯意志論、馬克思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然而最先受歡迎的是尼采的唯意志論。為什么在眾多完整、嚴謹、龐大的體系面前偏偏選中了體系支離破碎、理論殘缺不全的尼采?為什么同屬唯意志論的尼采與叔本華,中國的先進文化人往往對后者不置一辭?這不能不從這種理論自身的特點和中國當時面臨的具體情勢中尋找解答。當時中國內部封建政治腐敗崩頹,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亡國滅種之勢迫在眉睫。一種失敗悲觀的情緒上下蔓延。振奮民族精神,反抗黑暗惡勢力,避免淪為奴隸民族,亡國滅種的悲慘命運,重新以宏放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中國先進文化人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他們苦苦求索,尋求著這樣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動力。系統、完整、學院化的理論體系,中國的知識分子暫時還來不及思考和消化,他們需要的是能夠迅速地付諸于實踐、指導實踐的哲學理論,即行動(實踐)哲學。這就是何以尼采哲學、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直至馬克思主義(實踐性是它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受到他們注目、歡迎、接受的原因。
尼采哲學的中心是唯意志論。它強調個人意志,把主體意志放在本體地位,高度擴張主體意識,強調意志的重大作用,它要使個人的要求、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乃至當作一切的主宰,它極端藐視現象世界,提出“重新估價一切價值”,“打倒偶像”,而這與中華民族要求重新強大起來,與舊傳統決裂,提倡個性自由解放,反對封建專制暴政,避免民族危機的歷史要求是相契合的。
上面強調了理論被接受的兩個主要原因。但我們從實際觀察注意到,一種理論并不是完完全全按其本來面目,毫不走樣地傳播、被接受的。中國先進文化人與德、意法西斯對尼采哲學接受的范圍、程度、內容就大不一樣。中國先進文化人接受的并不是尼采哲學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核心部分。這表明理論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有著不同的特點。
從來沒有一種理論是在本來意義上完全徹底地被人接受的,尤其是作為外來文化輸入的情況下,它受到時空限制、媒介(語言等傳播工具)影響。理論在傳播過程中會產生形變。另一方面,人們對理論的接受并不是無條件的全盤吸收,而是有選擇的,選擇角度和內容,依對象對主體的滿足程度而定。此外,接受者在接受某一理論時,往往并不慮及理論創立者本身意圖和出發點,而是按自身的要求和理解加以接受。因此常常會出現理論提出者的意圖和接受者完全相悖、或者不同的接受者在不同層次上接受同一理論而付諸于完全不同的實踐的現象。
經過這樣的分析之后,我們再來觀察尼采哲學所以同時被兩種絕然對立的階級、集團所接受這一復雜現象就不會迷惑不解,也不會因為今天的教科書把尼采哲學宣判為反動的唯心論哲學和代表了壟斷資產階級的瘋狂欲望而在具體分析五四文化現象時處于兩難的境地。
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機。在這樣的歷史緊急關頭,一種對解決現實危機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的行動哲學就比抽象浮泛的思辨哲學更受歡迎。尼采哲學對傳統理性和現存秩序的否定,非道德論觀,主觀上符合中國先進文化人反抗千年封建傳統和舊的倫常秩序、推翻現存制度的愿望和要求,而在權力意志這部分中,中國人只是汲取了其主體擴張、強化個人意志的因素,因為要求個性自由和解放,沖破封建制度和意識形態對人性的壓抑和束縛,也正是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當先進的中國文化人尋求救國救民道路,得不到普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在他們探索對國民性的改造時又常常首先過多地發現民眾中的落后消極因素,自然就會產生一種孤寂落寞的情緒,而尼采哲學中對超人的頌揚和愚民的詛咒,也就頗能引起他們的共鳴(當然僅限于這種意義上)。
另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現象是,同是唯意志論哲學,尼采在中國政治和文化界的影響比叔本華大得多,而叔本華卻頗受一些具消極傾向的文學家的歡迎,例如王國維。這歸根結蒂是由兩人哲學特質的不同所決定的。叔本華的生存意志說尤其他的倫理觀是悲觀主義的,他對人生的態度最后歸結為對人生的否定。這顯然與五四文化人爭取民族解放、救亡圖存的理想格格不入,因而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冷落和摒棄。
如是觀察和分析后,我們就不僅能理解和評價五四文化人何以對尼采哲學歡迎接受。更重要的是,我們能認識到對一種理論的評價,既不能僅僅根據它對進步或反動力量的影響而褒揚或貶抑,也不能僅僅就理論本身作出純粹的邏輯結論,而應從歷史背景、思想淵源、承繼關系、主觀動機、客觀效果等等方面給以全面綜合考察,作出準確、恰如其分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