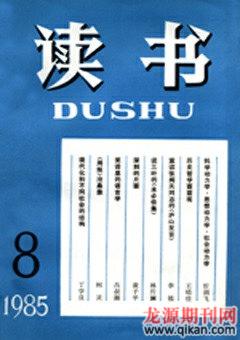接受美學的開山鼻祖
姜云生
繼《讀書》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張隆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文初步向我國讀者介紹了接受美學的基本概念之后,張黎也在一九八四年第九期《百科知識》進一步闡述了作為“新的美學觀念”以及“西方文學研究中一種新興的方法論”的接受美學,較詳細地介紹了接受美學的主要內容。之后,國內不少報刊(包括一些文摘報刊)紛紛轉摘以上內容,接受美學為更多讀者接受。一九八五年第二期《讀書》又有劉再復撰文據此發揮,談了接受美學對他的啟發。以上的介紹,雖在個別細節上略有不同,但大體上都認為接受美學是近十幾年來新產生的美學流派,其理論奠基人為波蘭哲學家英伽頓,聯邦德國的漢斯·羅伯特·堯斯一九六七年發表的《文學史作為文學科學的挑戰》一文,被認為是接受美學形成一個學派的宣言。
關于接受美學的紹介文字目前還不多見,就連所謂其“宣言”《文學史作為文學科學的挑戰》一文,也未見譯介。但據劉再復同志云,《讀書》和《百科知識》上兩位張先生的文章已經“相當清楚地描繪了接受美學的主要輪廓和基本面貌”。如果劉先生的話可以成立,那么我要說:接受美學并非一種“新的美學觀念”,羅曼·英伽頓和羅伯特·堯斯也算不上這種文學研究方法的創始人,著名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讓—保爾·薩特早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什么是文學》一書中,就率先提出了這種文學理論,該書《為何寫作?》一節(見《現代西方文論選》第18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版,伍蠡甫主編)詳細地分析了作品的創作與閱讀兩個方面,指出閱讀是包括寫作在內的整個文學創作過程中有機的一環,作家與讀者是互相合作的一對。若將薩特的理論對照接受美學的幾個主要方面(關于后者,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復述,請讀者參閱張隆溪、張黎及劉再復諸先生的有關文章),我們將會發現:(1)如果接受美學真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薩特倒是其開山鼻祖;(2)薩特的理論不但包括了接受美學的主要內容,而且在作家與讀者的關系之論述上,立足點更高,更有見地。為便于讀者比較,茲將《為何寫作?》一文中有關理論簡介如下,每一段內容均盡量引錄原文——
(一)文學創作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它離不開閱讀。
“這個辯證關系在寫作藝術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為明顯,因為文學客體是一個只存在于運動中的特殊尖峰,要使它顯現出來,就需要一個叫做閱讀的具體行為,而這個行為能夠持續多久,它也只能持續多久。超過這些,存在的只是白紙上的黑色符號而已。”(《現代西方文論選》第193頁。下引書名同,引文只注頁碼。)
“寫作活動包含著閱讀活動,后者與前者存在著辯證的聯系,而這兩個互相聯系的行為需要兩種截然不同的代理者。正是由于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努力,才使那個虛虛實實的客體得以顯現出來,因為它是頭腦的產物。沒有一種藝術可以不為別人或沒有別人參加創造的。”(第195頁)
(二)讀者的活動是一種主動的再創造。
“……從一開始,意義就不再包含在詞語中,因為讓每一個詞的詞義變得可以理解的,反而正是讀者;而文學客體盡管是通過語言被人認識,卻決不是用語言表現的。而且,一本書中排列成行的成千上萬個詞可以一個一個分開來念,從而使這本書的意義不顯示出來。要是讀者不是從一開始而且在幾乎無人引導的情況下去極力領會這種不言之意,簡而言之,要是他不去虛構這種不言之意,沒有把他所喚醒的詞和句子放在那兒并把它們緊緊把握住的話,那么他就會一事無成。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把這個活動叫做再創造,或者叫做發現,也許會更恰當些,我的回答是,首先,這種再創造將會跟第一次創造一樣新鮮,一樣有獨創性。……他(指作者——姜注)的不言之意是主觀的,先于語言的。那只是無言,是與靈感相一致的富有生氣的一種內容,它將由詞來一一加以表達,而讀者創造的不言之意卻是一個客體。在這個客體的最中心,存在著更多的不言之意——這是作者沒有說出來的。這是一個有關不言之意的問題,這些不言之意十分特殊,以致它們在由閱讀引出的客體之外,不能再保有任何意義。”(第196頁)
“……讀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也就如何存在著;……”(第198頁)
“……觀者的想象不僅有調整作用,而且有組織作用,這種想象并非漫無目的地展現;它被召來在藝術家所留蹤跡之外重組美麗客體。”(第199頁)
(三)閱讀是有指導的創造
“……讀者必須不斷越過作品的文字自己創造出這一切來。當然,作者在引導讀者,不過作者所做的全部事情也只不過引導而已。作者豎立的界標被空間所分隔。讀者必須把它們連起來;他必須超過這些界標。簡單地說,閱讀就是有指導的創造。
…………
以上連篇累牘地摘抄,無非是想讓讀者看到:薩特關于閱讀與寫作、讀者與作者關系的分析,與接受美學何其相似!差不多可以斷言,接受美學的最主要的內容,薩特早就有所闡述!如果說還有什么欠缺的話,那便是“接受美學”這個名稱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薩特關于作者與讀者關系問題的闡述,似乎比目前我所見到的接受美學理論更透徹,更全面。在這個問題上,薩特反復強調以下兩點——
(一)作者主動意識到讀者的重要性,向讀者發出吁求。
“既然創作只有在閱讀中才臻完備,既然藝術家必須委托別人來完成自己所開始的工作,既然只有通過讀者的意識藝術家才能認為自己在與作品的關系中是本質的,因此,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一種吁求。寫作就是向讀者提出吁求,要他把我通過語言所作的啟示化為客觀存在。”(第198頁)
“……作家要求于讀者的,并不是一種抽象的自由,而是讀者全部的天賦;連同他的感情、他的偏愛、他的同情、他的性生活方面的脾性,以及他的價值觀。”(第202頁)
(二)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創作過程的合作是有機的辯證關系。
“……作者進行寫作,是為了要跟讀者的自由打交道,他需要它是為了使自己的作品得以生存。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他還需要讀者把他交給他們的這個信任還給他,需要他們承認他的創作自由,并且需要他們也用一種對應而相反的吁求來獲取這種自由。這里,出現了另一個關于閱讀的辯證關系;我們越體驗自己的自由,我們也就越承認別人的自由;別人對我們要求越多,我們對別人的要求也越多”(第202頁)。
在薩特的文章里,還有許多讀者(或觀眾)參與整個創作過程的具體分析、舉例,這兒不再一一摘抄。但讀到這里,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對目前介紹的接受美學概貌發出一點小小的質疑,即:接受美學的真正開山鼻祖究竟是誰?羅曼·英伽頓及漢斯·羅伯特·堯斯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薩特的影響?從薩特一九四九年出版《什么是文學?》到一九六七年堯斯發表《文學史作為文學科學的挑戰》,這種把讀者作為文學創作“動力過程”的主動因素之一的學說,是如何濫觴、壯大而終于成一個學派的?凡此種種,若能進一步作番比較研究,必然會有更大收益。